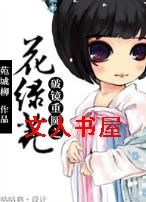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20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河道转角处,小屋近在眼前了。
唯一能称得上“家”的地方。
像夕阳等待地平线那样,他等待着结局。
屋里没人。
它已经无法再供人居住。他铺设的屋顶垮了,压倒他做的桌椅。他钉好的篱笆满地横尸。他疏通的水井被拦腰折断的红松堵着。或许看不惯这个空荡荡的家被灰尘浸渐蚕食,不知什么时候,暴风雨夹杂雷电,干脆利落地毁了它。
毁得就同它认识他之前一般彻底。
云缇亚将轮椅移到尚且完好的一角屋檐下。在这里,可以望见属于他和爱丝璀德的那道河湾。他俯身洗剪短了的银发,而她用裙子兜起水,一遍遍浇到他头上。
现在他的头发重新变长了,像只小兽,围着他颈窝。
薄暮和拂晓静卧在他双臂间。
他醒着,而它们在做梦。
他等待那个记忆中已笃定、但他仍愿意为它供奉一丝幻觉的结局。
夕阳嵌进地平线的身体。四周暗下来。夜枭的鸣声取代了淡黄柳莺的鸣声。星光洄游,如薄雾逆向穿行于河流之上。
云缇亚张开眼睛。
“啊,你在这里呀——”
他听见有人欢快地叫道。但那不过是风,经过阔叶林。
他发觉自己不管尽多大努力保持清醒,终究还是沉陷梦中。而这个梦,正被死亡的子宫所孕育。
可以放弃了吗?
痛苦早已离他远去,它带走呼吸里的温暖,还有时间。
只剩下疲惫,比他曾战胜过的任何敌人都强大。
可以松开试图握紧的手了吗?
薄雾彼端透出极轻极淡的紫罗兰色,淡得就仿佛一个人全身的鲜血,倾入汪洋大海。
他等的结局依旧没有到来。
这是最后一次看黎明升起吧。
他想。
屋檐后面,乍然,有道微小的光华眨了一眨。
哦。
露珠的反光。
不,不对,那是……
轮子转动,像趋光的飞虫被吸引过去。屋后空地原有他亲手掘的墓穴,一个对他和爱丝璀德同样重要的人安眠于此。现在,这儿飘摇着绝非磷焰的微光。
它来自一朵平平无奇的白色小花。
“高崖百合,春夏两季都开,只能长在贫瘠的土壤里……”
云缇亚垂手去触摸那花,浑然不觉自己离开了轮椅,摔倒在地。
原先,石块整齐垒放墓前,无名的白桦树作为墓碑。摧毁小屋的暴风雨也将白桦树连根拔起,泥土像被犁过似地翻开,底下埋葬的遗骸曝露在外。那颗头骨躺着,静静地,如同走完了一生的旅者十分自然地躺下去歇息一样。
它曾被人大力踩踏过,留下一条裂缝。
花朵从裂缝间嫩生生地探出来。
瓣沿有声音坠落。
坠自他心中,然后才落入他耳中。
一声。
又一声。
“啊,你在这里呀——”
回头的刹那,整个世界擦亮了。他看见萤火——名叫萤火的狼,眸子碧青明灭,弓起刚劲的背脊。第二眼,它显得比他熟悉的萤火要瘦一圈,眼神也锐利而陌生。年轻的公狼身边,毛色洁白的朝露张大一双乌黑瞳仁,朝他边嗅边叫唤。
乌黑卷发,洁白衣裙。
光阴慢条斯理地溯流,他在溪水里梳洗如溪水那么长的头发,全身上下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的女人撑着蕉叶,笑吟吟将一枚篦子递给他。被发丝、蕉叶的脉络和篦子密齿细细筛过的光阴,终于一点一滴,都滋养到那花朵扎根的缝隙中去。
他的喉咙颤动着。
“爱……”
在声带焚烧过后残余的荒芜之地,也开始生长出语言。
供奉幻觉,然而回报以真实。
“爱……丝…………”
你看,时间是可以后退的。即使无法把我们带回过去,它也能圈住我们。所有你以为走过了的路,其实只有一个圆的直径那么长。所有你以为遗失了的事物,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身边。
“我爱的人呢?”
“他们会伫立在生命之河必经的微光中,等待着和你重逢……”
“我说过,”爱丝璀德双眼清亮,“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翻倒的轮椅旁边,她拥抱他。发肤贴得不能更近。她的黑发与他的银发。他伤痕虬结的浅黑色皮肤与她细腻的白皮肤。
那是夜与昼。
而黎明就升起在它们之间。
☆、尾声:远空
当你是生命颤抖的唇上的一句默语,我乃是那唇上的另一句默语。然后生命将我们道出,我们便在追忆昨日、向往明天的颤动中降生、长大。昨日是称臣的死神,明日是冀求的新生。
——《先驱者》
尾声:远空
我站在这里,向你们讲述那个男人与那个女人的故事。眼前刚好刮来五月的风,将羊群像白色荼蘼花一样绚烂地吹入田野。夏天拖着绿油油的裙裾在自己的筵席上奔跑,泉流、林木以及飞鸟都是它的宾客。我见到浅淡的细埃沉浮,我听到绣眼鸟和蓝腹山雀的鸣唱,它们受阳光催促,去邀请更多的人来赴这场盛会。这是曼特裘一世的时代结束后的第十年,夏依二十五岁,我十九岁。我们的国度至今没有名字,从异国人给她的熙熙攘攘的称号中挤出来,走上十个夏天用青草为她铺成的大道,走向前方的悠长季节。
而我站在这里,站在她的脚印当中,向你们讲述那个男人与那个女人的故事。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两人。十年间,我和夏依六次返回鹭谷,等着我们的都是尚有余温的小屋。门口的园圃才锄过土,采摘下来的蔬果放在盆里还很新鲜,床铺干净整洁一尘不染。唯独人不在。
他俩的事我们只能从鹭谷镇上居民的闲聊中知悉。天气晴好的早晨或傍晚,山丘上常常有个白衣黑发的女人,用轮椅推着一个男人漫步。那男人不能行走,面目全非,但十分安静。女人不时低下头和他说话。谁也没想过要接近他们。当他们交谈时,风会起舞,替他们抹去周围的声音。
狼跟在他们身后。
鹭谷林区依然有狼。它们人畜无害,只捕食林子里各种小动物,偶尔聚集起来围猎糟蹋庄稼地的山猪和熊。镇民们再次习惯了与这些野兽和平共处,将它们同重新组建的民兵队一并视为镇子的保护者。
我们没在鹭谷久待。要做的实在太多。无论我的家乡旺达镇,还是哥珊,都只是短暂的居留地,我们旅程航道中的沙洲小岛。夏依忙着钻研草药学,乌梅加肉豆蔻可以止泻,蓖麻籽捣烂治毒疮瘰疬,悬钩子发汗退热,芦荟擦剂缓解烫伤。他试图将这些和他父亲传下的解剖学融合起来,我也经常会就人体结构向他请教——为了增进剑术。哥珊率先开办了面向平民的学校,学费允许用劳动代偿,如果以优秀成绩结业后愿意付出同等时间到下面小镇里的学校去教书,更是分文不收。夏依学习治病救人,而我学习如何保护自己。
我只有左手可以持剑,伊叙拉将军说,这是缺陷,但也是优势。虽然贵为总督军,而且三度被选为执政官,他仍让我们像称呼第四军统帅那样称呼他。早几年教皇的残余势力在边境发动了两场小规模叛乱,他是忙里偷闲,抽空来给我们讲习。有以前老师的传授和军队里一些底子,我学得很快,不到半年就能在右臂残肢绑上小盾维持平衡,左手用偏门的戳刺来对付惯用右手的敌人。
待完成学业、准备到家乡旺达新办的学校去报道的那天,伊叙拉将军把我们叫来。“喂,那家伙怎么样了?”他问。
我和夏依对望一眼。“您指的是……”
“云缇亚啊。杳无音讯,无论官方慰问信还是以私人名义写的信件,连个水花都没回一声,我送东西他也不收。冬泉山脉附近发展起了新的茹丹城镇,据老一辈人说,略有当年吉欣城的影子。真想他过去看看哪。”
夏依笑出声。这家伙还是那样,脸上什么都藏不住。我们拿出一幅画,送给将军,他瞧了老半天,挠着头哈哈大笑。这是当他以执政官与总督军的身份出席公民大会时我们无缘得见的表情。
十年前,我们初次回鹭谷时,在那空寂无人的小屋里歇了一宿,翌日醒来,床头摆放着一只木雕小狗。第二次我们有意留下信函,照样过夜,早晨收到填充了麦芽和薰衣草的布偶。第三次收到椴树皮纸订成的一本药草图鉴,专门给夏依的,配词注解是熟悉的花体字。第四次收到植物种子拼缀的挂画,即我们给伊叙拉将军的这件赠礼,画上有个人我怀疑是他,独眼,骑一匹呲牙咧嘴的马,正在被月亮追赶。第五次我留言说剑技长进了,于是收到一柄精巧的黄铜鞘小匕首。第六次也就是前年,恰逢冬天,收到手织的兔毛围脖,云朵那么软和,戴上才发现边角用染色线将我与夏依的名字绣在一起。
在我们第七次赶往鹭谷的路上,尘土蹁跹,空气里拥挤着夹带汗味的呼吸。这是大地的气息,粗俗,却富有生机。路面拓宽、夯实,形成驿道,零售商铺在道旁聚集。高架水渠修起来了。远远地,可以望见城墙。我有点替自己的家乡旺达嫉妒鹭谷。比起上次来,这地方变化更大了:它正向平原上扩展,由一个镇子逐渐变成哥珊五分之一那么大的城市。
这十年来国外的大事件林林总总,而尤以今年为甚:沙努卡可汗才回到中洲,立刻叫本土茹丹人和苏佞人的抗击缠得脱不开身;他侵占帝国东部六省而建立的亚布舍阑汗国,自他独生子一死,便被他的亲兄弟和手下大将拆为四块,早年投靠他的暗血茹丹驭主慕雅德也在其中分了一杯羹。趁着三大汗国与暗血茹丹国乱斗不休,耶利摹帝国开始整顿还没有被连年征战耗干净的力量,准备收复失地。至于奥伯良三世,病恹恹而且脑子已经不大清楚的皇帝,没能撑过今年。他膝下无嗣,皇冠交到妹妹诗蔻缔公主——她丈夫就是那团叫卡尔塔斯公爵的肉球——四岁的儿子手中。对于帝国人,这个位置的变迁似乎不影响他们耕地、打铁、做买卖和战斗,但我不知道这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据说小皇帝长得清隽瘦削,简直是从舅父孩提时的画像里走出来的,完全不像他那比怀孕母猪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