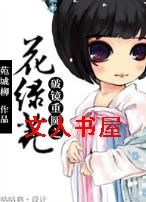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1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虚妄。”
云缇亚说。
一丝叹息在他话语的瀑布中溅起几可忽略的水花,转瞬无存。
爱丝璀德双眼许久未曾眨动。“就这些吗?”她问。
她走近前,抬起一只手。云缇亚以为她会一掌掴在他脸上。他不打算闪避。
可那只手仅是把一件东西递了过来。
朱红的桃花心木篦子。
“我以前送给你,”她虚浮的目光触摸着他剪裁到耳根的发梢,“即使你已经不需要了也罢,我并不准备再收回去。”
云缇亚看着她缓缓举步,走过他身边。若他的心还鲜活,这平静必将令他畏惧。
……但它现下俨然已是死物。
夏依和凡塔抱着药镰和柳条篓从屋里跑出来,眼见气氛诡异,都不敢开口,快速奔向爱丝璀德。“我带他们去采药。”似乎觉得还是该知会一声,她说。
云缇亚脑中木然。
“走铺了捕兽夹的那边。小心陷阱上做的记号。”
除了脚步,他未听到任何声音。
最后连这也不存在了。天际红霞抹散开去。艳色的河流复归明澈,仿佛记忆深处的血痕与战火终究为时光所冲化。
云缇亚仍一个人坐着。膝头摊开那本日记。
像一块被山洪推来的岩石,落了根,生了苔,便不愿意再动了,偶尔也是风嬉笑着来喘吁着去。天空渐渐又彤光斜照,只不过从东边换到了西边,月牙在苍白的底色上刺破尖角。
爱丝璀德没有回来。
纸页翻动。那小小的线条人一直等着,但屋子是空的。他奔走,寻觅,叫喊,遍体鳞伤,蹒跚踉跄。雨填满了整个山谷,洗去他带血的足迹。他开始做梦。待他的梦中之梦醒了,她会自身后蒙住他眼睛,用言笑晏晏来昭告她的出现。
雨下得铺天盖地。
而她再也没有回来。
作者有话要说: 本章插图
☆、Ⅷ 此间(7)
“你自信能从这样一个时代中幸免吗?……”
弓身是复合黑木,很沉,长久以来已被持弓者手上的剑茧磨得光润;反倒是弓柄镶嵌的乌银和象牙,不知不觉侵蚀出了古旧的边沿。男人的粗糙手指攥住它们,一分一分绞紧弦索。将足有半个成人身高的长弓挽到背后,他承负着它的重量,那只不过是十数年前伸过来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肩头。
“驭主。”伊叙拉用自己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他端起弯刀。辉光在他戴着半片面罩的脸上映出一枚月亮。
吉耶梅茨去世那年的深秋特别冷,仿佛严冬受到死亡的召唤提早来到。那时候令整个教皇国为之剧颤的叛乱,已随着一个人了无悬念的失败而告终,但真正的凛寒才刚刚起步。伊叙拉只记得坎伯兰战场通往哥珊的路无比漫长,他坐骑前面驶着三步一顿的囚车,后面则是怎么也载不完的叛党首级。无数死者,和一个即将死去的俘虏,这就是他生平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带给那座纯白之城的全部。
高耸的内城城墙和永昼宫双塔已经遥遥可见了。部队暂停下来。不用等到下一次休息,他们便能抵达圣都。伊叙拉扯开酒袋灌了一口,还剩不少。往常他定然会一饮而尽,可此时,浇到喉中,却寡淡无味。
副官走过来低声说了两句。伊叙拉跳下马,走到囚笼前,抽刀挑起上头遮盖的黑布。
那双伤口般血红的眼透过栅栏望他。满含倦意。
“你还活着。”伊叙拉冷冷说。
贝鲁恒笑了。重病和伤痛堆压在他身上,几乎要熄灭他最后一丝萦绕人世的气息。但他仍清醒着。伊叙拉不知道这该值得敬佩还是怜悯。
“有水么?”
“只有酒。”
“……也行。”贝鲁恒说。伊叙拉必须极力屏息才能听清楚他的语声。他递去皮袋,贝鲁恒没接。伊叙拉不管副官一旁支支吾吾地劝阻,拿钥匙打开囚徒腕上铁镣。昔日的第六军统帅手抖得厉害,好像捧的是一团火焰。用马奶掺杂稞麦酿制的舍阑酒烈性非同寻常,他几度咳嗽,待皮袋空了,唯余喘息。手里的火焰窜到他脸颊上,伊叙拉瞥见他颈子处几道不易察觉的鞭痕。禁令在先,茹丹士兵们只能悄悄地发泄怒意,只要不是太过分,伊叙拉一般也充耳不闻。
他们需要一个释放的缺口……那些被吉耶梅茨溘然留在黑暗中的族人。
“笑什么?”白舍阑人问。阴影里,贝鲁恒脸上的表情一闪即过。
“想起一些人……的命运罢了。”苍白的手指抓着栅栏,酒精似乎给了他暂时振作的力量,他的话虽轻却是清晰的,尽管仅维持了短短片刻。“第四军如果由你来继承,大概……会存续下去吧。”
“你没有说这话的资格。”
伊叙拉一把扣住他的手腕,令他看着自己。“驭主一生为茹丹人的自由战斗,为全族的存活不惜向人屈膝,最后却因你们西方白佬争权夺位的内乱而死。我族如今寄人篱下,信奉他人的宗教,受人驱遣,但总有一天能获自由。我只忠于吉耶梅茨,不是你们教皇国的宗座,不是诫日圣裁军!西方的神明存不存在,爱不爱祂的信众子民,与我何干?但惟独你——”字字顿挫,声如寒冰,“制造一切杀戮的人,斩断我族中兴支柱的人,不配发表这番感慨!”
“只为吉耶梅茨和你同族战友之死,为什么要送我回哥珊接受审判?用你所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杀了我……岂不是更加解恨?”咳嗽声剧烈不止,直欲将某个温热的脏器也咳出来一般,而被紧攥的手竟无颤动。“伊叙拉,你并不信仰异国他乡的神祗……但你自信能从这样一个时代中幸免吗?”
谵语。
不过是将死者的谵语而已。
“谁能说他人的生死真与自己无关?谁能独立于洪流之外活下去?波浪滔天,陆沉为海,连飞鸟都失了归巢无处落足,谁竟幻想自己能保有一个干干净净的身体?你站在这土地上,就得背负它正在罹受的悲苦……尽管你体内流着的是茹丹人和舍阑人的血液。如果你不想被冲垮溺毙,倒也简单,只消丢掉那微不足道的清醒和良知,等现在发生的成为历史,它自然会为每个人承担起罪责……”
“就凭你,”伊叙拉喝断,“也跟我谈什么清醒良知!”
所有人的视线齐齐投转过来。一声雷霆后跟着的是死寂,士兵们鲜见平日随和不拘的首领如此厉色,都有些惘然。副官面色泛白,好半天才想起清清嗓子:“大,大人,早说过这家伙……”
伊叙拉推开了他。
贝鲁恒还在笑。鲜红得随时像有血珠滴下的额印表明,他仍是一个圣徒。
“我低估了你?但愿如此……”与血同色的眼瞳抬起,令人惊愕的是它们仍能聚敛锋刃之光。“听着,伊叙拉,”言语仿佛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口中吐出,却照旧,轻如飘雪,“有朝一日你也许会走上我曾站立过的位置。你的光辉将被献祭给民众的渴慕,你的肉体将用来供养他们的饥饿。真到了那时,你无法摆脱,也无力抗拒……‘他’会令你迷醉,令你入梦,如同他对这整个国家所做的一般。但你必须清醒。万刃加身也不能昏迷,黑夜漫长也不能睡去。无论有多艰难,你的眼睛也必须睁开,否则就丧失了最后一丝看见晨光的希望……”
“伊叙拉,”垂死的男人说,“像吉耶梅茨那样,睁着眼,活下去。”
“——这算什么?忠告吗?”
“作为答谢你一路上的照顾。”贝鲁恒轻擦脸颊,烈酒燃烧的最后余焰随他手指拭净。“或者,就当我不胜酒力……胡言乱语吧。”
伊叙拉用马鞭指着囚笼后面,几辆大车拖载的、原本被称为第六军的叛军士兵头颅。
“你亏欠的是他们。”
贝鲁恒望过去。许久,有阴翳蔽上他眼睛。“……是啊。”他说。
他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伊叙拉将蒙住笼子的布幕放下。十天后,在哥珊,他旁观了贝鲁恒那被冠以净罪礼之名的死刑。其时他已穿上了吉耶梅茨遗留的战铠,披风背面纹上自己的白枭图案。整个诗颂广场染得一片猩红,狂信徒们待人群散去,费力地引来河水冲洗残迹。他没想到一个人身体里流出的血会那么多,几乎要布满他视野所能涵盖的大地,而它们,终究和千百年来染红哥珊的众多无名鲜血一般,一点点地被从圣城纯白无瑕的面庞上冲刷殆尽。
“将军。”通往仪式走廊的门推开了,来者一袭毛皮镶边的红袍,手捧礼器。是总主教。两年前他也是这样一副装束,低着眉眼捧来宗座亲书的任命敕令。时间的碎片总是不断穿梭反复。伊叙拉还刀入鞘,锵地一声,血光在他眼前的昏暗中瞬即退去。
冲刷殆尽。
“猊下的座驾就在圣泉厅外面,只等您一起登车了。”
伊叙拉把弯刀和装满三十四支箭的革囊挂在腰后。他握住另一柄武器。
教皇所赐的十字权剑。
指头的硬茧与琴弦涩涩摩擦,乐音悬停在决泄前的一霎,又飘忽着接续下去,像一只足踝被丝线牵缚的飞鸟。聋诗人的六韵诗却提前唱到了收梢,五指一划,汩汩喷涌的圣泉池水仿佛大幅丝绸断裂,那瞬息过了,它们才重新开始流动。
“这首歌太老了,诺芝。”教皇移开托在下颔的手,脸上难得泛起年轻时代的笑意。
聋诗人在乱发后翕动着浮肿的眼皮,没人知道他从对方唇形上还读到了别的什么。“它还没写完,我就失了聪,自那以后我的下半身一直站在坟墓里。”久未开口,他嗓音嘶哑,“由衰朽之手创作出的诗歌,想必也腐烂可笑吧。”
“那一年你刺聋自己的耳朵,因为你不想写、也再写不出令我满意的诗歌。身为诗人的诺芝,那个时刻就已经在我面前这副躯体上死去。”教皇轻叩座椅扶手,响应着空中并不存在的节拍,“我竟不配让一个歌者为我发声么?哈……贝鲁恒也和你一样……”
“您需要的是为您执剑的手,不是歌唱的喉咙。”
教皇哑然失笑。鎏金三重冠冕的流苏垂饰蔽盖住了他的表情。
“但我与他不同。”聋诗人从乐师的位置上站起,深深一躬,“他尚有持剑刺向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