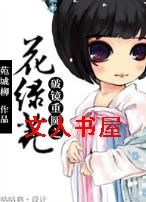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母亲为了她的祈誓,长年素食,别说鱼,连煮过乳酪的锅也不碰,连浮起一星油沫的菜汤也不喝。本来多雍容优雅的美人,没几年就瘦成了一副活骨架。”吉耶梅茨撩起面幕的下摆,又往口里倒了一杯石榴清酒。“结果呢?祈誓能有多大的作用,你自己很清楚。”
云缇亚不置可否。他看见路尼枢机正在和贝鲁恒交谈,神情关切中甚至透着几分谄媚。两名女修院长请贝鲁恒说起在西庭的见闻,从国都大圣堂的穹顶画到大公夫人的腰围都是她们感兴趣的话题,而贝鲁恒只是淡淡微笑,以水代酒。聋诗人又唱起了一首用俚语写成的箴言歌,有几位枢机主教似乎觉得歌词太过粗鄙,但见到贝鲁恒乃至上座的教皇都听得颇为入神,便也放松了眉头,和众人一起鼓起掌来。
“把你的锡塔琴拿出来,再唱一曲吧!”教皇笑着端起杯子,虽然知道他的宠臣懂得唇语,声音还是洪亮到令席上每个人都能听见,“圣贝鲁恒和你不是忘年之交么?就唱由他作词,你所谱曲的那首歌。”
尽管早已年近五十,教皇圣曼特裘一世仍然是云缇亚所见过的最英俊的人。绛紫镶金的日轮和十字星嵌在他微现纹路的额心,除此之外,他全身并无多余饰物。衣着只是简单的圆领垂襟大袍,外搭不知有多少个年头的旧金花鼠皮披肩,而他的黑发却仔细上过油,连鬓角都修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唇边始终带有笑纹,但眉尖也始终敛着反复打磨的犀利,他的手现在已很少握剑,却仍然坚硬、修长,充满力量。很难相信,在这位名将出身的至圣者面前,甚至察觉不到一丝半点的压迫感。人们视他为兄,奉他为父,以他的声音为神谕,以仰望他为莫大光荣,甚至争相模仿他的言行习惯,乐此不疲,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威严,或者比历史上几位以仁慈宽和闻名的教皇更为博爱。他的英俊不仅存在于面庞,那是一种流露在影子与足印里的白皙光辉,用天使的语言也无法述说的玄妙,令少年为之疯狂,老者为之哽咽,妇人为之着魔,男人为之效死。
曲子又奏起来了。有人跟着和唱,有人轻轻击打节拍,而吉耶梅茨依旧没有抬头。
“我今天见到了令嫒。”云缇亚低声说。
吉耶梅茨放下手中的吃食。云缇亚能感到那鹰一般的目光刺穿面幕朝自己射来。“达姬雅娜?”
“圣者似乎对她颇为赏识。”
“关我屁事。她不是老早就和我断绝关系了么?因为我身为妃主的配偶却没有跟随一同殉死,因为我是茹丹的将领现在却寄人篱下为异族统帅军队,因为我对她说要么参军,要么进修院,要么不做我的女儿。她选了第三条路。她以为总有一天她会当上妃主,会带族人重返家园。笑话!茹丹早就没了,被舍阑人杀得干干净净。她不是我的种,她身上没有她母亲坚强隐忍的半点血液,只是幼稚地相信音乐和文学会给她带来所谓的骨气。音乐?文学?我早告诉过她,在火海、尸堆和舍阑人用她兄弟姊妹的脑袋砌成的头骨塔跟前,那些狗屁都不是。”
杯沿有意无意地碰到唇间,酒淡得有种苦味。“……她不过是个孩子。”云缇亚说。
“十七岁,不是七岁。云缇亚,你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那时‘诸寂团’还如日中天,不是吗?”
云缇亚没有再吭声。在他的四周,永昼宫这头巨兽仿佛正对坐在它喉咙里的渺小存在沉默地微笑。从它的至深暗处,响起直抵记忆的隆隆回音。那些过去黯然难辨,他早已不愿去反刍,然而面部的伤痕又隐隐痛了起来,似乎回到了多年以前,有人拿着烧得发白的烙铁,在脸上使劲按下的那一刹那。
吉耶梅茨突然扔开酒瓶,将脸深埋在双手中,面幕被他的粗糙手指揉成一团。“答应我,”他艰难地叹息,“她那么天真幼稚,在这座城不会比兔子在狼群中活得更久。或许她和你的母亲一样……都在用一辈子去寻找永不能得到的东西。”
流畅的旋律在聋诗人琴弦上扬起一个颤音,如冰泉浪花激突。云缇亚看着教皇从座位上起身,对贝鲁恒点点头,于是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不过这对席间的氛围已没有太大影响。主教们相互说着客套的敬辞,除了阿玛刻,没人向不起眼的末席投来目光。吉耶梅茨并未要求什么,但云缇亚已经懂了。
“我答应。”他说。
拨子轻盈划下,锡塔琴的四根弦一同铮然作响,将他的低语淹没。
晚宴散去后,云缇亚与阿玛刻一起步出宫门,在圣湖能容纳八辆马车并驾齐驱的长桥上行走。夏天的夜来得太晚,西方天幕呈现出黄昏与黑暗深深交融的幽红色,月亮倚在那里,孤独而冷寂,它的对面,逝海之上,群星正焕发着喧闹的光辉。
“这座城市真奇怪,”阿玛刻说,“它看起来似乎随时可以为它的主人献出生命,却安然无恙地这么屹立了上千年。”
云缇亚猛地抓住她的手。他四下里望了望,没有“葵花”在附近出没。“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姐姐,要是真听见了,他们才不管你是圣者的人呢。”
阿玛刻挑挑眉。“所以我倒喜欢早晨那小姑娘,至少她说话棱角分明。好啦,陪我四处走走,你不希望我被这石头笼子闷死吧?”
云缇亚促狭地笑起来。仿佛又回到儿时,他们在开满山萝花的原野上追逐奔跑,然而四面的风汹涌如潮,刮散了彼此的呼喊声。“请留步,两位。”一个风一样冷冽的声音迎面唤道。
阿玛刻注视着那人,眼睛因他意料之外的出现而点起了惊喜的光芒。他是个颀长优雅的男子,身穿镶银线的黑衣,面孔就像用整块的淡色珊瑚雕成,下刀滑润,别无瑕疵,但在云缇亚眼中,那实在是一张面目可憎的脸。它如同真正的塑像一般,僵硬冷漠,纵使台柱坍塌,基座碎裂,灰尘盖顶,血污溅身,它依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那是一个久谙世事的参谋所独有的脸。
“……珀萨大人,”云缇亚听见自己从牙缝中挤出这个名字,“您也来了?在依森堡呆得很无趣吧?”
珀萨并不理会他。“我有军情要禀报圣者。侍卫说,他和你们俩在永昼宫参加宴会。”
“圣者正与教皇猊下单独会面,可能要稍等片刻。”阿玛刻笑意盈然,“我带你先过去。”
参谋公事公办地点点头,随她离开。云缇亚回头望着贝鲁恒最信赖的左右手与阿玛刻并肩而行的背影,直到它们完全被永昼宫庞大的影子吞噬,这才转过身,缓步走远。夜幕已经完全降下,如轻纱覆在他双肩,却感觉异常沉重。
他向人影稀疏处走去。灰衣的祈誓者们点亮了石头街道旁一列列灯柱,一群人排着整齐的队从它们眼前跑过。那些“葵花”总以为自己是不穿甲的军人,他们严格遵守着军人的组织纪律,好像自己真有一天能代替圣裁军冲上圣战的沙场。“主父只是暂时离开,”一个瘦得像被挂起来风干了好几年的红发老头在诗颂大道的广场上发表演说,“等有了足够的虔诚作为祭品,他自然会回到我们身边。”葵花们为首领鼓掌迎合,几个年幼的茹丹孩童却不识趣地追逐一只夜光蝶,撞进了大人的队伍中,母亲连忙将他们拉开,但演讲尾声的针锋仍然刺到了这些傲慢无礼的异族蛮子身上。“听说舍阑人养了一种鸡,它们的毛色纯白,可一根根拔下来再看,皮肤竟然是黑的。它的骨头,血肉,油脂,肝肠……都是黑的,把它们腔子剖开,心脏就像一块完全烧透的木炭。”
“哎哟,导师!这我可不明白了。”底下的人冲干瘦老头喊道,“只听说舍阑人养马用来骑,养羊用来吃,养大象用来打仗。他们养鸡这种弱不禁风的可怜东西干嘛?”
“弱不禁风?你想错了,”导师大声回答,“那鸡能斗,能啄人,它们也什么都能吃,除了不吃鱼!”
葵花们轰地大笑起来。他们之中的茹丹人低头沉默,一言不发。云缇亚站在黑暗中,对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甚至感受不到愤怒。这片大陆的居民憎恶茹丹人,他们一直认为是这个流亡民族将噩梦般的舍阑军队引到了自己的土地。太多的茹丹人在失去家园和血亲后反沦为征服者的帮凶,远远超过接受教皇国庇护并皈依辉光教的人数,而即便是后者,也依然顽固地用传统和积习将自己与西方人加以区分。这本来就是不足为奇的一件事。哥珊容不下与它面貌相异的人。
“……一个人出来散散心吗?”他忽然问。
白衣黑发的女子坐在灯柱下,用手中的鱼骨轻轻梳理大狗的颈毛。“您好像很寂寞啊,大人。”她笑了,灯光为她的盲眼覆上一层阴影。
“我八岁那年跟着母亲来到这个城市,”云缇亚低声说,“我的母亲爱上一位圣徒,希望得到他的拯救。不久,她被人残酷地杀害,谁也救不了她,而我那时就在近前,眼睁睁看着她血流满地。”脸上的烙印开始灼烧发烫,然而他的言语冰冷。“尽管我对凶手恨之入骨,却没有为她复仇的力量。她选择用这座城作为她的坟墓,我无能为力。”
爱丝璀德缓缓站起来,纤白的手伸向黑暗,摸索到了他的手腕。“既然无力,”她说,“何须内疚?”
“你不会明白。”云缇亚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多喝了几杯,为什么会突然跟她提起这些,但令他最悲哀的是,自己在说到母亲时心里已不再有任何波动,“在哥珊,无力是最大的一种罪恶。”
风从街道彼端吹来。萤火低低长啸,双眸却静默如星光。
两人沉默地同向而行,又或许只是恰巧,彼此的散步都漫无目的。最终海岸阻断了去路。茹丹人厌恶海,他们对故土有着极为倔强的眷恋,而海往往意味着迁徙。他们甚至厌恶贝壳装饰,拒绝使用从鲸精香与砗磲中提取的银色染料,但舍阑人还是强迫他们渡过这广阔得令人绝望的水域,踏上连一块石头也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即便在这里改变了信仰,他们仍旧对海退避三舍,哪怕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