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处长-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眼睛,瞟一瞟远处空寂的凉亭。虽然人显得很笨拙,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蛮大的气力。原来粉嫩红润的小脸,也变得苍白了,有几颗细细小小的雀斑,很美丽地洒在小巧的鼻梁上。
镇长自然极高兴。就要为人之父了,心头窃窃的有份激动。想想也的确不容易,快四十的人了,讨了三个婆娘,才在小媳妇肚子里怀上这么一个。要不是美女岩,恐怕……
想到此处,镇长脸上就有了一份不自在。
临产期到了。镇长买了两挂长鞭子,杀了家里最跳壮的母鸡,然后请来镇上最有名的接生婆,静候着小媳妇生下孩子。
可小媳妇却没法将肚子里那坨肉生下来。
她双手反背着,紧紧抓住床架,使出了平生的力气。为了憋住劲,她咬紧嘴唇,倔强地不肯哼出一声。开始自然挺过来了,到了后来,身上的劲越来越小,那小脸因用力过大,变得扭曲了。再后来,小媳妇就绝望地合上了眼睛。同时松开那被咬得稀烂的嘴唇,想哼几声,可喉咙里已无法送出清晰的声音,只有干瘪瘪的咕噜声,自牙缝间艰难地挤出来。
接生婆无计可施,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在房里团团打转。镇长慌了,没别的办法,只得听从旁人的计策,赶忙派手下人去镇上请来仙师,在堂屋里折腾了个够。
就这么捱过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小媳妇就那么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一直没能生下肚子里的生命。
此时,大约是夜灯初上的时分吧,窗外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那又是从镇外凉亭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又真真切切;缥缥缈缈,又实实在在。
那是箫声。
整个镇子突然间就静止下来,黄昏留存下来的一切喧闹和嘈杂,一下子全都隐匿起来,仿佛要腾出一片悠远的空间,好让人们用心灵去接纳这份久违的,曾是那么熟悉而又投缘的声音。
不过,镇上人却感觉出,这箫声分明与从前有了别样的意味。不再黯淡,不再哀怨,更多的是流畅,是明丽,是豪迈和崇高。那从容的倾诉里,潇洒地流淌着一份激越;那殷切的呼唤里,恣肆地汹涌着一种自信,一种生命的骚动。
小媳妇微微启开了那双沉重的眼皮。她听见,不,是看见了那个彩色的声音,在她那生与死的神秘空间闪耀着,迸射着。她死灰的目光深处爆出两颗灼灼的火花。她全身的血管都张开了,她生命的、精神的力量全部集中于万劫的两腿之根了,她最后一个挣扎,那声憋得就要窒息的新鲜的哭声,便陡地落入尘世。
这哭声,刚好接上那嘎然而止的箫声。
同时嘎然而止的,还有小媳妇那曾经非常绚丽的生命。
镇上人此后再没听到过那箫声。
却不明白,到底是小媳妇带走了那箫声,还是箫声带走了小媳妇。
不过,镇上人再不会将那箫声忘记。此后的岁月里,他们经常能在镇长儿子脸上,依稀读出箫声的影子。
依傍着悠悠雄河的半边街,铺满方方正正、厚厚实实的青石板,一页一页,嵌连着,拼缀着,宛若一部拙朴而又深沉、古旧而又幽婉的历史。
贝子公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些青石板。贝子公祖上曾显赫过,据说还出了一位举人。半边街的青石板就是贝子公祖上中举时,为光耀门庭和行善积德砌就的,至今,半边街人娓娓道来,仍然那么入耳中听。只是到了贝子公上面两辈,才渐渐破落下来,轮到贝子公,便只有当清道夫的份了,每日挥舞着大扫帚,在街上不倦地清扫。
解放前夕,贝子公以其清道夫的便利,掩护过几个从雄河对岸渡过来的剿匪队员。还提着高耳瓷罐筛了谷雨茶给他们喝。那个高个子队长站在街边的青石板上,一连喝了两大碗哩。接着半边街就解放了,高个子队长要贝子公当半边街的镇长,他忙摆手,说自己不是当官的相,还是留下来,像从前那样扫扫半边街的青石板。贝子公于是仅仅换了个清洁工的小头衔,照旧拿着那把竹扎的大扫帚,自街头扫至街尾,再自街尾扫到街头,像写一行永远也写不完的大字,一写就是几十年。几十年,这些青石板沾着阳光或濡着雨雾,白天晃着他闪亮的瞳子,夜晚荡着他甜美的睡梦,让他觉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亲切几分。
忽然有一天,有人向贝子公走过去,要接过他手上那把大扫帚。他该退休了。贝子公当然很不情愿。他将脑壳别一边,瞟了瞟街外的雄河。雄河可作证,它记录着贝子公为半边街辛辛苦苦劳作的影子。但贝子公知道,不交出这把大扫帚是不行的,镇上事先已通知了他。他的目光从雄河上收回来停在脚边的青石板上时,眼睛兀地就模糊了。
这块青石板,就是高个子队长喝贝子公的谷雨茶时站过的。
好在贝子公的家就在半边街,虽然不拿那把大扫帚了,但每天开了家门,仍能与这些紧紧拼连着的青石板晤面。此时贝子公的心情就会熨贴一些,交出大扫帚时心中那种难受的酸楚,便要轻淡许多。
然而,雨雪风霜的浸蚀,再加上近几年各类车子的增多,街上的青石板开始破损了。有些青石板昨天还是上好的,那么平平整整,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发现裂开了一条缝隙。再过三五天,经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拖拉机和大卡车一糟蹋,便彻底地开了裂,变得身首各异。这几年,半边街突然兴起修建私宅的风气,一些缺德鬼还趁夜撬开破裂的青石板,搬去作宅基。好端端的一条街面,于是像得过疮疥一般,东一个眼,西一个洞,坑坑洼洼,不成体统。
贝子公的眼泪就往肚里流。一块青石板就是他身上的一块肉,他被剜得痛苦不堪。他弓着背去镇上跑了两趟,要镇上请石匠将街面维修一番,并惩办那些撬青石板的缺德鬼。镇办秘书倒是非常殷勤,又倒茶又敬烟,还用小本子将贝子公的意见一一记下,说镇长一有空,就向他详细汇报。可贝子公走后,却一直未见镇上有任何行动,青石板仍在一天天破裂,一天天减少。
贝子公又去镇上跑了几趟,终是无效。
这晚上贝子公失眠了。一辈子还是头一次失眠。因为伤心,也因为愤慨。他辗转反侧,就那么眼睁睁望着下弦月悄然爬上窗棂,又慢慢消失于灰蒙蒙的屋檐角。这时,一样清脆轻盈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以往的夜晚,怎么却没听见过这美妙声音呢?原来这声音虽然清脆,却十分细小,丁丁冬冬,仿佛针尖掉在石板上,不是夜深人静之时,是无法让人感觉得到的。贝子公的心里,竟因此生出几分兴奋,几分喜悦,刚才的愤懑消失了许多。这声音的确太生动,太动人了。贝子公就枕着这轻悄悄的丁冬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贝子公就起了床,颤巍巍拿着铁桶,去接昨晚那个声音。那是一眼细细脉脉、清清亮亮的泉水,自贝子公屋后的岩壁上垂挂下来,悠悠然滴在岩壁脚底的石槽上。这泉水甘纯甜美,细腻清润,贝子公喝了一辈子,人也因此健旺精神,清爽醇厚。对啦,四十多年前,贝子公给剿匪队喝的谷雨茶,就是这泉水泡的,那位高个子队长还一抹嘴巴,边咂舌头边说,喝了这样的上等泉水,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口渴了。
铁桶很快就接满了,贝子公弯腰提起来,进了茶堂屋。水烧开之后,先上满两个开水壶,余下的,倒入早准备好的高耳瓷罐,趁热泡上茶。饭后,旭日自东边升起,那阳光潋潋滟滟,洒在半边街上,贝子公已在自家门前端端正正摆上一张桌子,以及数把竹椅。桌子上除了开水壶和高耳瓷罐,还有七八只绛紫色的陶瓷小杯,外加一个盛满茶叶的竹筒。贝子公的茶摊就这么开张了。
还不到十分钟,贝子公设摊司茶的事就不胫而走,传遍整个半边街。好似出了桃色新闻,大家觉得既新奇而又有趣。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司茶行善的老一套?当然,从前不同,从前半边街哪个家里添了喜,或是儿子中了秀才,当了官什么的,往往会在桥头亭间,或岔道口街巷旁摆设茶摊,无偿供应过路人,以行善积德,保佑家人平步青云,福如东海。也有些是平生造了孽,摆茶摊消人干渴,而免除自己灾难的。半边街曾出过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子,却不幸沦落烟尘,到了晚年,她为了洗净自己的龌龊,在街旁孜孜地司茶三年,终于赎回声誉,百年归世后,半边街人为扬其美德,给她做了三夜轰轰烈烈的道场。只是后来,这种司茶行善的事被当做四旧,挨了批判,在半边街销声匿迹了。而今,贝子公的儿媳在城里当了工人,有吃有穿,用不着他祝福庇荫;他自己没病没痛,健健旺旺,也不需要赎罪消灾,却突然摆起茶摊,要行善积德,好像扫了大半辈子街还很不够一样,岂不有点怪异?
贝子公才不在乎这些哩,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一双老眼熠熠生辉,饱含了笑意,迎接着上前喝茶的客人。客人受到感染,在竹椅上落了座,茶未入口,心内已舒泰三分。贝子公问明了是要热茶还是冷茶,要冷茶就筛那高耳瓷罐,清晨上就的茶水刚凉;要热茶,则先拿过精致的小竹筒,在陶瓷小杯里倾了茶叶,再去倒开水壶里的热开水。无论冷茶还是热茶,味道都那么浓酽且纯正,谁喝过谁称善不已。
岂料喝茶人刚放下杯子,欲拍了屁股抽身离去,贝子公却冷不丁伸出一只布满厚茧的苍老的大手,说道:“五分钱一杯。”
茶客中,有些是见过外面的大世的,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老人孩子摆设茶摊,一毛二毛一杯地卖给顾客,已不鲜见,故马上自身上掏出零钱交给贝子公,微笑着道声再见,离开茶摊。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本地茶客,以为贝子公是在开玩笑,竟犹犹豫豫立于桌旁,未知该不该去身上掏钱。但见贝子公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温和慈祥的笑意中,分明深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茶客心想,这茶实属茶中上品,平时很难喝得到,五分钱一杯,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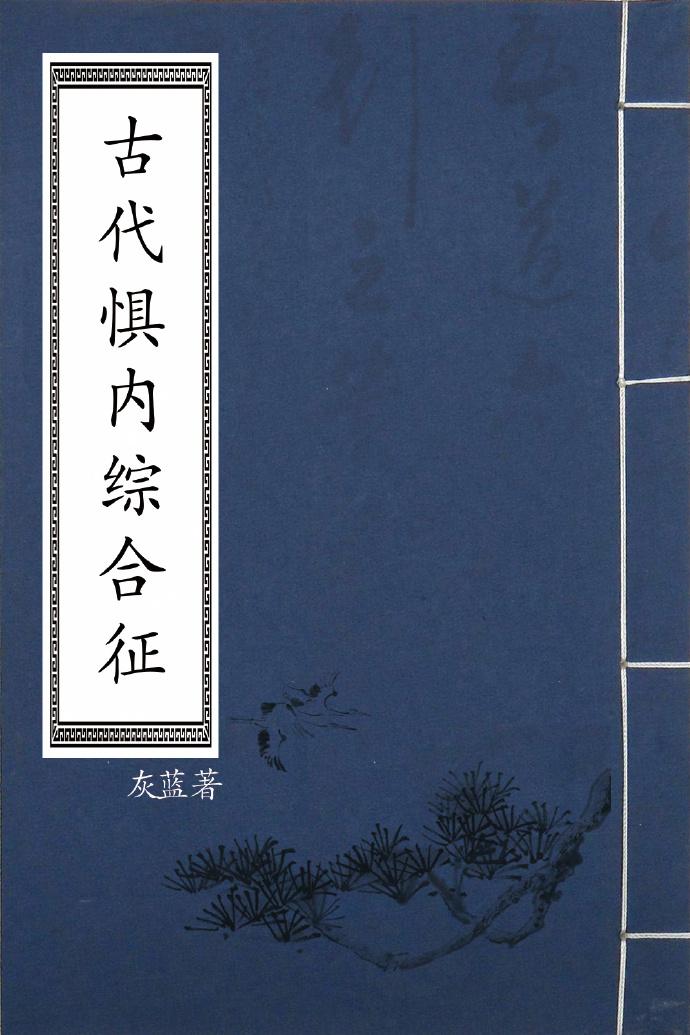

![[综合]转世千载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90/90982.jpg)

![(综同人)[综合]攻略之神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98/985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