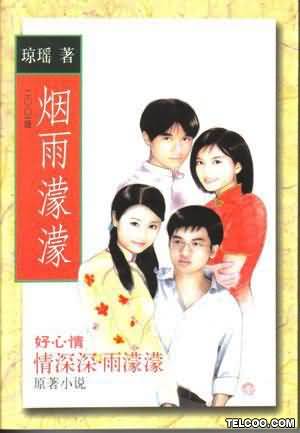烟雨凤凰-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是我
带着你刺的伤茁壮成长
——写于1998年冬至
最初的梦想
无可掩饰,也无法逃避,岁月的车轮像柔软而尖锐的刷子,那么不经意的,缓缓拂过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与面容。这么多年,从懵懂走向明了,从彷徨走向从容,从期盼走向拥有,从拥有走进淡然。
去北京,我的梦想并不是继续做一个舞蹈演员。而是希望能独立的站在舞台上成为一个歌者。让身边的家人朋友费解的是三岁开始钟情跳舞的我,怎么突然间想要去唱歌了呢!在我十四五岁时,虽然还没有真正恋爱失恋过,但每当我听到流行歌里那些凄凄绕绕的思念与离别的情愫时我觉得我都懂得。对我而言,舞是跳一个“美”字,而歌则是唱一个“悲”字。三岁的我懂得了美便爱上了跳舞,当十四岁的我懵懂的懂得了悲,便又爱上了唱歌。但在歌唱技巧上还尚未成熟的我,必须先作为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的身份才有机会留在北京。
当时,对于我和周围的人都觉得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因为那时候的我在湖南省里和基地部队时不光已是领舞独舞演员,而且还为部队及地方各大晚会做舞蹈编排。来北京前十七岁的我还刚刚为部队独立编排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舞剧。着武装,淡红妆,十七岁的少尉女军官自然走在哪里都会成为焦点。从十五六岁不小心长成大姑娘后,就常会听到对我的各种赞誉。“这么小的女军官啊”,“长得多漂亮啊”,“她的舞跳的最好了”,“腿真长”……但是没人能想得到这样的姑娘家就没有男生追求。因为姑娘十四岁当班长,十六岁当排长,管理的整个舞蹈队近二十人几乎个个都比我年龄大。但军令如山倒,队员们在业务和日常生活上都得听我这个小排长的。所以在大伙眼里优秀的我直到来到全中国的优秀人才都聚集的北京,也并不生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自信,有天赋,能吃苦。而且需要遇见强者来刺激让我变得更强。长期在一座山头赛跑,不管是跑在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我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要去一个新的环境了我兴奋!拭目以待吧,我很快就会独自站在舞台上,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静凝听我的歌声。
信心满满蹦蹦跳跳的我,似乎后脚还留在湘西溪水里的青石板上,前脚已踏进钢铁丛林中的立交桥上,从傍晚江河边静逸安详的吊脚楼纸窗里透出的幽兰烛火,到高悬在摩天大楼上五颜六色夺目的霓虹灯,眼前漫天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这视觉影像带给一个土家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在祖辈口中言传的,儿时黑白电视中所看到的,我心目中永远闪耀着光芒的北京站到了!
新团体的早晨,所有的舞蹈演员每天都聚齐要到一个巨大敞亮的排练厅里上集训课。哪里的排练厅都一样,有着整面墙的大落地镜子,但这里不同的是有一个剧场大小的舞台与排练厅连在一起,便于成型的作品在这舞台上进行彩排录像。我记得那个早晨来到这里第一次见到那群女孩时的情景,上集训课的女孩们穿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练功服围绕着排练厅的把杆标准的用芭蕾步站立着,晨光从窗外洒在刚擦得发亮的木地板上,一个女孩弹着舒伯特的一首钢琴曲,女孩们随着音乐的变化流畅整齐的伸拉着腰腿。她们每个人的样子就像是站在阳光丛林中修长而高贵的小鹿。画面美极了。她们美极了。当时我真不忍心进入这样的画面里面,生怕自己会打眼破前的意境。我的身高在南方算是偏高的,站在这北方的女舞蹈演员的队伍里充其量我也就算个中等个子。而且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两年正处于发育阶段的身体突然超规范的生长。脸蛋、胸部、屁股、大腿和胳膊处处都如同裹不住的奶酪。以专业舞蹈演员的标准来说我算是一个小胖子。
眼前的这些女孩都出自中国舞蹈界的最高的学府,习舞七八年的本科毕业高材生。我专业习舞的时间连她们一半都未满,而且还是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艺术学校。我的这点功夫上她们的课等于一个中学生在啃大学的课本。就算悟性再好的人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够跟的上的!于是,每天晚上我都会自己跑去排练厅补习白天所学的功课。虽然我清楚自己志不在此,但既然我被借调来到这儿,就不能太丢人,呆一天就有一天的样子,我必须要进步先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长期的被留下来,我才有去当歌手的机会。舞蹈集训课上跟别人有差距,但我有打不死的蟑螂精神。
与过去在湖南不同了,来到这里参与的舞蹈剧目里我从领舞排在了队形中最后最边角的位置。记得有一支叫《春色满园》的集体舞蹈,每个演员手中拿着两把大粉红扇子代表着花瓣,过程中演员用肢体及扇子表现出春天里开出的各种花朵的形态,时而几人把扇子拼在一起变成大大小小的花朵,时而演员们接龙在一起随音乐起伏滚出满台花瓣翻涌的波浪。我的任务是当舞蹈中某一朵花需要花瓣更密茂时,我便拿着扇子从台口冲上舞台摆一个姿态添补空缺,换队形继续舞蹈时我再冲下舞台,等到接龙时我便再冲上舞台补充滚浪的人数,滚完浪我又再冲下舞台等候,最后一个造型是所有演员围成里外两圈用身体和扇子拼成一朵巨大的牡丹,人数越多越壮观,我便再次出场冲进演员中完成春色满园的角落里那一小片花瓣。五分钟的舞蹈我共分三次上下场,坐在最边侧有观众还猜想这个舞蹈演员来来回回的到底是裙带松了呢还是鞋带开了!我能很清晰的记得当时无论是做远处背景中的花朵,还是接龙滚浪,到最后摆出大合影般一个微笑的姿势,这每一次的上台,下场,站立转身我都洋溢着饱满的感情,这并不因为什么道理和觉悟,只是因为我只要一站在这舞台上,音乐和灯光一洒落在我的身上便让我肃然起敬,甚至每一个呼吸及抬眼闭眼的过程都让我陶醉,站在最前面或最后面,舞动五分钟或者五秒钟,都一样。这一次我才认识到,我是真爱这舞台啊!我和曾在湖南共事的人们都没想到,来到北京再也不是最专业,最优秀,最美貌的我成为了舞台上一个跑龙套的舞蹈演员。作为一个这样的群舞演员我并没有丝毫的不高兴,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比过去更好,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新鲜的事物与人。如今我在这里要从头开始从小做起。忘记从前的光环重新出发。我会成为全北京跑龙套的舞蹈演员中最出彩的。只要是在舞台上,无论怎样,我都很快乐。
梦的背面
舞台上体验的是生命直达到灵魂。舞台下体验的是生活直达你的心灵。在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空间,到底哪一个更真实永久……
初来乍到,我兴奋,像在家乡那样地与身边每个新面孔打招呼:“你好,我叫阿朵。我从湖南湘西来。你知道湘西吗?你从哪里来?”
很快,我发现我来到的这个新环境新团体,似乎并不习惯这般热情的打招呼,不习惯与不够熟悉的人亲近。就彷佛新环境里有很多人穿的并非柔软的布衣,而是金属做的,可防身的盔甲。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北京,是一个能看见梦想的地方,也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有一个女舞蹈演员患了腹泻,在排练结束后大声问排练厅里所有人是否有止泻药,在场的人都说没有。我想起妈妈给我带的一种叫土霉素的止泻药,于是拿着药敲响了她的宿舍门。她把门开了一条缝问我来干嘛。“给你药,你不是拉肚子吗”我说。她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迅速接过我手里的药瓶,随即便扣死了门,没有表情,没有言语。
我怔怔地站在门口,心里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晚上,我到公用电话亭给妈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在新的团体里生活得很好,新伙伴们都很喜欢我,帮助我。说着说着,我突然想家。眼泪流了下来,流进了嗓子里。我说慌了,我说的只是我所希望的。
来到陌生环境的我需要朋友,我曾很多次想让自己做的更好,让新团体里这些优秀而漂亮的女孩们喜欢我,我的热情主动,我所有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我想跟她们成为朋友。
过了两三个月,我仍然像刚来那样一个人在食堂吃饭,一个人上街,一个人去排练厅练功。渐渐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从这群女孩的“言谈举止”中得出了不与我靠近的结论:她来自小镇;她不是科班出身,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也不是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她爱出风头,跳群体舞的时候总想表现得与众不同;她过于陶醉于自己的表演的状态中;她不知道这些名牌;她过于丰满的身体对于舞蹈演员来讲是种耻辱;她的热情有企图;她对男人的笑很风骚……这些话语从舞台的侧幕条边,上场前的服装更衣间,就寝前的洗漱间,和女生公用洗澡堂里传入我的耳朵。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被别人否定的声音。我不解,心中百味翻滚。我感到委屈,却又不知该怎么做,我没有打电话回家,因为我不想说慌。于是连着好几天一天黑我便躲在被子里流眼泪。与我同寝室的“梦”是新来的,跟我几乎同一时期进到这个新团体。她发现我不像之前那么爱说爱笑了,难过的我把疑虑告诉了她,梦说她也听到过关于我的这些言论,但并非只有我一人被女孩们这样议论。她安慰我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才会说这些话。听了梦这么一说,我困惑的是当一个人不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又为何要如此否定别人并将其拒之千里外。我不喜欢这样!
一次排练后回宿舍的走廊上,我遇见那几个女孩端着脸盆有说有笑迎面走来,走廊狭窄,当我与她们擦身而过时,她们停止了说笑,离我最近的那个女孩撞着我的肩膀同时,她眼角向我投射出了一丝不屑的眼光。当我走过了转角,走廊突然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爆笑。回头只看空空的走廊。那笑声为何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被带回到在湘西上小学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