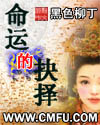抉择-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作者很会设置“纠葛”。这本书能让读者有兴趣急切地读完它,是因为它里面布下许多“纠葛”。是这些“纠葛”组成通篇的网状的生活长卷。每一个“纠葛”都是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一堆事与另一堆事的矛盾,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矛盾。这些矛盾分布得越多越广,解决得越久越难,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起一怎样解决”矛盾的情绪也就越强烈。当然,蕴含于矛盾之中的内涵应该有意义。这样,当作者每解决一个纠葛,才能令读者获得对社会对人生的某些感悟。如果这种感悟是多层面的,那么,读者自然就会感到长篇小说独特的审美情趣,而这是区别于中、短篇的。《抉择》网结了许多矛盾,构成了书中全部生活的流程。开始,工人要“闹事”,控告厂领导腐败,谁是谁非;李高成开始觉得工人有理,但觉得干部也情有可原,听谁的;李高成的妻子为什么要阻止他开始调查中纺,而他的领导严阵为什么也干预他;杨成的提醒究竟是何用意;“特高特”突然甩来30万元,与他即将开始的中纺调查有何联系;甚至省委的态度究竟如何都构成了全书的“纠葛”。这些“纠葛”的解决,都是读者渴望得到答案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获得的,并且通过作家对这些矛盾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有力的把握与处理,读者正是随着这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从中获得对以上我们分析过的作品社会内涵与人生内涵的参悟。
(二)依靠情节的力量。过去我们对情节的理解较多地强调了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而常常忽略了它本身就有推动故事发展的需要。张平显然深知其理。他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性,帮助了刻划主要人物李高成性格的复杂性,揭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的。《抉择》的情节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而对工人“闹事”,李高成要调查,妻子警告,严阵把电话打到党委常委会上,也是警告。李高成终于下决心派出调查组,妻子却为他收下30万元的红利,他仍执意要调查,就又有严阵的电话警告,和他妻子收下30万元红利时做了手脚的录音带,造成他接受贿赂的假象,又有结果没有问题的假调查报告,而且处理中纺的权力仍掌握在严阵手里,待到李高成仍没有退缩之意时,中纺突然宣布要“破产”,直至省委终于采取断然措施一举收审了腐败分子,全书的情节波澜方才靠“突转”的手法最后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高潮后又跌宕一笔,成了人民保卫李高成之举,用来检验省委的反腐败是真是假,似乎有些画蛇添足之感)。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情节是波连波,浪赶浪,然而却是看前波不知后波,知晓了前浪却不知晓后浪,这种神秘感就使故事本身富有了生动性和丰富性,使得读者的心绪富有波澜。《抉择》如果没有这些情节骨架的支撑,所有的生活场面以及所有世态与心态的描写也就失去了依附,难以构成现在比较完整的宏篇。
(三)悬念的运用。“悬念”是建立在对文学接受者的心理特征把握上的,也是叙事文学的一种艺术经验。张平在《抉择》中运用了“悬念”的技巧,只不过这种运用不像古代小说那样,可以脱离开规定情景和人物行动而纯属“卖关子”的形式主义作法,而是将它融汇于人物命运和事态发展中。比如,中纺领导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么会这样快就集体腐败了呢?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上面还有什么人是他们的后台?李高成调查中纺的工作步骤,为什么严阵了如指掌,总在他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制约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吴爱珍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情节发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际遇命运与性格发展出现的悬念中。这些悬念是作者在叙述中运用的戏剧法的悬念技巧,这些技巧在读者心理制造了疑团、期待的阅读效果,也是作者编织故事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我们进行了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之后,我以为还不要忘记了张平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主观的介入。如果从审美风范上说,小说分倚重客观与倚重主观两大类的话,那么,张平属于后者。他的小说中,作者主观介入的程度是少见的。主要表现在他的主人公从始至终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一是在理性观照下进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扩大了思维空间,突出了作品的题旨;二是许多段落的内心独白,简直就是主人公的灵魂拷问,不仅增强了主题的深度,增强了对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强了这一形象对读者心灵的艺术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发挥这一长处时,亦有“过度”之处,这就带来较多的内容重复,显出冗赘之弊。这些都会破坏艺术的表现力。我以为,这值得作者再细细运思一番。
一曲反腐败斗争的嘹亮战歌——代序
严昭柱
继《天网》、《孤儿泪》之后,张平又推出了他的新作、长篇小说《抉择》,生动地描写了国有大型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一场惊心动魄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读完《抉择》,我认为,它不但是近两年来直面社会矛盾、反映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新潮中的一部佳作,而且它在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的努力和实绩,可能会把反腐败斗争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表现反腐败斗争,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难点。说到底,难就难在作家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根源、本质和前景。在创作实践中,这个难点常常对作家敢不敢揭示现实矛盾、展现激烈而复杂的反腐败斗争,通过艺术表现能不能鼓舞群众和干部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构成一种认真的考验和挑战。事实上,这类题材的作品有一些是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但其整体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们往往揭露腐败现象较为充分,而描写反腐败的斗争方面却相当薄弱,有的作品主人公还不得不无奈而痛苦地与腐败现象暂时妥协。诚然,揭露也就是一种鞭挞,痛苦无奈地暂时妥协也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控诉和抗议。这比起那些对于腐败现象不愤恨、不控诉、不触及,却沉溺于自恋等所谓“私人化写作”,甚至欣赏和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品来,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对于腐败止于揭露、止于抗议,又是不够的。我们的作家应该更加热情地去反映和汇歌我们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才能为主人公提供更深远的背景、更广阔的舞台、更激烈的冲突,一句话,提供我们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典型环境,才能真实地再现代表时代发展趋势、前进方向的典型人物,鼓舞干部、群众把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和夺取更大胜利。
张平的《抉择》,不但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而充分的揭露,而且对反腐败斗争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展现,在对环境的典型化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在反腐败斗争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突破。
《抉择》直面现实矛盾,对腐败现象的揭露是尖锐的,同时又是深刻的。它所描写的中纺集团公司的腐败现象,可以说触目惊心。它不是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而是公司整个领导班子都烂掉了;它不仅是这个班子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而且有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充当后台;他们把一个两万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搞到濒临破产,而他们光间接送给严阵的贿赂款就达几百万元,后来在严阵的内弟钞万山家里就搜出人民币130多万元、港币20多万元、美元近10万、8千克金条、数百万元存款、大量首饰珠宝和11套房产证!或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作者把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班子写得如此腐败,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它的典型性?难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吗?如果可以代表,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吗?这种疑问,其实包含着对于典型的一种流行的误解。简明地说,典型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都既有个别性,又有普遍性。中纺集团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就既是“这一个”,而又有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不应该误解为仅仅是量的规定性,而应该理解为主要是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不应该要求作者笔下的中纺班子成为现有的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洁或腐败的平均数。这种要求之所以不适当,因为它必然会否定文学形象应有的个别性,也就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而且,这种要求也不合乎人们文学欣赏的实际经验。实际上,通过中纺班子的文学形象,人们并不是获得所有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廉政状况的统计值,而是引发和深化了对于腐败的根源、实质和危害的认识和思考,是激发和强化了对于腐败的憎恨和反腐败的决心及勇气,这些,恰恰是这一文学形象的质的普遍性。因此,中纺领导集体严重腐败这一文学形象的典型性,主要应该从它所概括的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质来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可以说,中纺班子集体腐败这一文学形象概括了相当丰富的现实内容。譬如说,它概括了一些腐败分子“发国难财”的丑恶罪行:国家年年向中纺贷款,但是,“贷得越多,亏得就越多!为什么?这些亏损究竟是怎么亏出来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规律,太让人深思了”。而事实是,例如1994年国家贷给中纺公司8千万元,公司领导却从中拿出2千万元办了一个“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个实体,这些实体的经理和负责人,几乎全是他们的子女和亲信。结果中纺公司是停工停产了,而那些派生出来的小厂小企业小公司,一个个红火得不得了——“许许多多的腐败分子,正是在亏损企业的招牌下,大捞特捞,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