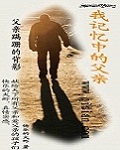父亲进城-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直拖着。
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知道躲是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父亲在床上和母亲反复商量研究决定,向亲家求救。
父亲终于要通了亲家的电话,亲家一如既往的热络。亲家甚至在电话中怪罪父母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自己打电话,还说要找个时间老哥俩要小酌一次,畅叙一下心曲。父亲被亲家的真诚感动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而感到脸红。在这种真诚的气氛之中,父亲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在不远的地方闪烁着。父亲和亲家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终于说到了守备区和自己的命运,亲家果然直言不讳地说:裁军这是军委定下的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听从党的安排吧……
父亲听到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刚开始那点热乎劲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还是委婉地把自己的心愿说给亲家听。这引起了亲家强烈的共鸣,其实亲家的心愿是和父亲一样的,他们何尝不想就这么一路风光地干下去呢?就这样,父亲和亲家在电话里沟通了两个小时,才放下电话。放下电话的父亲冷静了下来,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亲家也在被“裁”之列,也就是说身为军区副司令的亲家也已是自身难保了。他又想到了,亲家在电话里说过的话:咱们都找一找吧,分别跟领导谈谈,也许有希望,但估计用处不大……
父亲想起亲家这前后矛盾的话,彻底失去了信心和斗志。那一刻,父亲似乎老了十几岁。但他不想就这样失败,他要努力,他还要争取。那些日子,父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频繁地向军区各位领导家打电话,父亲动用了这么多年所有的关系,他想起了战友,想起了同乡,想起了对自己不错的领导……父亲给这些人打电话时是低声下气的,可怜巴巴的。父亲说:首长,我小石还小呢,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我是还可以干一番的……
那一年,父亲五十六岁。五十六岁的父亲在说自己还小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壮感。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听着,听得她也眼泪汪汪。
父亲又说:老张,看在咱们十几年交情的分上关照一下吧。我并不大,才五十六岁,还小呢……
父亲还说:老首长,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我还小呢……
那些日子,父亲绝望得要死要活。他时常在办公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到办公楼的最顶层,凝望着营区。看着那里熟悉的一草一木,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凉,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父亲想什么呢?没有人能说得清。
母亲独自守在家里,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空空落落的房间,心里充盈着前所未有的荒凉和忧伤。她已经没有心情更没有良好的状态出入家门了,即便出门她还能找到昔日良好的感觉么?茶几旁那叠报纸已落满了灰尘。家里已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报纸是自然不需要看了。一个人在家,看那些报纸给谁看?寂寞忧伤的母亲回想起这个家昔日的辉煌。
大约从父亲当上团长那一年开始,老家的人已经把父亲看成是很大的一个“官”了。这在老家频频来人的次数中可见端倪。来人初始于母亲的老家,其实母亲老家没有什么亲人了,自从母亲在逃难的路上和家人走散以后,便再没有下落了。父亲把母亲从小村接走后,曾专门为寻找亲人,两人双双回过一次“家”,仍然没有找到母亲亲人的下落。可以想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人不是饿死了就是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母亲对寻找自己的亲人失去了信心。起初的日子,她还曾为亲人的下场伤心地哭泣,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地淡忘了。
父亲十三岁离家参军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父亲的父母——那两个赌徒他没有什么眷恋的,父亲已料定了他们的结局,不是死在赌桌上,就是饿死在千疮百孔的小屋里。令父亲伤心落泪的仍然是妹妹,他一想起老家,首先想到的是妹妹被冻死时的样子。妹妹在雪地里举着一双小手,眼睛望着远方。父亲一想起这个场面,恍惚间觉得妹妹在呼唤他,等着他去救她,父亲想起这些,心就被刀戳了似的痛。父亲恨自己的父母,由父母扩展到恨自己的家乡。他离开家乡后,便铁了心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好长时间,父亲和家乡断了往来。
母亲却和自己的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母亲一个人等待父亲的日子里,她得到过无数小村人的接济照料,这一点她没有忘,父亲也没忘。因此,母亲有理由和家乡人来往。终于,村人们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找到了母亲的门下。因时间久远,母亲对那些乡亲的面容已经淡忘了,但熟悉的乡音,使母亲很快便和乡亲们亲热起来。乡亲来的不是一人,而是一伙,他们在家里住下来。他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知道母亲嫁给了一个“官”,作为接济过母亲的村人便有理由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他们久居乡下,对城市早就有了一种仰慕和神秘感,他们起初把母亲当成了沟通城市的桥。
那时,刚刚过去困难时期,父亲只是个团长,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住房也紧张。来的人之中,有男乡人也有女乡人,他们是搭帮结伴来的。因此,住宿便成了问题。最后,父亲带着权和男乡人们住在一间房里,母亲带着敏和女乡人们住在一起。那些日子,家里热闹而又混乱。乡人们大声地讲话,大声地吐痰,大声地在厕所里大小便,一副鸡犬不宁的样子。白天的时候,父亲去上班,母亲打发走敏和权去上学之后,便带领男乡人女乡人们去逛街。城市永远都对农村人有着一种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在母亲的引领下如饥似渴地在城市里漫游着。采购是谈不上的,他们的腰包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他们来到这里是来看望城市的。出发前,母亲已把干粮备下了,带着馒头和咸鸡蛋,馒头是母亲自己做的,咸蛋是母亲腌的。一直到傍晚时分,乡人们在母亲的引领下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回来。一进门,村人们便一屁股坐在地下了(凳子不够用),母亲还要为一家人和乡人们准备晚饭。母亲在做饭的过程中,乡人们抽了支烟,又喝完了一壶茶之后,精神慢慢地回转过来。然后他们兴奋地议论城里的一切,像坐在田间地头议论收成似的。
就这样,母亲老家的乡人们在家里住了几日之后,城市也逛得差不多了,城里的饭也吃了(他们一直称母亲做的饭为城里饭),但并没有人提出要走。乡人们的介入,已使父母的正常家庭秩序受到了影响。母亲虽心存对乡人们的感激,但也不能这么无限期地随乡人们住下去。在母亲和父亲简短地商量后,在吃饭的时候,由母亲说。母亲说:地里的庄稼收了吧?乡人答:收过了。母亲说:二遍麦该种了吧?乡人们:就这几天。母亲说:各位表婶表叔,俺小邱不是不想留你们,你们都太忙还要种二茬麦,俺就不留你们了。等明年庄稼收了,再来住。于是表婶表叔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该回了,该回了。并一致决定,明日就回。父亲、母亲便吁口气,看着即将要走的乡人,觉得这几日也没啥。晚饭后,父亲陪着乡人说了许多话。
第二日,吃过早饭并不见乡人们走,他们也不提议去逛街,而是照旧坐在地上床下说一些关于种二茬麦的话题,母亲也不好说什么,一旁陪着。直到父亲晚上回来,看到这些乡人们仍没走,便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也正疑惑,两人琢磨一下,才明白车票还没有给人家买。母亲吸取了教训,第二日,一吃过早饭,母亲便带着乡人直奔火车站。买过火车票。一直把家乡人送到车上,母亲才真正吁口长气。
接下来的连续两三个月里,一家人过起了紧张日子。家里的米面吃空了。那时部队吃的也都是定量,家里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买完车票后自然也要紧张一阵子。
在连续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家人要连续地喝粥。父亲、母亲能忍受紧张的日子。敏和权一坐到桌前,端起粥便往碗里掉眼泪。父亲就说:没啥,这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你们的爸爸小时候是靠要饭长大的。
敏和权这时就哭出了声,原因是他们刚被老师批评过。批评两人的理由是:两人在上课的时间里要不停地请假上厕所。敏和权都感到委屈,他们不能在老师面前哭,便在父母面前哭,把泪水流进稀薄的粥碗里。
父亲当团长时,老家来人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父亲职务的升迁,来人的次数便愈来愈频繁了。当然首先仍是母亲老家来人,他们不再单纯地亲近城市和向往城市了,再来家里时,而是有事求父亲。在当时的年代里,当兵很时髦,当兵不仅暂时可以离开农村,在部队里还有希望入党、提干,那就意味着光宗耀祖了。最不济的,找个对象,也比平时好找了许多。
聪明起来的乡人也不再单纯地和母亲攀同乡关系了,他们绕来拐去的总能和母亲套上一层亲戚关系。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经常出现一群喊母亲姑、姨或奶的适龄青年男女。他们在父亲或者其他长辈的带领下,前仆后继地来到家里。他们的目的简单而又明朗,那就是当兵。
他们住了下来,吵吵嚷嚷,不住地呼唤父亲,亲切地叫着母亲,然后阐述着自己当兵的理想。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敏和权仍在上学。三五人一伙来到家里,一副不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弄得父亲有些心烦意乱。
母亲在这种大呼小叫中,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尊严。那些日子,她虽累虽苦,但心情是快乐的,她喜欢听这些乡人们说着那些肉麻的恭维话,更喜欢当救世主那份感觉。她真心希望,把家乡那片土地连同乡人一起搬到部队,搬到城市里来。
让几个青年男女当兵对父亲来说不是太困难。他们很快被父亲接收了下来,并打发他们的父母或长辈离开,这些乡人终于满意地离开了。车票自然又是父母给买的。
父亲便在夜晚的床上叹气,母亲仍沉浸在乡人们的喜悦里。母亲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