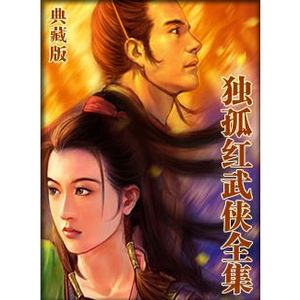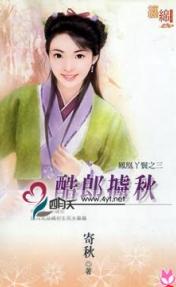小春秋-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帕斯卡尔说:世上一切灾难都起于人不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一棵“思想”的芦苇;颜回有芦苇之风,孔子在众弟子中对他评价最高。说起来,孔老先生也有些凡人的毛病,看《论语》就知道,他也喜欢背后议论人,但他对颜回是一贯地夸奖,这可能是因为颜回能做到的,孔夫子本人也做不到。
孔子就是个不肯呆在屋里的人,他要奔走,要实践,总想干点什么,他的大部分弟子都和他一样,很积极,很忙,忙于做官、办外交、做买卖,忙于改变世界。这当然也属于做好事,是做好事中的行动派。
行动派的代表人物是子贡和子路,他们做的好事想必很多,但历史上鲜有记载——古代的史家如同现在都市报的记者,对人性抱着相当阴暗的看法,他们通常喜欢报道坏事——但有几件还是流传下来了,连同孔子的评论。
比如有一次,子贡在外地碰见了一些鲁国老乡,也不知是掳去的还是骗去的,老乡们已经沦为奴仆;子贡是仁人,有不忍之心,况且又是老乡,于是出钱把他们赎出来带回了鲁国。
然而当时的鲁国有一项政策,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金由国家财政支付。但子贡在做好事啊,怎么能拿着发票去报销呢?所以,“来而让,不取其金。”
至此,子贡算是把好事做到底了,他完满实现了中国人对“好事”的全部预期,但事情传到孔子那儿,老爷子却不以为然,子曰:都像子贡这样,以后鲁人被拐卖了恐怕就没人再去赎了。
相反的,有一次子路见义勇为,抢救了落水者,被救的人千恩万谢,最后说:也没别的,这头牛你牵了去吧。子路竟不客气,施施然牵着牛回了家。这件事真的有点不靠谱,把好好的一件“事迹”弄的不好报道,但孔子得知,竟大加肯定,断言:鲁国人民从此必将争先恐后地拯救“溺者”矣。
两件好事,两种态度,由此可见孔子对人的道德实践抱着相当现实的态度,他相信人有道德之心,但也相信人有利己的本性,他的意思是,你的境界那么高,高得凡人跟不上,那么德行也可能就变成怪癖,失去了教育意义。
当然,按我的想象,子贡也可能不服气,心里说:做好事还做出错了,都像颜回那样倒是不会出错。可是他做了什么?
孔子则说:都像颜回那样,也就不需要做什么了。
君子之睡眠问题
《易经》《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就是说如果一人他是个君子,德才兼备,人五人六,这时候他绝不能松懈,必须“朝乾夕惕”,从早到晚奋发向上而战战兢兢,如服了伟哥之人,如横过马路之鼠,总之保持肾上腺素的充分分泌,永远兴奋和紧张。
为什么呢?孔子给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人当了君子就必须奋发向上,不向上就会退步、堕落,就不再是君子;第二呢,人当了君子就比较招人烦,所以必须战战兢兢,以防小人暗算。
后一个理由的依据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果换了庄子,就会说:得,咱也别当君子了,当棵小灌木成不成?但孔子他老人家不这么看,他认为不仅不能当灌木,而且还得越长越高;那么风来了怎么办?除了提心吊胆就只有长成一棵钻天杨,收枝拢杈,别去张牙舞爪地招风。
——都是老掉牙的智慧,而且智慧和智慧之间还要吵嘴,所幸我在此要谈的只是一个相关的小问题:君子之睡眠问题。
做君子,长期兴奋长期紧张,没有一副好身板显然是不行的。春秋时代人的平均寿命顶多三十几岁,孔夫子却活到了七十多,属于古稀人瑞,不作“文化昆仑”“大师”“巨人”真是天都不答应。考察老先生长寿之道,除了食不厌精,热爱旅行,还有一条是反对睡觉——这方面有个“宰予昼寝”的例子: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老爷子看见了气得什么似的,一口断定“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可怜的宰同学别说是大树了,一觉就把自己睡成了朽木。
这段公案成了现代人打倒“孔家店”时一个颇为煽情的口实。我上初中时正赶上批林批孔,老师愤怒声讨“克己复礼”,大家听了也无甚心得,但讲到“宰予昼寝”这一段,同学们对该老头儿的印象马上就不好,白天睡一小觉,多大个事儿呢?值得这么上纲上线?
后来人长大了,读了《易经》,再读《论语》,读书而明理,终于比较理解孔老夫子的苦心:睡觉在古代的确是个大问题,那时候空气清新,人的想法又相对地少,大众娱乐活动基本没有,生活全面无聊,一个人就很容易昏昏欲睡,夜里睡了,白天想想闲着也是闲着,再眯一觉,这样下去他就比较慵懒、比较松懈,就比较不容易“朝乾夕惕”,他就只有堕落下去了。
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古典中国的有志青年乃至老年,与睡眠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莫过于“头悬梁、锥刺骨”,那是苏秦在苦读,头发吊在房梁上,一锥子扎进骨头里,知道的,他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玩儿S/M。
话说到这儿,又说回到“古老智慧”:孔子催人上进,这很好,但人太上进了,就难免自虐、变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就难免别人看你不顺眼。所以,让我选择的话,吾从庄周,我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不上进,而是两千年来太上进,自己把自己逼拧巴了,所以,重新把自己理顺溜的办法之一,就是睡个好觉,放松,爱怎么着怎么着。
寡人有疾
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又爱钱、又好色,火气又大,对这样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孟轲先生说,好啊,只要百姓吃得饱,只要街上没有老姑娘和老光棍儿,只要一怒而能安天下,那么,您就好货、好色、好勇吧。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TXT小说下载:。。〗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孟子是那个时代的良心。孔子生活在他所想像的落日余晖中,而在孟子面前,茫茫长夜已降临,“上下交征利”,“率兽而食人”——在鲁迅之前两千二百多年,孟子就以“吃人”的意象断定社会的兽性本质。也正因为暗夜当前,孟子激烈而坚定,他把一种行动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入孔子开创的传统:“仁义”不仅是源于古老记忆的价值,而且成为一种必须为之战斗的社会理想。
对气大声宏的“理想主义者”,我一向怀有疑虑。理想主义是美的,一个人很可能仅仅因为理想主义的美才成为理想主义者,所以当今的“理想主义者”学中文的居多,结果呢,我们看到的大抵是作秀而已。所以,我真正尊敬的理想主义者为数甚少,孟子是其中之一。该先生东奔西走,见过了一连串儿君王,从不谄媚,从未卑怯,他永远居高临下——大众欣赏和热爱居高临下地对他们说话的人,比如台上的明星或屏幕上的专家或骂人的作家,但君王们可没有这种自我作践的癖好,所以,孟子的居高临下是危险的,他竟履险如夷。
这需要真正的勇气,而孟子从不缺乏勇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在古代儒生身上时有所见,他们是真的不怕,不仅因为他们胆儿大,更因为他们从孟子那里传承着一个根本信念:在君王的权威之上,另有道德和伦理的权威,凭依着这种权威,他们英勇无畏地捍卫人类生活的基本权利,比如不挨饿,不被欺负,不被人吃。
那些儒生已被忘掉,只有孟子,尽管我们努力忘掉他,他那机智、热情,或严厉如坚金的声音在汉语中依然回响:“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君子远庖厨”、“与民同乐”、“国人皆曰可杀”……
但响声最大的,可能还是孟子的对话者诚恳的声音:俺有毛病,俺好钱,俺有毛病,俺好色,俺有毛病,俺见了穷人、弱者或者想起远在天边的外国人就压不住火儿,怎么办呢?
孟子沉默。
人性与水与耍赖
有一次孟子碰见告子,二子讨论了一个大问题:人性之本质。告子曰:人性如洪水急流,东边'〃文〃'决了口就向'〃人〃'东流,西边'〃书〃'决了口就向'〃屋〃'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不以为然,该老先生好口才,冷笑一声问道:
水固然是向东流也行向西流也行,但难道它向上流也行向下流也行吗?
这一下问得告子当场傻掉,是啊,水是下流的,水向低处走,也就是说,水并不是那么好性子,随你怎么引导和塑造。
这和人性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孟夫子气壮山河地断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显然,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对不对且不说,他这种论辩方法我就很不佩服,人性是人性,水是水,两样东西不可比,一定要比,水之下流也未必证明人性之善,证明人性之下流岂不更为贴切?
但在古典中国,孟子的说法一直占着上风,每个中国人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本来是善的、好的,只是……唉!世道啊,没办法呀,怎么俺如今变成了这样了呢?二千多年来,大家就没好好想想,如果每个人原本都是善的,那么那个“恶”是从哪儿来的呢?
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认真研读一下贪官污吏们在监狱里的写作成果,你会发现,老套路没有变,此时率兽食人的“猛虎”居然也是孟子的信徒——虽然这帮家伙大概一辈子也没读过一行《孟子》,虽然孟子提起这帮家伙就咬牙切齿——他们通常会哼哼唧唧地回忆纯洁的童年或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