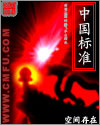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鼎盛时期。
城子崖发掘的结果证明,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而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这一命名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却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紧密相联的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考古学家梁思永于1931年春天在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当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了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一龙山文化一商文化三叠层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划分的科学依据。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并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龙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在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而什么样的文化又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在1932年春进行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的价值。因为有了宫殿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从这次发掘开始,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地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示和研究这些宫殿基址上来。由于这些宫殿是在很长时期内陆续建造而成,旧的毁弃后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的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多人。他们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安阳殷墟所经历的近9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郑州商城的发现
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又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自幼对古器物颇感兴趣,早年曾作为一名技工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并随考古人员学到了一些考古和知识。抗战期间在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他一度出任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会员、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才使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二里岗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