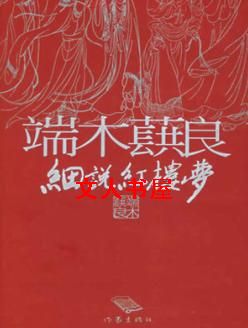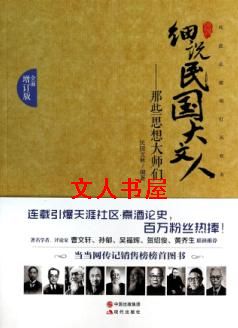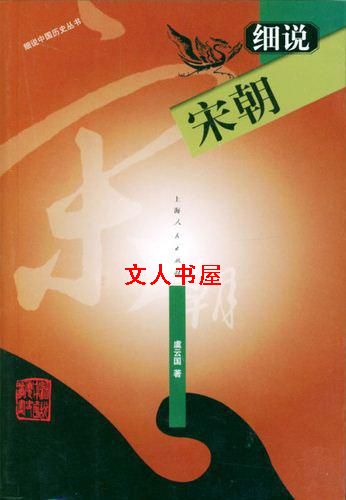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五、“史鉴”何如“有据”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为咏史诗十首。
其中第九首诗写《西厢记》中的“蒲东寺”,第十首诗写《还魂记》里的“梅花观”。
这组诗,总的题目是咏史的。前八首所咏,都是有史实可据,只有后边两首与“史实无考”。
“蒲东寺”和“梅花观”都是根据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故事写出来的。按理不应列入“咏史”篇目里面才是。
在这回书中,写众人看了“咏史诗”都同声叫好时,唯有薛宝钗提出异议,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这时,曹雪芹也为林妹妹说:“若云无年代可考……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何难也……不过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岂不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其实,宝钗在这番话里,一方面“假撇清”说“自己也不大懂得”,因为在她心目中,是把《西厢记》和《还魂记》派作“邪书”之类,话里说“我们也不大懂得”,意思是指派唯有黛玉才懂得,把球踢给了黛玉,这儿就泄露了自己的心机。
在“庚辰本”中,脂砚在这儿批写道:“余谓颦儿必有来讽,不意竟有此饰词代为解释,此则真心以待宝钗也。”
这条批语说得很对,可惜另外还有一点,脂砚未予指出,作者在宝钗口中用的是“我们”来包括黛玉在内的称谓,而黛玉却用“咱们”相称,证明黛玉对待宝钗是无间无隙,在推心置腹地说话,而宝钗却用“我们”。在这个小段中,一用“咱们”,一用“我们”,泾渭分明,以小见大,可见作者对塑造二人的为人,一丝儿也不放过。
六、“铁门槛”和“一刀两断”
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从哪本书上摘录下来一段王夫之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绣帐,寓意则灵。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
这几句话,说平凡也平凡,说不平凡也不平凡。不平凡的是,王夫之居然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槛”。
这真如禅宗的“当头棒喝”!
我国一向崇尚自然,凡是顶礼泉林的艺术家,从来都受人爱戴。巢父、陶渊明、阮籍、嵇康、顾恺之、刘希夷、温飞卿、倪云林、唐寅、祝枝山……人们都认为唯有他们才是高人,天地灵气,山水佳音,都由他们主领掌握。至于“金铺绣帐”,则是鄙俗不堪的事物,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而只有藏垢纳污的用场。但是,王夫之却把这些“金铺绣帐”庸俗事物,和高雅超凡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并列在一起,而且给了他们同一把钥匙:“寓意则灵。”
“烟云泉石”是人的自在生存空间,应该说是“第一自然”。“金铺绣帐”则是由人创造的生存空间,可谓“第二自然”,也和泉林一样,要和人的意识感情熔铸在一起,它就会焕发出灵感,丰富人的世界。人所以和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会创造,能创造衣、食、住、行和理想。
王夫之却认为:只承认“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才是大千世界的一切,是画地为牢,是固步自封,是铁门槛。
韩愈曾经说过一句话:“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很对。做古人的影子,随人说短道长,都是不中用的。韩愈改变了六朝以来的文风,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艺术天地里应该涵盖什么,应该表现什么。韩愈就是韩愈,不能向他要求更多的东西。
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王夫之时代,就像黄河流到龙门,奔腾而下,开创了另一个起点;鲤鱼流到这里,便要翻身,更要跳起,形成新的飞跃……
王夫之很清楚,有历史责任感,作了震古烁今的宣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理。”王夫之要别开生面。
读者因为习惯于曹雪芹自己标榜的话:“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这才是曹雪芹故作狡猾处。曹雪芹不是一个画像师,铁门槛他是不会立的。曹雪芹不是一个出纳员,铁算盘是不会用的。曹雪芹的性格,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他是十足的“不肖子孙”,但若按照道家“不肖”的定义,则恰巧合适。
大家都知道《芙蓉诔》祭晴雯的“悼词”,是为阿颦作谶(庚辰本七十九回脂砚评语)。这在“碧纱帐里,卿何薄命,黄土垅中,公子无缘”等句,更是明白交待了。芙蓉寓意至深,就是林黛玉的化身。
曹雪芹借着为晴雯作诔的机会,向世上宣称:“他要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与世无涉”,“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我又不稀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赏称赞”,“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作俑也”。
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这是说不读圣贤经典之书,反而运用微辞1《楚辞》如数家珍),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他奉女儿为“星日”,但在那时,能与“星日”作比的,只能是皇帝老子),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出一篇长文《石头记》)?
括弧内是我搬运过来的,请读者原谅。
这篇自供状,说得何等清楚,坦诚、激愤、毫无保留,这才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动机和经过呢!
一个人既不能离开眼睛里面的世界,也离不开自身所经历的世界,但是必须要和感情意念熔铸塑造在一起,才会创作出幽微灵秀的艺术来。这种感情是有层次的,由于囊括内容丰富,涵盖角度广阔,自然也就博大渊深,无往而不至。
汤显祖写《还魂记》,是在追求“有情之天下”。他回答他的朋友(那些认“理”不认“情”者)说:你们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谛听之,并理亦无。”他认为无情,也就无理可说,情和理不能像西瓜似的,一刀切成两半;却像藕那样总是常扯着。所以杜丽娘可以还魂,死而复生。这和汤显祖欣赏苏东坡的笔墨、米襄阳的山水,都是一致的。从苏、米手上出现的白石枯木、烟云林泉,回漾着灵气,都有着生命,都不复是一般的“木石烟云”了。
罗丹也说过:“美丽的风景所以使人感动,不是由于它给人或多或少的舒适感觉,而是由于它引起人们的思想。看到的线条的颜色,自身不能感动人,而是由于渗入其中的那种深刻意义。”
古今中外的大艺术家,对最高艺术境界的认同,都有一个会合点。情理相生,灵肉一致,王夫之、汤显祖、罗丹、曹雪芹等等,在这儿都互通了消息。
七、林黛玉两次“失乐园”
从古到今,建造人间“伊甸园”的,只有《红楼梦》中那座“大观园”。
王夫之没有机会阅读《红楼梦》,《红楼梦》那时还记在“女娲石”上,所以,曹雪芹称它为《石头记》。
但我觉得引用王夫之的几句话,好像对《红楼梦》更适用。因为《红楼梦》恰恰记的既是“金铺绣帐”的事物,同时又是写的“亲睹亲闻几个女子的悲欢离合,兴衰际遇”的故事。两相对照,王夫之的话对《红楼梦》是合适的。
因为曹雪芹也是经历过“亲睹亲闻”的启示,但他又反对铁门槛,在这儿和王夫之就成了同调。
试看《红楼梦》里写了一个“铁槛寺”和“馒头庵”,妙玉自诩辨歧途知泉源,自称“槛内人”。这些名号和内涵,都是从唐代王梵志的讽刺诗意派生出来的。
在曹雪芹笔下写“铁槛寺”,成了王熙凤拆散姻缘、图财害命的密室;“馒头庵”成了秦钟和智能的偷情地。两处清净佛地,竟然全无半点“清净”可说。
住在拢翠庵中的妙玉,原本是“槛内人”。正可说明拢翠庵也就是“铁槛寺”。妙玉由于她无力跳出大环境和小环境的约束,最终的结局是:“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白玉无瑕遭泥陷”,仍然在铁门槛中毁灭。
曹雪芹能超出“亲睹亲闻”这个框子,也就是能从“目之所见,身之所历”的铁门槛中脱身出来,这样才能有《红楼梦》的产生。
引发曹雪芹的动力,不是别的,而是由于林黛玉的两次“失乐园”,使他要上天去补天,下地去补园,结果都适得其反。
黛玉第一次失乐园,在《红楼梦》中是这样记的:
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待到绛珠仙子背负着“还泪债”下凡转世;“辞父”、“进京”、“寄养”贾府,又住进了人间的“伊甸园”。这座连神仙也住得的地方,是为元妃省亲而营造的紫府璇宫,是被人们艳羡的乐园。绛珠仙子成了人间乐园的“潇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