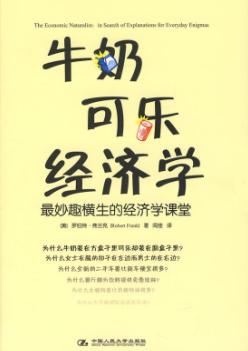经济解释-第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认为不能;今天还如是看。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些理念下有学者提供过有说服力的假说验证。
因为上述的原因,本卷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他家所说的有好些地方不一样。虽然这门学问在六十年代兴起时,我算是个正选人物,但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与他家分道扬镳,一士谔谔,感到寂寞。我是顽固的。我的顽固是因为我坚持如果推不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费心思。既然没有证据经济学可以改进社会,解释世事是剩下来的唯一用途了。
究竟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在哪里呢?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历来有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其二是收入的分配(ine distribution)。加上货币,把一个经济的整体加起来,就成了宏观。传统的制度分析也离不开这两方面。很不幸,这传统完全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产权、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这样,不仅旧一套的制度分析与制度无关,而就是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方面,漠视了价格与合约的安排,行为或现象的解释就不可能有大作为了。不同的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会导致不同的安排,而不同的安排会影响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安排就是制度了。选择安排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
前两卷对行为的解释,或明或暗地我都以一些制度的安排为基础。本卷是回到基础那方面去。
(《经济解释》之六十七)
第一章:高斯定律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定相同。这分离是大话题,有百多年的争议,曾经波涛起伏,一九六○年高斯发表了他的鸿文后开始平静下来,但今天还是余波未了。
简单地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按自己个人的利益与成本作决策的,外人或社会受到的影响他可能不管,或者要管也管不来。这个人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利,但不一定收到回报;他的行为可能对社会有损,但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举个例。我到某机构讲话,有酬金,收到的酬金私利是机构愿意付的,在边际上我的利益与机构的利益没有分离。但如果我讲话时有记者在场,内容发表于报章上,社会可能得益,但我不获回报。没有回报,从社会的角度看,在边际上我讲话的供应是太少了,传统认为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这是指在边际上,社会产值(social product)与私人产值(private product,我的私人回报)有分离,前者高于后者,政府是应该补贴我多讲的。这是传统之见。
反过来看问题也类同。如果我的讲话在报章发表后对社会有害,但我却不需要赔偿给社会大众,那么在边际上,我的私人成本(private cost,这指准备与讲话时间)是会低于社会成本的──我的私人时间成本加社会受损的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边际,因为我不需要赔偿给受损的,我是讲得太多了,于是无效率,违反了柏拉图情况。政府应该强逼我赔偿给社会,或要抽我讲话税。这也是传统之见。
传统之见,是如果在边际上社会的产值高于私人的产值,或社会的成本高于私人的成本,市场是失败了。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以补贴或抽税的方法(或其它方法)来修改上述的产值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s)或成本分离(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最早提出近于上述的分离概念的,应该是英国的卓域克(E。 Chadwick)。此君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或公安的文章,指出盗窃或抢劫的行为对社会有害,犯罪的不需要赔偿给受害者,对社会无效率,所以政府要设立公安或警察管治。卓域克是米尔(J。 S。 Mill)的朋友。后者的智商之高,据说是人类纪录,而又是经济学大师。他于一八三四年提出了贫民法律,指出贫困的人对社会有损害,应该予以协助。更重要的是米尔于一八四八年提出灯塔的例子,其后于一八八三年瑟域克(H。 Sidgwick)再把灯塔大事宣扬。
灯塔的例子有几方面的问题,但这里有关的是灯塔建成后,利用灯塔的指引而在黑夜中避开礁石的船只,逃之夭夭,不付费用。这样,灯塔就没有私人建造了。这是说,灯塔的社会收益远高于私人的收益,二者有分离,政府是要资助建造灯塔的。后来高斯考查英国的灯塔史实,一九七四年发表文章,说有几个私营灯塔的人发了达。但他的论据不足,因为那些灯塔收费是由政府支持的船务公会代收的,而灯塔发达的原因,是私营业主把灯塔卖给政府。政府通过法例要收购所有灯塔,若不是有管制,私人不抢多建才怪。
第一节:庇古的分析
推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中心人物,是庇古(A。 C。 Pigou; 1873…1959)。这位在剑桥承继马歇尔的讲座教授者,写了两本关于福利经济的书,而最重要是一九二○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是巨著,差不多整本是关于社会成本问题的。
庇古的长处,是采用例子很富想象力。但他的分析能力并不超凡,喜欢把一般是同类的例子分类,使论点混淆不清。庇古最弱的地方,是对事实的考证马虎之极。伟大如剑桥的经济学传统,在事实考证那方面是令人失望的。马歇尔马虎,庇古更马虎,而与庇古同期的凯恩斯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过人之处。
庇古最有名的关于社会成本的例子,是一家工厂污染邻居。他在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到这例子,但因为浅白易懂,也就成了名。一家工厂为了生产而污染了邻居,但工厂不用向邻居赔偿。工厂于是只算私人成本,即是工厂本身需要支付的生产费用。但因为生产而对邻居的污染,其损失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社会成本是工厂生产的私人成本加邻居的污染损失。在不用赔偿给邻居的情况下,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了。按照庇古的理论,工厂若不赔偿给邻居,政府就要干预,以抽税的办法使工厂减低产量,或迫使工厂搬迁。
骤眼看来,这样的分析若加上数字示范,看到社会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产值,政府的税率应该是多少非常明确,所以分析有说服力。一个大学生,上过一课庇古的分析,就可能认为自己懂得怎样改进社会了。后来凯恩斯学派对国民收入增减的数字分析,也同样地可以使学生在一课之内觉得自己学会了济世之法。经济学被认为可以改进社会,这些「秘方」就是原因。
庇古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大地如茵的禾田,火车从中穿过,其火花损害了谷稻,也不用负责。这例子有个真实的笑话。一九六九年,史德拉与艾智仁旅游日本,坐火车穿过田地。他们问火车上的管理员:近于车轨的农地是否因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响应,是近车轨的地价较高,因为火车的声浪把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在庇古的巨著中,长篇而大论的例子是农业。这是中国的不幸。庇古分析地主与雇农的合作关系,指出地主若不自耕,对社会总有不良影响。例如,因为租约短暂,农民租用农地不会在地上多作投资,而地主也没有意图多投资于土地,因为农民不会珍惜地主的钱。工具、房产等的投资也如是。总之,地主不自耕对社会一无是处,为祸不浅也。庇古举出爱尔兰的例子,说凡是租用农地的生产都不成话,引经据典,说得有声有色。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在那里的图书馆内作了详尽的追查,找到庇古在脚注引经据典的书籍,这些书籍的脚注提到的书籍,一路追查下去,结果是找不到任何证据说农业租耕地的产量比自耕地的为少。那是说,庇古是胡乱地引经据典,可能希望读者不会像我那样,花一个星期时间去追查他的脚注经典,及经典的脚注经典,查到不能再查为止。
胡乱引经据典的行为可不是庇古独有的。理论上的引经,引者不敢乱来,因为引错了被引的人会反驳。但事实的引经是另一回事,胡乱引的在经济学很常见。一九六九年我研究公海渔业时,就发觉有类同的习惯。一位作者举一个假设的例子,第二个作者引而据之,经过了三几个,就变成了实例,一般学者深信不疑。我对文章的实例抱怀疑态度,上述的经验是原因。有些作者我是不怀疑的,但那是名牌效应了。
我说庇古的农业分析是中国的不幸,因为这分析当时影响了另一个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教历史的唐尼(R。 H。 Tawney; 1880…1962)。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作为联合国前身的一个教育顾问,一九三○与三一年间他两次到中国,勾留了几个月,凭自己的想象力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 and Labour in China)。这本书十分有名,翻译后在中国洛阳纸贵。
唐尼是社会学家,其思想相当左。他的中国名著用的是庇古的经济分析,引用的事实比庇古还要马虎,论调是针对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中国的共产革命,唐尼的书受到大事宣扬。
我从来不知剥削为何物,但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间美国的卜凯(J。 L。 Buck)教授在南京大学(又称金陵大学)兴师动众,作了历史上最详尽的农业调查。这调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农业租耕地的生产效率不比自耕地的差。事实上,租耕地的产量大约比自耕地的高百分之二。后来卜凯教授的几个中国助手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其结论也相同。这些结论与同期的唐尼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卜凯的中国农业研究的详尽调查资料,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巨册。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购得了一册,可能是孤本了。几年前一群来自南京大学的学生到港大造访,我把该巨册送给他们,在册上陈述往事,请他们送到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不久前听到该大学将有卜凯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