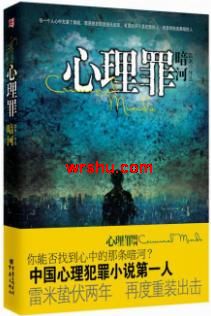法哲学原理-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藏邪恶本性的坏人,以期对杜绝邪恶至少有所贡献,——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用这种方法而使其内容具有肯定的一面,所以它们都成为出于善良意图,从而都是善行。要象上述那些博学的神学家那样在任何行为中找出肯定的一面,从而找出某种善的理由和意图,其实只需要极少一点理智教养就够了。
因此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在这种抽象的善中,善和恶的区别以及一切现实义务都消失了。因此之故,仅仅志欲为善以及在行为中有善良意图,这毋宁应该说是恶,因为所希求的善既然只是这种抽象形式的善,它就有待于主体的任性予以规定。这里牵涉到“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一恶名昭彰的命题。
这一说法就其本身说自始是庸俗的,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同样笼统地回答它:正当的目的使手段正当,至于不正当的目的就不会使手段正当。目的是正当的手段也是正当的这一句话是一种同语反复的说法,因为手段本来就是虚无的,它不过为他物而存在,而只是在他物中即在目的中才有其规定和价值,也就是说,它如果真正是手段的话。不过上述命题不止具有这种同语反复的形式意义,而且指某种更确定的东西而言,即为了某种善良目的,把原来完全不是手段的东西用作手段,把某种本来是神圣的加以毁损,总之,把罪行当作某种善良目的的手段,以上种种都变成许可的,甚至还是人们的义务。当人们谈到上述命题时,在他们脑际浮现出对上述在法和伦理的孤立规定中肯定要素的辩证法的模糊意识,或者浮现出对同样模糊的一般命题的模糊意识,这些命题有如,你不得杀人,你应关心你的福利和你的家庭的福利。诚然,法官和士兵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杀人,但是,杀哪种人和在什么情况下杀人是许可的而且是义务,都有详确的规定。所以那怕是我的福利或我家庭的福利,都要服从更高的目的,被降到次要地位,而成为手段。可是标志某种行为为罪行的,不是依然模糊的而受制于某种辩证法的那种普遍性,相反地,它早具有客观上已经确定的界限。现在,被设定为与罪行的这种规定相对立的东西,以及仿佛可以从罪行中除去犯罪性质的那种东西,就是正当目的,它无非是关于善的和更善的东西的主观意见。这种情况同样就是意志死抱住抽象的善不放,这就是说,一切关于善恶邪正的、自在自为地存在而且有效的规定都被一笔勾消,而这种善恶邪正的规定都被归结为个人的感情,表象和偏好。主观意见终于被宣示为法和义务的规则,因为(五)把某种东西视为正当的这种信念似乎该是规定行为的伦理本性的那种东西。我们所希求的善尚未具有任何内容,而信念的原则则更肯定,把某种行为归属于善之下的规定只是主体权限范围内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伦理客观性的假象也完全消失了。这种学说是与屡次被提到的那种自命哲学有直接联系,这种自命哲学否定有可能认识真理,然而伦理的命令正是精神作为意志的真理,也就是精神在自我实现中的合理性。由于这种哲学把对真理的认识宣称为越出认识范围的(照他们看来认识只限于现象方面)空虚的自负,于是在行为方面也必然直接以显现的东西作为原则,从而把伦理性的东西设定在个人特有的世界观和他特殊的信念中。哲学就这样地衰退颓废,这当然最初只是作为学院式的废话,从而是一件非常平凡无足轻重的事件出现于世,但这种观点必然要深入到伦理——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而成为伦理的观点,到了那个时候,它这种观点的真正意义才会显现于现实界,而为现实界所领会。由于行为的伦理本性完全是主观信念所规定的这种观点传播很广,所以从前人们所常谈的伪善,如今几乎已不再成为问题了。其实,品定邪恶为伪善是以下述为基础的:某些行为是自在自为地属于犯过、罪恶和犯罪之类,又犯错误的人必然知道这些行为的本性,因为即使在假装中他滥用虔敬和正直的原则和外表上行为,他也必然知道并承认这些原则和行为的。换句话说,关于邪恶,一般总是假定,认识善和知道善与恶的区别乃是每个人的义务。但无论如何,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从事罪恶和犯罪的行为,人既然是人而不是禽兽,这种行为就必须作为罪恶或罪行而归责于他。但是,如果好心肠、善良意图和主观信念被宣布为行为的价值所由来,那末什么伪善和邪恶都没有了,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他都可通过对善良意图和动机的反思而知道在做某种善的东西,而且通过他的信念的环节,他所做的事也就成为善的了①。这样就再没有什么自在自为的罪行①“他感到完全具有信心,对这一点我是绝不怀疑。但是世间多少人不是开始都由于这种确信的感觉而干出了罪大恶极的勾当!所以,如果一切都根据这种理由而得到饶恕,那末对于善与恶的决定、荣与辱的决定,不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判断了。于是疯癫将与理性具有同等的权利,换句话说,理性将不再有任何权利,不再有任何效力和威信;理性的呼声变成了空谷之音,而真理就在完全不怀疑的人这一边了!。
①参阅柏拉图:《理想国》,第337节a;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4—57页。——译者
这种宽容完全对于无理性有利,结果所届,殊属不堪设想。“雅可比给霍尔麦伯爵的信,论斯托尔堡伯爵改变宗教信仰,1800年8月5日。于奥依丁(载《布伦奴斯》,柏林,1802年8月号)和罪恶了,代替上述那种坦直而自由的、顽强的、干脆的罪人,出现了凭借意图和信念而完全得到辩解的意识。在行动中所抱的善良意图以及我对这一点的信念,就可使我的行为成为善的。
我们在判断和评估一种行为时,如果依照这种原则,那只好以行为人的意图和信念即他的信仰作为标准。然而他的这种信仰不是象基督要求信仰客观真理的那种意义上的信仰,因此,对具有虚伪信仰的人,即具有内容上是坏的信念的人,所作的判断也是坏的,即与其坏的内容相适应的。相反地,他的这种信仰指忠于信念而言,这里要问的是:人在行动中是否一直对他的信念保持忠诚,这是形式的主观的忠诚,它成为义务的唯一尺度。
在这种信念的原则之下,由于信念同时被规定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所以错误可能性这种思想也必然会冒出来,这一点从而含有绝对规律这一前提。但是规律不会行动,只有现实的人才会行动。根据上述原则,在评估人的行为时,唯一重要的是,看他在何种程度上把上述规律采纳在他的信念中。但是,如果按照这种原则,应当根据上述规律作出评价的,即应当一般地据此来测定的,不是行为,那就看不出上述规律究竟是为什么的和有什么用处。这种规律就蜕变为具文,事实上就成为空洞字句。
其实,它只有通过我的信念才能成为一种规律,成为使我负义务和对我具有约束力的东西。这种规律得主张本身具有神的或国家的权威,甚至具有数千年之久的权威;在这几千年中它是人类和人的一切行动及命运赖以联结起来和巩固地存在的一根纽带,——这就是一些包含着无数个人的信念的权威。但是我也可把我的个别信念的权威跟它们对抗,因为作为我的主观信念,它的唯一有效性就是权威。初看起来这好象是自负透顶,但根据主观信念是唯一尺度这个原则,那就根本不是自负了。即使理性和良心——究非浅薄科学和恶劣诡辩所能驱除的——由于高度的前后不一致,而承认错误的可能性,但是把犯罪和一般的恶说成是一种错误,那就把错误缩减到最小限度。其实,过错是人的常事,谁不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有过错误呢?我昨天中午吃的是卷心菜还是白菜呢?关于无数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有错误。但是,如果一切都以信念的主观性和坚持信念为转移,那末重要和不重要事情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但是,上述承认有可能犯错误这种高度的前后不一致,系根源于事物的本性,如果换一个论调,说成恶的信念只是一种错误,那它实际上就转变为另一个前后不一致——不诚实的前后不一致。一方面既然说,信念应该是伦理性的东西和人类最高价值的根据,从而被宣布为至高无上和神圣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说一切问题都是关于错误,我的信念是一种卑不足道的和偶然的东西,其实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可能这样地或那样地对我出现。事实上,如果我不能认识真理,则我之所谓确信是极其无聊而卑不足道的。
所以我无论怎么想,反正都是一样;存在我的思考中的,只是那种空洞的善,理智的抽象。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根据以信念为理由来作辩解的这个原则,可以得出,在应付他人反对我的行为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时,我得承认他们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至少他们依据他们的信仰和信念主张我的行为为犯罪;根据这种逻辑,我不仅自始得不到任何东西,甚至反而从自由和光荣的地位降到不自由和不光荣的情况。这就是说,我感觉到正义——在它的抽象形态中既是他人的也是我的——只是他人的主观信念,而在它对我实行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只是遭到外力的强制。
(六)
最后,这种主观性在它的最高形式中才被完全领会和表达出来,这种最高形式借用柏拉图的名称就是叫做讽刺(Ironile)的那种形态。不过这里仅仅从柏拉图那里借用名称而已。他用这个词①描述苏格拉底在个人谈话中所应用的一种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