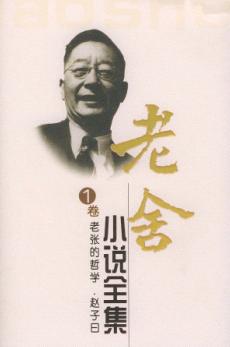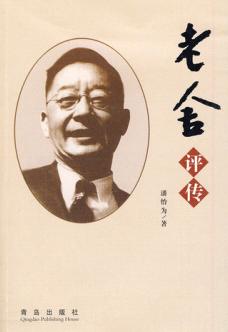老舍新诗-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时节也忘不了发财,即使发了横财,他们依然郁郁不满。
在鲜果糖食摊子左右,茶馆的门旁,离茶客们不过三五步远:瘸腿红眼的老妇与衰翁,用报纸弥补着一身的破烂,两手轮流搔抓疮疥的幼童;红绿相间的脓血满脸;瘦得象条竹竿,
脸上似乎只剩了机警多疑的一双眼;一面留神着警察的动静,一面向茶客们伸着手抖颤。
他们的饥苦,绅士的安闲,或者不无关系,这边品茗,那边讨饭;因此,讨饭的活该讨饭,绅士们只能给他们一声“讨厌”。
一盏红灯在小门上闪动,香臭难分的气味流到街头,有枕有床,无日无夜,这里的享受是鬼域的风流。
一时的兴奋,给绿脸上微添光彩,终生的懒惰,使晴朗的世界永远昏幽。
假若一年半载的,这里只活埋了一二懒汉,那倒也引不起任何人的忧愁;可是,肯狠心毒死自己的,定会豺狼般的向别人索酬:看,茶楼上藏着的弱女,不是被家里吸血的烟枪葬送了自由?
茶肆中闲坐的那些活鬼,除了私人的利益,似乎对一切全愿结仇,他们是田主,房东,或典当的老板,多一些乞用正是他们的丰收。
***
碧绿的河水,赭色的群山,一眼望不尽的都是蔗田:半绿的蔗梗,微黄的蔗叶,一片片连着灰淡的远天。
公路两旁,晾着半干的宽叶,侧着身让路,男女横负着长长的蔗秆。
蜜饯的麦冬,蜜饯的桔饼,甜蜜的内江,确是儿童们的乐园;连鲜红的辣椒也得到变成糖果的机会,多棱的冰糖,代理着幌子,在铺外高悬。
苦工们挑着整盆的糖癋,河岸上系着运糖的木船;
散布在四乡的是“漏棚”与糖厂,田沟里流泄着黑红的蜜汁,甜里带酸。
墙头上一列列的瓦盆瓦罐,竹棚下糖盆坐着小坛,用河泥作成的光润的土饼,垫了一张糙纸,压在糖盆上边:泥饼中的水分滤过了蔗滴,掀起泥饼,二寸厚的糖沙松软鲜甜;滴入小坛的蜜水,再炼成滴,“二白”的制造也是那么简单。
古拙的用具,简陋的方法,一万元的资本,现在,也极容易赚到两千,茶馆里忧时之论,只怕民贫物竭,其实因战时的需要,只要生产便会赚钱;土盆泥饼一日多似一日,蔗糖已大篓小篓的运往陕甘;就是那牛津风度的学士,和以巴黎生活为标准的什么官员,也勉强喝着云南野长的咖啡,幽默的微叹:噢,中国糖也有相当的甜!
***
在这永是峰回路转的行程里,到处都看见肥健诚朴的壮丁:公路上,镇市中,随时听见齐呼的一二三四,天还未亮,城里城外都起了抗敌的歌声。
散沙般广大的民众,
今天齐一了脚步,筑起肉的长城;铁的纪律,疗治了精神与身体的病态,纵莽关西大汉,一声立正,也都挺起前胸;两三个月的训练,他们晓得了国事,激愤的愿从万重山里冲到南京。
同时,在那些繁闹的城市里,新中国的生命也春草似的峥嵘:古代的铜锣敲报着更次,五更起来的却是新时代的男女学生;军帽军衣,一律的赤着脚,“唤醒操”跑尽了全城;红润的脸上流着热汗,早雾未退,那些纯洁的心中却见到光明;“中华民国万岁!”
“万岁!”连挑着青菜的也应了声!
新生命新精神正在滋长,因了抗战,建国必成。
可是,这歌声与呼喊,无疑的惊扰了贵人的晓梦,就断定了天下并不太平。
忌妒,安闲,自私,凑成悲观的心理,新的气象使他们气短心惊;挂着山羊胡的老狐狸,卑鄙贪污而外,之乎者也的制造着无理的怨声。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的,
可想不先把狐狸之血祭了抗战的英灵?
***
山城里几乎都有座小小的公园,山水之间的简阳更难例外:万安桥下荡漾着晴江,园里的红梅使晴光倍觉可爱;微风把香味送入竹林,是诗是画,一片悠闲自在。
啊,可这是什么时候?
一处的风花阻不住山河破碎的感慨:看着这里的梅艳江波,想起了东海的崂山与泰岱;领取山河之美要先还我山河,铁与血争夺着这伟大时代!
***
快到成都,快到成都!
成都!成都!
从小学地理上就知道它“地处盆底”!
究竟什么是盆底?
加快了速度,汽车似乎了解客人的心急。
到了吗?快到了吗?啊,在哪里?
快了,还须翻过一道山,不过三十多里。
什么,三十多里?还要翻山?
哼,这广大的地土,真有时候使人沉不住气!
忘了看山,忘了南北与东西,眼钉着面前,祷告着那就是平地!
平地,平地,有希望,车已由高而低;可是,那边还有金黄的路一条,横在山腰里;快,快呀!绕过那道山腰,无疑的会看到神手捏成的盆底!
似一股山洪,车往下流,群山倒退,林鸟惊起;快!快!这时候忘了什么蜀道难不难,见着平原,就是北方人的故里!
***
比北平老着好多辈的成都,却可笑的被称作小北平!
地形建筑民情的相似,怎能曲解了历史的实情?
武侯祠的松影,
薛涛井的竹声,
使人想象着汉唐的光景,要从历史的血脉里找到这不朽的名城。
***
知道历史的悠长,
才会深思民族的宝贵。
几间屋宇的堂皇,
几个汤圆的精美,
几疋蜀锦的光柔,
几家庭园的明媚,
纵使能媲美,或胜过,北平,啊北平,已失身在倭敌的手内!
从这万峰环卫的城里攻出,一直到收复那遍地黄金的东北!
所需的是热血与刀枪。
用不着那使人衰颓的北平风味!
***
宽敞的平房,
小小的巷道,
在闹市略有些嘈杂,
颇有些地方静如大庙。
大街上,扁扁的腊味猪头悬在檐前,象些老大的蝙蝠睡着午觉,里边还有多少样小吃食,坛罐上标着红签,样样精巧;几片洁白的丝棉悬在另一家,瘦脸的衣匠缝着蜀锦被套;每一家小食馆有他特有的作风,门外标着离奇或雅趣的字号;再过去,也许就是一条深巷摆着鲜花,金桔和水仙一束束的香色俱妙。
在肃静中这老城有它的风趣,在不大惹眼的地方有它的豪华奢傲;还不至落雪的冬阴,已使茶馆中的雅士们穿起轻暖的皮袄。
***
抗战的中华,不但开开了西南财物的宝库,也没忘造就着新中国的人才:静美疏落的“华西”招待着流亡的姊妹,望江楼外,川大忙着起建楼台;种着楠树的街巷,在冬晨的薄雾里,一群群提着书包墨盒的男女小孩,说着南北各方的言语,可是
合唱着“不作奴隶的人们,起来”。
残暴愚顽的日寇,自作聪明的封闭了清华北大,炸碎了南开;哈,这不为考举人而设的教育,小儿女也懂得关切着胜败兴衰。
***
闲适的成都有它的忙碌,窄窄的古巷里,阴暗的小屋,男女挤在一处,工徒们打着哈欠,手却不敢停住。
这边栽着牙刷,
那边切着牛骨;
叮叮当当,这里打着铜壶,哗啦哗啦,那边织着土布,印着“抗战建国”的毛巾,描了金花金字的蜡烛,硬砸透眼孔的绣花针,煮软再加工的牛角器物;千只万只的手,
准确,细腻,勤苦,
一齐在支持着一日三餐,一齐在抵御外货的流入。
这才是与抗战有关的成都,民族的巨手画出自力图存之路。
***
一片阴云,千里归路,别矣成都!
重新再走上那伟大的公路;啊,那征服——万壑千山的公路,象征着民族的前途;艰苦,可是光明,哪一座晴峰没有幽谷?
让我们英毅无畏的展开地图:团结为桥,渡破艰苦,正义之路,冲过了荒芜!
阴云,瑞雪之母!
别矣,成都!
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十四日《大公报》
慈母
没见过比它再伟大的东西,因为它的名字叫“国”。
在那淫腐的巴黎,
或是崭新的赤俄,
我低首独行,“中国人”,背后那么指着我。
我恋着莎士比亚的情歌,或看醉古代希腊的雕刻,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却象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
我听着西伯利亚的夜莺,或是世界语的秋风瑟瑟,这些音乐在我心中的抑扬,是李白杜甫用惯了的平仄。
梦里,常是梦里,我轻唱着乡歌,病中,特别是病中,渴想着西湖的春色,我的信仰,也许只有一点私心,离着中华不远的当是天国!
我愿与流星们穿舞过银河,我愿与白鸥在太平洋上飞过,假若正飞着,偶然有个微音:你是哪儿的?我无须思索,更惊奇的准备,向那金黄的北平,或那乳绿的扬子,往下奔落。
我爱着全世界,爱着黄白棕紫种种的人儿,每个言语有种乐音,每样皮肤有个可爱的颜色;我爱着那朴素或艳丽的自然,我的朋友还有雪白的小猫一个。
但是那三个中国字,我的姓名,是宇宙间最甜的荔枝与甘蔗!
它们,三个小珠子似的字,串着我的灵魂,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我!
它们轻妙得不似“雪莱”,壮丽得不如“歌德”,但是自从在我母亲的口中,它们便带着“荆轲”与“岳飞”样的音色。
同样的,泰山、扬子、松花、洞庭,和那雪掩的金沙的戈壁大沙漠,听着,虔敬的,我的慈亲,就是它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
我唤着她的圣名,
象婴孩挨着饥饿,
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我将永远在那儿欣卧;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
打
(游击队歌)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