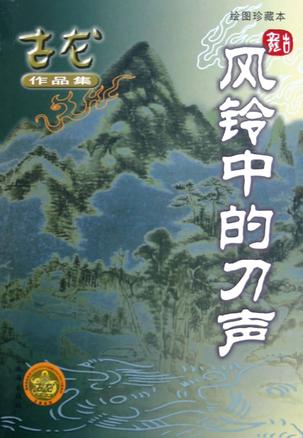黑夜中的猫群-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北富德说:“我告诉警方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给我的太太。我告诉他们我无法拿给他们看,因为它在你手里。我没有特别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聘请你。只是把大概情形说明,全盘的事只是稍稍提起而已。”
“很好。”
“我现在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警察看第一封信,柯太太,这封信可能和莎莉的死亡有关。可能也只有第一封信和这件案子有关,至于第二封信,就是我们昨天打开的那一封,我认为和本案毫无关系,我不想给警察知道有这封信。”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把许桃兰也拖进来。”
“为什么?”
“我告诉你我不希望把许桃兰拖进来。我不要她被直传,这封信会造成不良后果的。”
“为什么?”
“你还不了解吗?这件事并不单纯,有很多角度,警方会使许桃兰难堪的。”
“为什么?”
“老天,你看不出来呀!我太太可能——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护桃兰。”
“为什么?”
“天咒的,除了为什么你不能说些别的吗?”
“目前不行。”
北宫德研究一下她的理由。
柯白莎准备接受宓善楼的干涉。她问:“莎莉怎么回事?她怎么死的?是件意外吗?是不是被杀的,或——”
“多半是件意外。”
“说。”白莎道。等候宓善楼来禁止。
“显然的莎莉正在削洋芋皮,她去地窖拿些洋葱,手上拿只盘子,里面有削过皮和没有削过皮的洋芋。她右手又拿着一把削洋芋的长刀,她摔下楼梯去,长刀刺进了胸腔。”
白莎体会着他所说的一切。她问:“有什么使人想到这件事不是意外吗?”
“可以说有。”
“什么?”
“尸体的颜色。”
“那有什么分别呢?”
“警察说这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特征。”
“说下去。”
“就我听说,警察认为那把刀可能是在她一死立即被插进尸体去的,而她的死因好像不是这把刀。”
“懂了。”
“我要你想办法把这件事弄清楚。”
“什么方式?”
“我太太一定是会受到嫌疑的。我要你告诉警方有关匿名信的事,告诉他们我太太的失踪纯为家庭问题;她是要离开我才失踪的,不是为了她干了谋杀案。”
“我懂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希望第二封信给牵出来。桃兰是个大美女。假如她在这件事里一出现,报纸会认为大众对这件事会有兴趣。她的照片,……你知道他们喜欢登美女的照片。”
“大腿?”白莎问。
“当然。我不喜欢桃兰被他们这样宣传。”
“为什么?”
“那样不恰当。”
“为什么?”
“老天,我太太在吃莎莉醋,莎莉死了。为什么再要拿一个桃兰出来宣传,想再制造一个被害者吗?把桃兰放在这件事之外。我告诉你,不可以拖她进来。”
宓善楼始终没有开口禁止他们交换意见,这是非常不平常的现象,柯白莎一下警觉起来。她偷偷自肩后看去,看到的宓警官把嘴里的湿雪茄尾巴高翘在一个攻击性的角度,他已经退到一只她放她皮包的桌子边上,桌上的皮包拉链已经拉开,他现在正津津有味地看那两封原先放在白莎皮包里的匿名信。
白莎大大生气地说:“你浑蛋,你……你、……”
北富德的声音自电话那一端说:“怎么啦,柯太太,我没有……”
白莎急急向电话说:“我不是说你,我是在说那条子。”
宓善楼连头也没有抬。这两封信使他入迷了。
“条子在干什么?”
白莎泄气地说;“太晚了,你在和我说话时,我一下没有注意,没有经我同意宓警官打开我皮包,把两封信都拿去看了。”
“喔,老天!”北富德大叫。
“以后,你不要指挥我做事情的方法。”白莎怪在别人身上似地说。
她也不等答覆、把电话往鞍座一摔,差点把它摔破。
宓善楼把两封信折叠在一起,放进自己的口袋,把柯白莎的皮包拉链拉上。他没有看到白莎自北富德办公室偷出来的备忘录,也许是看到了,但认为没什么了不起。
“你还真认为你有权到老百姓房间来偷窃东西,还可以带出去?”柯白莎黑脸地指责他道。
善楼暧昧地说:“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在乎我如此做的,我们是老搭档呀。”
“不在平!”白莎大叫道:“你岂有此理,我可以把你脑袋打开花—一,假如你脑袋里会有脑子,我算输了你!你自大,穿老虎皮压动人,自以为大家会怕你,你这个——”
“免了吧,白莎。”他说:“你吵也没有用。”
柯白莎咬牙切齿,双手握拳瞪视着他不开口。
善楼说:“为什么呢,白莎?你反正不会隐瞒我的。我问北富德,他说的信在那里,他说在你手中。他说他最后看到的时候你把信放进了你皮包。所以我自己动手了。”
“你没有嘴,不能问我的呀?”
善楼露出牙齿,笑着说:“白莎,我有一种想法,北富德没有全说实话。他可是太急于告诉我一封信的事了。我每次一问他,他就快快的要说那一封信。我做警察太久了,你见到像他那种人,他主动急急提供你消息,就是因为怕你问到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一下就想到了,会不会不止一封信。”
“我想你也知道他会打电话来警告我,所以电话一响你就去掏我的皮包,别忘了,我嘴巴很快,你会吃大亏的。”
“当然你可以。”善楼不在乎地说:“但是,我知道你白莎不会如此干的。在这个社会本来是适者生存的,你骗我一下,我反骗你一下。你偷偷打了我腰部以下,我也不会去找裁判申怨……算了,我们来谈谈那个伸手抱他的小妞吧。”
“小妞怎么样?”
“她是谁?”
“我不知道。”
善楼把舌头放在上颚上啧啧出声,不表同意地说:“白莎,你总不会把我当小孩子看吧!”
“你怎么会想到我知道她是谁呢?”
“照你的性格,你会放过北富德不逼他告诉你小妞是什么人呀?”
“根本没有什么小妞?”白莎道。
“什么意思?”
“那只是匿名信。”白莎说:“匿名信你能相信呀?”
“你怎么知道根本没有这个人?”
“北富德告诉我的。”
善楼叹气道:“好吃!看样子目前只好让它这个样子了。”
“北太太的妈妈怎样了?”白莎问。
“半崩溃,妈妈和妹妹都够受的了。两个人不断分别打电话到总局看有没有报告北太太发生车祸。最后谷太太突然想到北富德可能用棒子打了自己太太的头,又把她藏在屋里什么地方,所以她开始在房子里逐间地查看。说是要从地窖查到阁楼。她从地窑开始……那是今天早上不到8 点的事。她看到的差一点把她吓昏过去。要知道一开始她以为那是北太太的尸体。不过她仔细一看根本完全是陌生人。北富德说这是莎莉。”
“谷太太不认识这女佣人?”
“显然不认识。谷太太住在旧金山。梅宝用了这个新女佣之后,她没有下来过。”
白莎道:“我看不出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联。”
善楼用鞋底擦着一支较大的火柴,想把他那半截熄了火的雪茄再燃着。
白莎道:“我看你倒不在乎,不过这浑蛋雪茄——味道的确使我倒胃口。”
“真不幸,看来你还没有吃早饭。”
“正要想先弄一杯咖啡喝一下。”
“好极了。煮一些又香又浓的好了。我也想来一大杯。”
白莎跑进浴室,快快把衣服穿好,走出来把床铺好,把壁床收回墙壁上去,使房间变大一点。她走进小厨房,把一只大咖啡壶放上炉子,她对善楼道:“我想要是我做好了蛋,你也不会拒绝的。”
“没错,两个。”
“土司呢?”
“喔!当然,不过腌肉要又多又脆。”
白莎什么也不说,一个人在瓦斯炉前忙着。嘴巴闭成‘一’字形,生气地不开口。
宓警官—一帽子在后脑勺子上,雪茄由于才重新点过,蓝烟袅袅—一把自己身体站在小厨房门口。“我只是陪你吃早餐。”他说:“吃过之后,第一件要做的是由你陪我去看北先生,我们三个应该好好聊聊。”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拖进去?”白莎问。
“我认为你可以帮我的忙。”宓善楼说:“万一北富德说谎,你可以告诉他,他脱不了身的,最好还是实话实说。”
“喔!由我来告诉他,是吗?”白莎挪揄地说,手里拿着一只平底锅,正想放上炉子,锅子成45度的角度,停留在半空中。
“一点也不错,”善楼道:“你有你的智慧盲点,但是你一点也不笨。”
善楼看到白莎脸上颜色的改变,他露齿和覆地说:“我看我最好先打个电话给姓北的,约好一下时间,免得他有藉口。”
他离开小厨房门口。白莎听到他在另外一间房里拨电话,听到他低声说话,他又回来站在小厨房门口。
“好了,白莎。他会在办公室等我们。他不要我们去他家里,说是他的小姨子偷听我们在谈什么。”
白莎没有搭腔。
善楼故意大声地打了一个哈欠,自己走出去选了最舒服的一张椅子坐下来。他把腿伸直,打开今天的报纸,翻到体育版。
白莎把盘子、杯子、刀叉放在她早餐小桌上。
“告诉我一些便衣条子的习惯好吗?”她问宓警官。
“哪一方面的?”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脱不脱帽子?”
“不行,那会失掉他们社会地位的。他们只在洗澡时才脱帽。”
“你那个蛋要煮多熟?”
“三分十五秒——再说一下,不是“那个蛋’,而是‘那些蛋’,多数。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白莎把—只盘子重重碰到桌上,几乎擦破了。“喂你吃早餐有一个困难,”她说:“那根死臭的雪茄在嘴巴里,不知你怎样喝咖啡?”
宓善楼不回答。他正在细读一则拳击的报导,那拳赛他昨晚也在场观赏,他要把记者的报导和自己的意见比对一下。
“好了,”柯白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