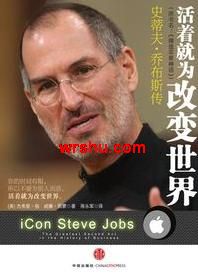活着-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余华
正文
中文版自序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原则,可是要捍卫这个原则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长时期的痛苦,因为内心并非时时刻刻都是敞开的,它更多的时候倒是封闭起来,于是只有写作,不停地写作才能使内心敞开,才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灵感这时候才会突然来到。
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轻微很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
事实上我只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为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
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他们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会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过去的现实虽然充满了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想象和个人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会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正像一位诗人所表达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威廉·福克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而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描写现实,可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现实的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点,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谣《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海盐,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日文版自序
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现在,当角川书店希望我为《活着》写一篇序言时,我想谈谈另外一个话题。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贺知章的《回乡偶记》说得就是时间带来的喜悦和辛酸: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讲述了一个由时间创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护的少年,资质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护独自来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处花木丛萃的庭院,占地一亩却寂若无人。崔护扣门良久,有一少女娇艳的容貌在门缝中若隐若现,简单的对话之后,崔护以“寻春独行,酒渴求饮”的理由进入院内,崔护饮水期间,少女斜倚着一棵盛开着桃花的小树,“妖恣媚态,绰有余妍”。两人四目相视,久而久之。崔护告辞离去时,少女送至门口。此后的日子里,崔护度日如年,时刻思念着少女的容颜。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终于再次起身前往城南,来到庭院门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是人去院空,门上一把大锁显得冰凉和无情。崔护在伤感和叹息里,将一首小诗题在了门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简短的故事说出了时间的意味深长。崔护和少女之间除了四目相视,没有任何其他的交往,只是夜以继日的思念之情,在时间的节奏里各自流淌。在这里,时间隐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着两个人的命运。我们的阅读无法抚摸它,也无法注视它,可是我们又时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来到一样,我们不能注视也不能抚摸,我们只能浑身发抖地去感受。就这样,什么话都不用说,什么行为都不用写,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也可以更短暂或者更漫长,崔护和少女玉洁冰清的恋情便会随风消散,便会“人面不知何处去”。类似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随处可见,让时间中断流动的叙述,然后再从多年以后开始,这时候决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铺垫,也不需要解释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文学的叙述里,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另一个例子来自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当但丁写到箭离弦击中目标时,他这样写:“箭中了目标,离了弦。”这诗句的神奇之处在于但丁改变了语言中的时间顺序,让我们顷刻间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速度。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不仅仅创造了故事和情节的神奇,同时也创造了句子和细节的神奇。
我曾经在两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里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一部是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两部作品异曲同工,它们都是由时间创造出了叙述,让时间帮助着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与此同时,文学叙述中的时间还造就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和《百年孤独》的故事和神奇,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简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学叙述的品质,这就是时间的神奇。就像树木插满了森林一样,时间的神奇插满了我们的文学。
最后我应该再来说一说《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余华 北京,2002年1月17日
韩文版自序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部作品,这样的任务交给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韩国的读者能够容忍我的冒险。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