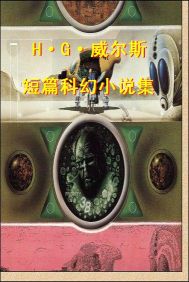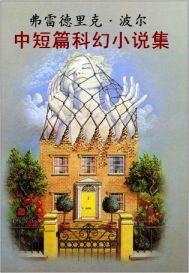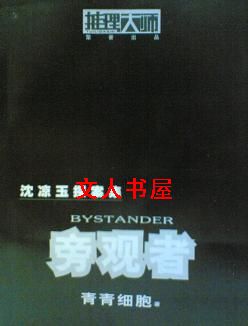蛤藻集-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他没办法。”
“什么?又没办法?这小子又要升官了!”宋伯公咬上嘴唇,象是想着点什么。
“没办法就又要升官了?”我有点惊异。
“你看,我这儿不是想哪吗?”
我不敢再紧问了,他要说一件事就要说完全了,我必须忍耐的等他想。虽然我的惊异使我想马上问他许多问题,可是我不敢开口;“凭他那个神气,怎能当上秘书长?”这句最先来到嘴边上的,我也咽下去。
我忍耐的等着他,好象避雨的时候渴望黑云裂开一点那样。不久——虽然我觉得仿佛很久——他的眼球里透出点笑光来,我知道他是预备好了。
“哼!”他出了声:“够写篇小说的!”
“说吧,下午请你看电影!”
“值得看三次电影的,真的!”宋伯公知道他所有的故事的价值:“你知道,孟秘书长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一点不瞎吹!同系同班,真正的同学。那时候,他就是个重要人物:学生会的会长呀,作各种代表呀,都是他。”
“这家伙有两下子?”我问。
“有两下子?连半下子也没有!”
“因为——”
“因为他连半下子没有,所以大家得举他。明白了吧?”“大家争会长争得不可开交,”我猜想着:“所以让给他作,是不是?”
宋伯公点了点头:“人家孟先生的本事是凡事无办法,因而也就没主张与意见,最好作会长,或作菩萨。”“学问许不错?”没有办事能干的人往往有会读书的聪明,我想。
“学问?哈哈!我和他都在英文系里,人家孟先生直到毕业不晓得莎士比亚是谁。可是他毕了业,因为无论是主任、教授、讲师,都觉得应当,应当,让他毕业。不让他毕业,他们觉得对不起人。人家老孟四年的工夫,没在讲堂上发过问。哪怕教员是条驴呢,他也对着书本发楞,一声不出。教员当然也不问他;即使偶尔问到他,他会把牙露出来,把眼珠收起去,那么一笑。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学生,当然得毕业。既准他毕业,大家就得帮助他作卷子,所以他的试卷很不错,因为是教员们给作的。自然,卷子里还有错儿,那可不是教员们作的不好,是被老孟抄错了;他老觉得M和N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把name写成mane,在他,一点也不算出奇。把这些错儿应扣的分数减去,他实得平均分数八十五分,文学士。来碗茶……
“毕业后,同班的先后都找到了事;前些年大学毕业生找事还不象现在这么难。老孟没事。有几个热心教育的同学办了个中学,那时候办中学是可以发财的。他们听说老孟没事,很想拉拔他一把儿,虽然准知道他不行;同学到底是同学,谁也不肯看着他闲起来。他们约上了他。叫他作什么呢,可是?教书,他教不了;训育,他管不住学生;体育,他不会,他顶好作校长。于是他作了校长。他一点不晓得大家为什么让他作校长,可是他也不骄傲,他天生来的是馒首幌子——馒头铺门口放着的那个大馒头,大,体面,木头作的,上着点白漆。
“一来二去不是,同学们看出来这位校长太没用了,可是他既不骄傲,又没主张,生生的把他撵了,似乎不大好意思。于是大家给他运动了个官立中学的校长。这位馒头幌子笑着搬了家。这时候,他结了婚,他的夫人是自幼定下的。她家中很有钱,兄弟们中有两位在西洋留学的。她可是并不认识多少字,所以很看得起她的丈夫。结婚不久,他在校长的椅子上坐不牢了;学校里发生了风潮,他没办法。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兄由西洋回来,得了博士;回来就作了教育部的秘书。老孟一点主意没有,可也并不着急:倒慌了教育局局长——那时候还不叫教育局;管它叫什么呢——这玩艺,免老孟的职简直是和教育部秘书开火;不免职吧,事情办不下去。局长想出条好道,去请示部秘书好了。秘书新由外国回来,还没完全把西洋忘掉,‘局长看着办吧。不过,派他去考查教育也好。’局长鞠躬而退;不几天,老孟换了西装,由馒头改成了面包。临走的时候,他的内兄嘱咐他:不必调查教育,安心的念二年书倒是好办法,我可以给你办官费。再来碗热的……
“二年无话,赶老孟回到国来,博士内兄已是大学校长。校长把他安置在历史系,教授。孟教授还是不骄傲,老实不客气的告诉系主任:东洋史,他不熟;西洋史,他知道一点;中国史,他没念过。系主任给了他两门最容易的功课,老孟还是教不了。到了学年终,系主任该从新选过——那时候的主任是由教授们选举的——大家一商议,校长的妹夫既是教不了任何功课,顶好是作主任;主任只须教一门功课就行了。老孟作了系主任,一点也不骄傲,可是挺喜欢自己能少教一门功课,笑着向大家说:我就是得少教功课。好象他一点别的毛病没有,而最适宜当主任似的。有一回我到他家里吃饭,孟夫人指着脸子说他:‘我哥哥也溜过学,你也溜过学,怎么哥哥会作大校长,你怎就不会?’老孟低着头对自己笑了一下:‘哼,我作主任合适!’我差点没别死,我不敢笑出来。“后来,他的内兄校长升了部长,他作了编译局局长。叫他作司长吧,他看不懂公事;叫他作秘书吧,他不会写;叫他作编辑委员吧,他不会编也不会译,况且职位也太低。他天生来的该作局长,既不须编,也无须译,又不用天天办公。‘哼,我就是作局长合适!’这家伙仿佛很有自知之明似的。可是,我俩是不错的朋友,我不能说我佩服他,也不能说讨厌他。他几乎是一种灵感,一种哲理的化身。每逢当他升官,或是我自己在事业上失败,我必找他去谈一谈。他使我对于成功或失败都感觉到淡漠,使我心中平静。由他身上,我明白了我们的时代——没办法就是办法的时代。一个人无须为他的时代着急,也无须为个人着急,他只须天真的没办法,自然会在波浪上浮着,而相信:‘哼,我浮着最合适。’这并不是我的生命哲学,不过是由老孟看出来这么点道理,这个道理使我每逢遇到失败而不去着急。再来碗茶!”
他喝着茶,我问了句:“这个人没什么坏心眼?”“没有,坏心眼多少需要一些聪明;茶不错,越焖越香!”宋伯公看着手里的茶碗。“在这个年月,凡要成功的必须掏坏;现在的经济制度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制度。掏了坏,成了功;可不见就站得住。三摇两摆,还得栽下来;没有保险的事儿。我说老孟是一种灵感,我的意思就是他有种天才,或是直觉,他无须用坏心眼而能在波浪上浮着,而且浮得很长久。认识了他便认识了保身之道。他没计划,没志愿,他只觉得合适,谁也没法子治他。成功的会再失败;老孟只有成功,无为而治。”
“可是他有位好内兄?”我问了一句。
“一点不错;可是你有那么位内兄,或我有那么位内兄,照样的失败。你,我,不会觉得什么都正合适。不太自傲,便太自贱;不是想露一手儿,便是想故意的藏起一招儿,这便必出毛病。人家老孟自然,糊涂得象条骆驼,可是老那么魁梧壮实,一声不出,能在沙漠里慢慢溜达一个星期!他不去找缝子钻,社会上自然给他预备好缝子,要不怎么他老预备着发笑呢。他觉得合适。你看,现在人家是秘书长;作秘书得有本事,他没有;作总长也得有本事,而且不愿用个有本事的秘书长;老孟正合适。他见客,他作代表,他没意见,他没的可泄露,他老笑着,他有四棱脑袋,种种样样他都合适。没人看得起他,因而也没人忌恨他;没人敢不尊敬他,因为他作什么都合适,而且越作地位越高。学问,志愿,天才,性格,都足以限制个人事业的发展,老孟都没有。要得着一切的须先失去一切,就是老孟。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我看将来的总统是给他预备着的。你爱信不信!”
“他连一点脾气都没有?”
“没有,纯粹顺着自然。你看,那天我找他去,正赶上孟太太又和他吵呢。我一进门,他笑脸相迎的:‘哼,你来得正好,太太也不怎么又炸了。’一点不动感情。我把他约出去洗澡,喝!他那件小褂,多么黑先不用提,破的就象个地板擦子。‘哼,太太老不给做新的吗。’这只是陈述,并没有不满意的意思。我请他洗了澡,吃了饭,他都觉得好:‘这澡堂子多舒服呀!这饭多好吃呀!’他想不起给钱,他觉得被请合适。他想不起抓外钱,可是他的太太替他收下‘礼物’,他也很高兴:‘多进俩钱也不错!’你看,他歪打正着,正合乎这个时代的心理——礼物送给太太,而后老爷替礼物说话。他以自己的胡涂给别人的聪明开了一条路。他觉得合适,别人也觉得合适。他好象是个神秘派的诗人,默默中抓住种种现象下的一致的真理。他抓到——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
“先喝一盅吧?”我让他。
他好象没听见。“这象篇小说不?”
“不大象,主角没有强烈的性格!”我假充懂得文学似的。“下午的电影大概要吹?”他笑了笑。“再看看樱花去也好。”
“准请看电影,”我给他斟上一盅酒。“孟先生今年多大?”“比我——想想看——比我大好几岁呢。大概有四十八九吧。干吗?呕,我明白了,你怕他不够作总统的年纪?再过几年,五十多岁,正合适!”
新时代的旧悲剧
一
“老爷子!”陈廉伯跪在织锦的垫子上,声音有点颤,想抬起头来看看父亲,可是不能办到;低着头,手扶在垫角上,半闭着眼,说下去:“儿子又孝敬您一个小买卖!”说完这句话,他心中平静一些,可是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一种渺茫的平静,象秋夜听着点远远的风声那样无可如何的把兴奋、平静、感慨与情绪的激动,全融化在一处,不知怎样才好。他的两臂似乎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