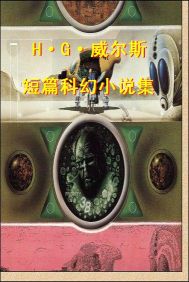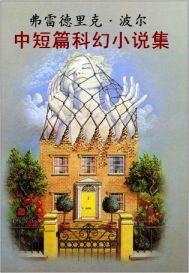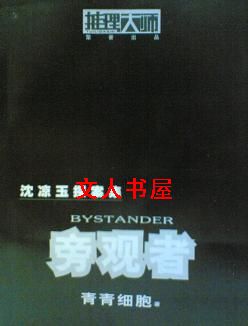蛤藻集-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不知道!”包善卿颤得更厉害了。“她要是想要钱,要衣裳,要车,都可以呀,跟我明说好了;何必满街去喊呢!疯了?卖国贼,爸爸是卖国贼,好听?混账,不要脸!”
电话!没人去接。方文玉已经瘾得不爱动,包善卿气得起不来。
张七等铃响了半天,搭讪着过去摘下耳机。“……等等。大人,公安局冯秘书。”
“挂上,没办法!”包善卿躺在沙发上。
“陈升!陈升!”方文玉低声地叫。
陈升就在院里呢,赶快进来。
方文玉向里院那边指了指,然后撅起嘴唇,象叫猫似的轻轻响了几下。
陈升和张七一同退出去。
新韩穆烈德
一
有一次他稍微喝多了点酒,田烈德一半自嘲一半自负的对个朋友说:“我就是莎士比亚的韩穆烈德;同名不同姓,仿佛是。”
“也常见鬼?”那个朋友笑着问。
“还不止一个呢!不过,”田烈德想了想,“不过,都不白衣红眼的出来巡夜。”
“新韩穆烈德!”那个朋友随便的一说。
这可就成了他的外号,一个听到而使他微微点头的外号。
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非常的自负,非常的严重,事事要个完整的计划,时时在那儿考虑。越爱考虑他越觉得凡事都该有个办法,而任何办法——在细细想过之后——都不适合他的理想。因此,他很愿意听听别人的意见,可是别人的意见又是那么欠高明,听过了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使他迷乱,使他得顺着自己的思路从头儿再想过一番,才能见着可捉摸的景象,好象在暗室里洗像片那样。
所以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可爱,也很可怜。他常常对着镜子看自己,长瘦的脸,脑门很长很白。眼睛带着点倦意。嘴大唇薄,能并成一条长线。稀稀的黑长发往后拢着。他觉得自己的相貌入格,奇…书…网不是普通的俊美。
有了这个肯定的认识,所以洋服穿得很讲究,在意。凡是属于他的都值得在心,这样才能使内外一致,保持住自己的优越与庄严。
可是看看脸,看看衣服,并不能完全使他心中平静。面貌服装即使是没什么可指摘的了,他的思想可是时时混乱,并不永远象衣服那样能整理得齐齐楚楚。这个,使他常想到自己象个极雅美的磁盆,盛着清水,Qī。shū。ωǎng。可是只养着一些浮萍与几团绒似的绿苔!自负有自知之明,这点点缺欠正足以使他越发自怜。
二
寒假前的考试刚完,他很累得慌,自己觉得象已放散了一天的香味的花,应当敛上了瓣休息会儿。他躺在了床上。
他本想出去看电影,可是躺在了床上。多数的电影片是那么无聊,他知道;但是有时候他想去看。看完,他觉得看电影的好处只是为证明自己的批评能力,几乎没有一片能使他满意的。他不明白为什么一般人那样爱看电影。及至自己也想去看去的时候,虽然自信自己的批评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可是究竟觉得有点不大是味儿,这使他非常的苦恼。“后悔”破坏了“享受”。
这次他决定不去。有许多的理由使他这样下了决心。其中的一个是父亲没有给他寄了钱来。他不愿承认这是个最重要的理由,可是他无法不去思索这点事儿。
二年没有回家了。前二年不愿回家的理由还可以适用于现在,可是今年父亲没有给寄来钱。这个小小的问题强迫着他去思索,仿佛一切的事都需要他的考虑,连几块钱也在内!回家不回呢?
三
点上支香烟,顺着浮动的烟圈他看见些图画。
父亲,一个从四十到六十几乎没有什么变动的商人,老是圆头圆脸的,头剃得很光,不爱多说话,整个儿圆木头墩子似的!
田烈德不大喜欢这个老头子。绝对不是封建思想在他心中作祟,他以为;可是,可是,什么呢?什么使他不大爱父亲呢?客观的看去,父亲应当和平常一件东西似的,无所谓可爱与不可爱。那么,为什么不爱父亲呢?原因似乎有很多,可是不能都标上“客观的”签儿。
是的,想到父亲就没法不想到钱,没法不想到父亲的买卖。他想起来:兴隆南号,兴隆北号,两个果店;北市有个栈房;家中有五间冰窖。他也看见家里,顶难堪的家里,一家大小终年在那儿剥皮:花生,胡桃,榛子,甚至于山楂,都得剥皮。老的小的,姑娘媳妇,一天到晚不识闲,老剥老挑老煮。赶到预备年货的时节就更了不得,山楂酪,炒红果,山楂糕,~X桲,玫瑰枣,都得煮,拌,大量的加糖。人人的手是黏的,人人的手红得和胡萝卜一样。到处是糊糖味,酸甜之中带着点象烫糊了的牛乳味,使人恶心。
为什么老头子不找几个伙计作这些,而必定拿一家子人的苦力呢?田烈德痛快了些,因为得到父亲一个罪案——一定不是专为父亲卖果子而小看父亲。
更讨厌的是收蒜苗的时候:五月节后,蒜苗臭了街,老头子一收就上万斤,另为它们开了一座窖。天上地下全是蒜苗,全世界是辣蒿蒿的蒜味。一家大小都得动手,大捆儿改小捆儿,老的烂的都得往外剔,然后从新编辫儿。剔出来的搬到厨房,早顿接着晚顿老吃炒蒜苗,能继续的吃一个星期,和猪一样。
五月收好,十二月开窖,蒜苗还是那么绿,拿出去当鲜货卖。钱确是能赚不少,可是一家子人都成了猪。能不能再体面一些赚钱呢?
四
把烟头扔掉,他不愿再想这个。可是,象夏日天上的浮云,自自然然的会集聚到一处,成些图画,他仿佛无法阻止住心中的活动。他刚放下家庭与蒜苗,北市的栈房又浮现在眼前。在北市的西头,两扇大黑门,门的下半截老挂着些马粪。门道非常的脏,车马出入使地上的土松得能陷脚;时常由蹄印作成个小湖,蓄着一汪草黄色的马尿。院里堆满了荆篓席筐与麻袋,骡马小驴低头吃着草料。马粪与果子的香气调成一种沉重的味道,挂在鼻上不容易消失。带着气瘰脖的北山客,精明而话多的西山客,都拐着点腿出来进去,说话的声音很高,特别在驴叫的时候,驴叫人嚷,车马出入,栈里永远充满了声音;在上市的时候,栈里与市上的喧哗就打成一片。
每一张图画都含着过去的甜蜜,可是田烈德不想只惆怅的感叹,他要给这些景象加以解释。他想起来,客人住栈,驴马的草料,和用一领破席遮盖果筐,都须出钱。果客们必须付这些钱,而父亲的货是直接卸到家里的窖中;他的栈房是一笔生意,他自己的货又无须下栈,无怪他能以多为胜的贱卖一些,而把别家果店挤得走投无路。
父亲的货不从果客手中买,他直接的包山。田烈德记得和父亲去看山园。总是在果木开花的时节吧,他们上山。远远的就看见满山腰都是花,象青山上横着条绣带。花林中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蜜蜂飞动的轻响。小风吹过来,一阵阵清香象花海的香浪。最好看的是走到小山顶上,看到后面更高的山。两山之间无疑的有几片果园,分散在绿田之间。低处绿田,高处白花,至高处黄绿的春峰,倚着深蓝的晴天。山溪中的短藻与小鱼,与溪边的白羊,更觉可爱,他还记得小山羊那种娇细可怜的啼声。
可是父亲似乎没觉到这花与色的世界有什么美好。他嘴中自言自语的老在计算,而后到处与园主们死命的争竞。他们住在山上等着花谢,处处落花,舞乱了春山。父亲在这时节,必强迫着园主承认春风太强,果子必定受伤,必定招虫。有这个借口,才讲定价钱;价钱讲好,园主还得答应种种罚款:迟交果子,虫伤,雹伤,水锈,都得罚款。四六成交账,园主答应了一切条件,父亲才交四成账。这个定钱是庄家们半年的过活,没它就没法活到果子成熟的时期。为顾眼前,他们什么条件也得答应;明知道条件的严苛使他们将永成为父亲的奴隶。交货时的六成账,有种种罚项在那儿等着,他们永不能照数得到;他们没法不预支第二年的定银……父亲收了货,等行市;年底下“看起”是无可疑的,他自己有窖。他是干鲜果行中的一霸!
五
这便有了更大的意义:田烈德不是纯任感情而反对父亲的;也不是看不起果商,而是为正义应当,应当,反对父亲。他觉得应当到山园去宣传合作的方法,应当到栈房讲演种种“用钱”的非法,应当煽动铺中伙计们要求增高报酬而减轻劳作,应当到家里宣传剥花生与打山楂酪都须索要工钱。
可是,他二年没回家了。他不敢回家。他知道家里的人对于那种操作不但不抱怨,而且觉得足以自傲;他们已经三辈子是这样各尽所能的大家为大家效劳。他们不会了解他。假若他一声不出呢,他就得一天到晚闻着那种酸甜而腻人的味道,还得远远的躲着大家,怕溅一身山楂汤儿。他们必定会在工作的时候,彼此低声的讲论“先生”;他是在自己家中的生人!
他也不敢到铺中去。那些老伙计们管他叫“师弟”,他不能受。他有很重要的,高深的道理对他们讲;可是一声“师弟”便结束了一切。
到栈房,到山上?似乎就更难了。
啊!他把手放在脑后,微微一笑,想明白了。这些都是感情用事,即使他实地的解放了一两家山上的庄家户,解放了几个小伙计与他自己的一家人,有什么用?他所追求的是个更大的理想,不是马上直接与张三或李四发生关系的小事,而是一种从新调整全个文化的企图。他不仅是反对父亲,而且反抗着全世界。用全力捉兔,正是狮的愚蠢,他用不着马上去执行什么。就是真打算从家中作起——先不管这是多么可笑——他也得另有办法,不能就这么直入公堂的去招他们笑他。
暂时还是不回家的好。他从床上起来,坐在床沿上,轻轻提了提裤缝。裤袋里还有十几块钱,将够回家的路费。没敢去摸。不回家!关在屋中,读一寒假的书。从此永不回家,拒绝承袭父亲的财产,不看电影……专心的读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