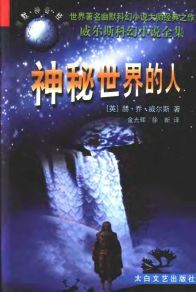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视觉设计、既完整又好笑的账目记录(周薪十元的石匠,非但作古已久,技巧与秘诀也跟着进了坟墓)。奇怪的是,书中还说明了哪种房子适合哪种个性、哪种行业的人。他把书放回去。
他抽出第二本,它几乎是第一本的两倍厚。上面写着“第四版,小布朗,波士顿,一八九八年”。里面有张卷首画,是悲伤的德林克沃特肖像,用软铅笔绘成。史墨基隐约认出了艺术家那个带有连字符的双名。写满了字的扉页上有一段题词:我起身,再将之拆除。雪莱。照片都是一样的,但多了一组图表,上面全是平面图,史墨基完全看不懂上面的标注。
第六版就是最后一版,是装订精美的厚重大书,运用新艺术风格的淡紫色。书名的字体仿佛要长出四肢似的延伸出卷曲的线条,整体而言仿佛映照在一座傍晚时分开满百合花、泛着涟漪的池塘上。这次的卷首画上不是德林克沃特本人,而是他妻子,是一张很像素描的照片,有炭笔画的烟熏感,五官模糊。也许这不是什么艺术效果;也许她就像史墨基一样并不总是完全存在,但她很美。书中还有题诗,书信,一大堆序言、前言和绪论,红字黑字都有。接着又是那些小屋,跟往常一样,只是这回看起来既落伍又突兀,就像被卷进现代潮流里的一座平凡小镇。瓦奥莱特的抄写员仿佛努力在那一页又一页大写的抽象概念上保持某种理智(随着书愈来愈厚,字体也愈来愈小),因此基本上每一页都会出现批注,此外还有题词、章节标题,以及所有那些能把一段文字转换成一个对象的相关事物,尽是些清晰、富逻辑却不值一读的东西。卷尾的空白页后面还附了一张图纸或地图,折了好几折,事实上还颇有厚度。纸质很薄,因此史墨基一开始不知该如何把它摊开。他先试了一个方向,结果有道古老的折痕就这样嘶的一声微微裂开,他抽搐了一下,重新尝试。他瞥见某些部分,看出那是一张巨大的设计图,但设计的是什么呢?最后他终于把它全部摊开了。图正面朝下搁在他腿上,他只需把它翻过来就好。但此时他却停驻不前,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上面是什么。我想你应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吧,医生这么说过。他把它从边缘掀起。由于年代久远、纸质细致,它就像飞蛾翅膀般轻轻飘起,一道阳光从背面穿透,于是他瞥见了写满注解的复杂图像。他把它放下来研究。
与此同时
“她到底会不会去,克劳德?”妈妈问,而克劳德姑婆回答:“好啦,好像不会。”但她不肯再多说,只是坐在桌子另一端,香烟在阳光下释出朦胧烟雾。妈妈正在做馅饼,面粉一路沾到手肘,尽管她喜欢把这称作不花脑筋的工作,但事实却非如此。事实上,她发现自己思路最清晰、想法最敏锐的时候往往就是烹饪时;她可以在身体忙碌的情形下完成其他时候做不到的事,例如将她的烦恼编排列队,每一队都由一份希望主导。有时她会在煮饭时突然想起遗忘已久的诗歌,或用先生、孩子、先父或她尚未出生但已能清晰预见的孙辈(有三个已毕业的女孩和一个清瘦忧郁的男孩)的语言说话。她对天气了如指掌。她把玻璃馅饼盘放进呼呼吐着热气的烤箱内,说不久就会有场暴风雨。克劳德姑婆没有响应,只是叹口气、吸口烟,用一条小手帕擦擦她满是皱纹的脖子上的汗,然后将它仔细塞回袖子里。“晚点就会清朗很多了。”她说完随即缓缓走出厨房,穿越大厅回到她的房间,看能不能在晚餐前小睡一会儿。她曾在这张宽大的羽毛床上跟哈维·克劳德度过短短几年同枕共眠的时光。躺下前她望向了山丘,确实看见有白色的积云往那儿集结,带着胜利的姿态节节攀升。索菲无疑是对的。她躺在那儿想:至少他是来了,而且没有造成任何冲突。其余的事她就不知道了。
与此同时,戴着低顶宽边帽的德林克沃特医生气喘吁吁地在“老石墙”旁停下脚步。这道围墙,也就是那片长满昆虫的多岩之地,分隔了“绿野”和“老牧野”,一路通到荷塘边缘。血压造成的嗡嗡声逐渐退去,因此他开始听得见他唯一关注的那出戏码:啁啾不停的鸟语、不成调的蝉鸣,以及上千生物进进出出的窸窣声。人类曾经插手于这块土地,但现在多半已经抽离。他可以在荷塘对岸的远方看见布朗家谷仓的屋顶,知道这片牧野已遭那家人遗弃,而这道古墙正是他们所留下的遗迹。景色因人类事业的进驻而变化多端,多出了大大小小的房屋、绵延的围墙、阳光明媚的牧野、池塘。医生认为这似乎才是“生态”一词的真义,他不时会在大城报上看到这个词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专栏里遭到误用。当他坐在一块长着青苔的温暖岩石上聚精会神时,一阵微风吹来,告诉他傍晚时分就会有一朵来自山间的云在此地化成雨水落下。
同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瓦奥莱特·布兰波的两个曾孙女就躺在索菲房里那张宽大的羽毛床上。黛莉·艾丽斯隔天要穿(这辈子可能只穿这么一次)的浅色长裙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柜外,在衣柜门上的镜中映出一模一样的倒影,背对着背。裙子下方和周围也缀满配件。索菲和姊姊赤身裸体,躺在午后的暑热中。索菲的手扫过了姊姊汗湿的身侧,因此黛莉·艾丽斯说:“哎,真的太热了。”但却觉得妹妹沾在她肩上的泪水更加滚烫。她说:“不久就会轮到你了。你会选中一个人,也可能被人选中,到时候你也会成为六月新娘。”但索菲说:“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接下来的话艾丽斯就听不到了,因为索菲把脸埋在姊姊的脖子上喃喃低语。索菲说的是:“ 他永远不会理解、永远不会看见,他们永远不会让他得到跟我们一样的东西。他会跑到不该去的地方、看见不该看的东西,永远看不出哪里有门、哪里该转弯。等着看好了,你尽管等着看。”就在这一刻,克劳德姑婆也在思考这件事,想着他们若等一等不知会看到什么。她们的母亲也感受到这点,但不是出自普通的好奇心,而是在刺探各种可能性。史墨基则以为此时是周日的休息时间,于是独自留在那满是尘埃的黑暗书房里,将整张图在面前摊开。而就在这一刻,这件事也让他浑身战栗,如一道火焰般蹿起、永不止息。
Ⅲ
山脚下住着一个老太太,
她若还在人间,就依然住在那里。
上个世纪末一个愉快的夏天,约翰·德林克沃特以看房子的名义到英国进行了一趟徒步之旅。某天傍晚,他来到柴郡一栋红砖造的牧师宅邸大门前。他迷路了,而且还搞丢了导览手册,因为几小时前他在一座磨坊旁吃午餐时,手册不小心掉到了磨坊的水槽里。现在他饿了,而不管英国乡间有多么安全可爱,他还是不禁感到不安。
古怪的内部
牧师宅邸里有一座无人照料、杂草丛生的花园,蝶儿在茂密的玫瑰丛间飞舞,鸟儿则在一棵多瘤而姿态跋扈的苹果树上啁啾跳跃。树杈上坐着一个人,刚好点燃一根蜡烛。为什么是蜡烛?那是一名白衣少女,正用双手护着蜡烛,火光忽隐忽现。她说(但不是对他说):“ 怎么了?”烛火瞬间熄灭。他说:“不好意思。”她从树上迅速敏捷地爬下来,因此他赶紧站得离大门远些,以免在她过来跟他说话时显得无礼莽撞。但少女没有过来。此时从某处(或者说是从每一个角落)传来一阵夜莺的歌声,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开始。
他不久前才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是真正的十字路口;虽然过去这一个月来,他也面临过不少抉择,必须决定要向下前往水边,还是往上越过山丘,但他发现这些历练对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他并无多大帮助)。他熬过了一年,设计出一栋巨大的摩天楼,必须在尺寸与用途容许的前提下,尽可能让外观看起来像座十三世纪的教堂。他把第一份设计图草稿送去给客户时,原本是把它当成一个玩笑、一种狂想,甚至是一种消遣,理应会遭到退件;但那客户没看出他这点心思,言明就要他的摩天楼盖成这种样子,就要它成为一座商业教堂。而约翰·德林克沃特没料到的是,连那状似受洗盆的黄铜信箱他也要,还有那些克吕尼式的古怪浅浮雕(描绘小矮人在打电话或阅读收报机上的纸带),还有位于建筑物高处、根本不会有人看到的怪兽饰,而且怪兽饰脸上就长着跟客户本人一样的凸眼睛和草莓鼻(但那家伙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客户认为没什么是他办不到的,所以现在一切都要完全按照德林克沃特的设计去进行。
这项计划不断拖延的同时,他差点就经历一场转变。就差一点,幸而他成功避掉了。那似乎是种非自身的东西,呼之欲出却又说不上来。一开始他是注意到有种东西迂回侵入了他忙碌但规律又充满古怪白日梦的生活:只是一些抽象的字眼,但却会突然浮现脑海,就好像有个声音将它念出来似的。其中一个是“多样性”。还有一天,当他坐在大学俱乐部里望着窗外的蒙蒙烟雨时,浮现的是“组合”二字。一旦说出口,这个概念就会占据他全部的心思,一路蔓延到他的工作场所和会计室,让他陷入瘫痪,无法将心思放在人称“昙花一现”的事业上,将构思已久的下一步付诸行动。
他感觉自己正缓缓陷入一场漫长的梦境,也可能正从一场梦中醒来。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都不希望发生。为了抵抗,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他阅读斯韦登堡和奥古斯丁的作品,而最能抚慰他的莫过于阿奎那:他几乎可以感受到这位众人眼中的“天使博士”正在一字一句完成他的伟大著作《神学大全》。他后来才知道阿奎那临终前竟把自己写的一切视为“一堆稻草”。
一堆稻草。德林克沃特坐在“毛斯、德林克沃特暨石东建筑事务所”开着天窗的长形办公室内,瞪着他建造的那些高塔、公园和豪宅的黑白照片,心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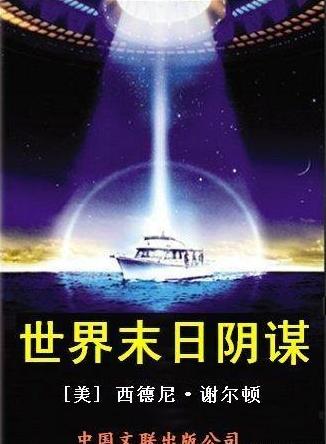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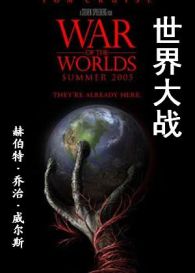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