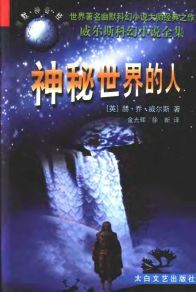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就好了。我们决定的做法是对的。倘若罗素·艾根布里克真是这位皇帝,或者已经让够多人相信他是(对了,我注意到他一直拒绝宣布自己的身份,真神秘),那么他对我们应该是有用而不是有害。”
“可以容我问一句吗?”霍克斯奎尔说,挥手要端着酒杯与醒酒瓶站在门边的石女进来,“你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文人小说下载
吵桥棍棒与枪支俱乐部的人靠回椅背上,露出微笑。“选举。”其中一个会员说,他是对霍克斯奎尔的结论抗议得最严重的人之一。“某些江湖郎中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他继续说道,“这是我们从去年夏天的游行暴动里学到的事。像万街教堂的骚乱等等。当然了,这种力量通常都是昙花一现。不是真正的力量。都只是虚张声势,真的。全是些转眼即逝的风暴。而他们也知道这点……”
“但是,”另一个会员说,“当这样一号人物接触到真正的权力分子,被应允分到一杯羹、意见被采纳、虚荣心受到吹捧时……”
“就可以吸收他了。说白一点就是可以利用。”
“你知道,”资深会员挥手表示他不喝饮料,“综观大局,罗素·艾根布里克没有真正的力量,他欠缺有力的支持者。只有几个穿着彩色衬衫的小丑和几个忠心人手。他到处办演讲,但到了第二天还有谁记得?他若是强烈地激起新仇、唤醒旧恨,那又是另一回事——但他没有。他谈的东西全都很模糊。所以,我们会提供他真正的盟友。他没有盟友,所以他一定会接受。我们会提供诱因。他会成为我们的人。而且利用价值可能挺他妈的高。”
“嗯哼。”霍克斯奎尔又说了一次。由于受过的都是最纯粹、层次最高的教育,她从来不觉得欺骗和隐瞒是件容易的事。罗素·艾根布里克没有盟友是事实,没错。但她理应让他们知道他其实是某些更强大、更难以名状、更阴险的势力所派出来的爪牙,虽然她还说不上来这些势力是什么。然而她现在已经跟这个案子毫无关系。况且他们八成也不会听她的,她可以从他们沾沾自喜的脸上看出这点。但想起自己知情不报的事,她还是涨红了脸,说:“我打算喝一杯。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喝吗?”
“至于那笔费用,”有个会员说,在她帮他倒酒时紧盯着她看,“当然不必退还。”
她对他点点头。“你们打算何时执行计划?”
“下礼拜的今天,”资深会员说,“我们会在他的旅馆里跟他碰面。”他起身环顾四周,准备离去。那些拿了饮料的会员纷纷连忙喝光。“很抱歉,”资深会员说,“您花了这么多力气,结果我们还是决定自行解决。”
“这样也好。”霍克斯奎尔说,并未起身。
此时他们全站了起来,以造作的姿态面面相觑,表达了深思的怀疑或怀疑的深思,接着就静静离去。其中一人出门时还说希望她没受冒犯,而其他人各自上车时也都在思考这样的可能:倘若她真被冒犯了,那么对他们而言会意味着什么。
霍克斯奎尔也独自思忖着这件事。
卸下了俱乐部托付的事,她就是个自由人了。倘若一个新的旧帝国正在重新崛起,那么她的力量就能获得更新更广的视野。跟大多数伟大巫师一样,霍克斯奎尔对权力的诱惑也未能免疫。
然而并没有什么新时代即将展开。说到最后,罗素·艾根布里克背后的力量说不定还比不上俱乐部的力量。
她该站在哪一边呢?倘若她能够分辨哪一边是哪一边的话?
她看着白兰地在酒杯上留下的印记。一个礼拜后的今天……她摇铃召来石女,命令她泡咖啡,准备彻夜工作——时间太少,不能睡觉了。
不为人知的悲伤
天亮后,她筋疲力尽但毫无斩获地下楼,踏上鸟鸣阵阵的街道。
她高耸狭长的房子对面有一座小公园,原本是公共公园,现在却已大门深锁。只有公园周围那些房屋与私人俱乐部的人握有钥匙,可以打开铸铁大门。霍克斯维尔就有一把。这座公园里满是雕像、喷泉和鸟澡盆之类的装饰品,很少能让她精神一振,因为她已经不止一次把它当成某种笔记纸,顺着太阳移动的方向在它的外围描绘出一个中国朝代或某种神秘的数学。当然了,这些她现在都已经牢记在心。
但在五月一日这个多雾的早晨,公园一片朦胧,丝毫没有严苛的感觉。整个空气几乎不像是大城的,充满了新叶的甘甜气息,而她现在需要的正是这种模糊朦胧的感觉。
来到大门前时,她发现那儿站了个人,正抓着栏杆无望地盯着里面看,像个被关在外面的囚犯。她等了一会儿。这种时间会在外游荡的只有两种人:勤奋早起的工作者,或是一夜未眠的失意者。眼前这个人长长的外套底下似乎露出了睡裤的裤脚,但霍克斯奎尔不认为这就代表他是个早起者。她摆出贵妇的姿态(遇上这种人就是要这样),取出她的钥匙,请那男子让开一下,因为她想开门。
“也该是时候了。”他说。
“噢,不好意思。”她说,因为他只是满怀期待地往旁让了一小步,接着就企图跟着她进来,“这是座私人公园。你恐怕不能进来。只有住在周围的人可以进来,你知道吧。有钥匙的人。”
此时她已经看清楚他的脸,他长着杂乱的胡子,脸上满是脏兮兮的皱纹,却还很年轻。他剽悍但空洞的眼睛上方长着一道连在一起的眉毛。
“真他妈的不公平,”他说,“他们大家都有房子,干吗还要座公园?”他愤怒又沮丧地瞪着她。她不知道该不该向他解释他不能进入这座公园一事并没有哪里不公平,就跟他不能进入周围的房子一样。他的眼神似乎在要求她提出某种抗辩,但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只是在抱怨那种广泛存在且没有答案的不公平,也就是弗雷德·萨维奇一再指出的那种,不需要什么虚伪或特别的解释。“哦。”她说,她对弗雷德也常这么说。
“而且这该死的公园还是自己的外曾祖父盖的。”他把眼睛往上转,开始计算,“是外高祖父才对。”他突然饶有意图地掏出一只手套戴上(无名指从一个破洞里露出来),开始擦拭一块镶在老旧门柱上的牌子,把上面的新生藤蔓和尘土拨去。“看到了吗?该死。”她花了一会儿时间才看懂,很惊奇自己以前从没注意到它。几乎整个学院派公共工程史都呈现在那排列得紧密无比的罗马式版面上了,钉子的钉头还是小花的形状。牌子上写:“毛斯 德林克沃特 石东 一九○○年”。
他不是疯子。遇上这种事时,大部分大城人(特别是霍克斯奎尔)都能清楚分辨这究竟是一个疯子不可能的狂想,还是一个迷失潦倒的人不可思议却真实无比的故事。差别极其细微,却蒙混不得。“你是哪位?”她说,“毛斯、德林克沃特,还是石东?”
“我猜你一定不会知道在这座城里要找到一点宁静有多困难,”他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乞丐流浪汉吗?”
“呃……”她说。
“事实是,你只要在一张天杀的公园长椅或一个门口坐下,铁定会有十几个醉鬼和大嘴巴的人在一旁齐声吵个不停。大谈他们的人生故事。一瓶酒传来传去。大家都是死党。你知道有多少乞丐是同性恋吗?很多呢。太令人惊奇了。”嘴里说很令人惊奇,但他却一副早就知道的模样,但不管怎样都同样令人愤怒。“安详与寂静。”他又说了一次,语调里充满了真实的渴望,渴望小公园里沾着露水的郁金香花床和满是绿荫的小径,因此她说:“好吧,我猜你若是建造者的后裔,破个例也无妨。”她转动钥匙打开了门。他在门前迟疑了片刻,接着就进去。
一进入公园,他的愤怒似乎就平息了下来,而尽管原本没这个打算,她还是跟他一起走上那些古怪的蜿蜒小径。小径看似通往公园深处,但却总会让你回到外围。她知道秘诀在哪里——当然,只要踏上那些似乎通往外面的小径,你就反而会往里面走,因此她巧妙地引导他往那个方向去。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来到公园中心,那儿矗立着一座凉亭或神殿之类的东西(但她认为其实是工具间)。层层叠叠的树木和年老的灌木丛让它看起来不像实际上那么小,从某些角度看去,它甚至像是一栋大房子露出来的前廊或屋角。而尽管公园很小,但透过某种植物的排列与透视技巧,在公园的中心几乎看不到周围的城市。她开始讨论这点。
“是啊,”他说,“愈往里面去就愈大。你要来一口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平的透明瓶子。
“现在对我来说太早了。”她说。她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打开瓶盖、喝一大口,他的喉咙八成已经老练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他竟然不由自主地用力颤抖了几下,脸孔因恶心而扭曲,她自己如果喝那么一大口一定也是这种表情。还很嫩呢,她心想。其实只是个孩子。她猜想他有不为人知的悲伤,于是开心地玩味起这件事,因为她正需要换换心境,之前的工作实在太沉重了。
他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年轻人用袖子擦擦瓶口,小心翼翼地把它盖上,然后不疾不徐地把酒瓶塞回棕色外套的口袋里。真奇怪,她心想,那个玻璃瓶和里面那残酷的透明液体竟拥有此等抚慰的力量,让他如此温柔以待。“那个天杀的东西是什么?”他说。
他们面对着那座方形的石头建筑。霍克斯奎尔认为应该是工具间,只是盖成了凉亭或某种微型欢乐宫之类的模样。“我也不是很确定,”她说,“但我想上面的浮雕代表四季,一面一季。”
他们面前那一面是春天。有个希腊少女正在摆弄盆栽,手里拿着一把很像铲子的古老工具,另一手则拿着一株幼苗。一只小绵羊蜷缩在她脚边,跟她一样满脸希望与期待,散发着清新气息。这是面很不错的浮雕,艺术家透过不同的深浅创造出一种印象,仿佛远方有新翻的田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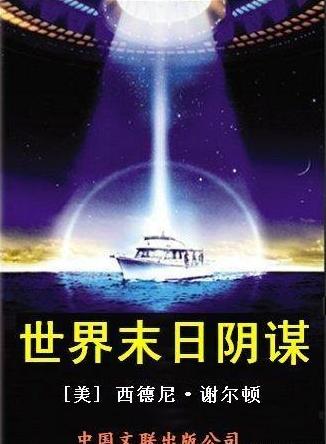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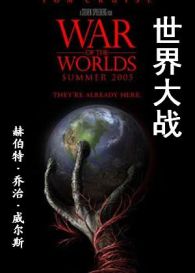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