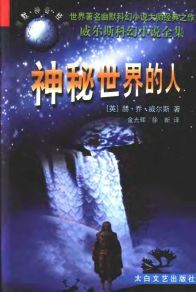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已出了神。
不,天命这种东西太沉重,不能放在椰子壳上。也太深沉,不能用油搓掉、用药草浴洗掉。若要达成西尔维的要求,若她年迈的心脏承受得了,黑婆将必须把它从西尔维身上抽出来、自己吞下去。首先必须找出它在哪里。她小心翼翼地接近西尔维的心。大部分的入口她都知道:爱情、金钱、健康、孩子。但还有一扇虚掩的门是她没见过的。“好,好。”她说,却很害怕那份天命从西尔维身上窜出、往她自己身上冲来时,她会丢了老命,或变得跟死了没两样。当她转头寻找自己的向导灵时,却发现它们全吓得跑光了。但她必须达成西尔维的要求。她把手放在那扇门上,开始将它推开,结果在门后瞥见了金色的天光,有一阵轻风和众多低沉的呢喃。
“不!”西尔维大喊,“不不不,我错了,不要!”
门砰一声关上。黑婆猛地一阵晕眩,倒回她小公寓内的椅子上。西尔维正摇晃着她。
“我收回,我收回!”西尔维大嚷。但天命从来都没有离开她。
黑婆恢复意识,用一只手拍着自己气喘吁吁的胸膛。“别再做那种事,孩子,”她说,却浑身发软地庆幸西尔维这次这么做了,“会出人命的。”
“对不起,对不起,”西尔维说,“这真是大错特错……”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黑婆说,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看着西尔维仓皇穿上外套,“休息一下。”但西尔维只想离开这房间,因为似乎有阵阵强烈的巫术如闪电般在她周围跳动。她懊悔自己竟然会想到这种馊主意,绝望地希望自己的愚蠢并没有伤及她的天命,或造成它反弹,或甚至吵醒它。她为什么就不让它安详地在原处沉睡、不去打扰任何人呢?她的心脏自责得狂跳不已,她用颤抖的手取出皮包,翻找着她为这场疯狂行为所准备的那叠钞票。
看见西尔维拿出来的钱,黑婆退了开去,仿佛觉得那钞票会咬人似的。倘若西尔维给她的是金币、是强效药草、是有褒扬力的奖章或一本玄秘之书,她就会接受,毕竟她通过了试炼,得到一点回报是应该的:但她绝对不收用来买杂货的肮脏钞票,不收千万人摸过的钱。
西尔维踏上街道匆匆离去,心想:我没事、我没事,希望事实果真如此。她当然可以不要这份天命,就像她也可以切掉鼻子。不,这份天命是跟定她了,她依然背负着它,就算是个负荷,她还是很高兴没失去它。尽管对它依然所知甚少,但黑婆试图打开她的心门时,她得知了一件事。她因此加快脚步,想找到一个可以进城的地铁站,因为她已经知道不管她这天命是什么,奥伯龙都在其中。当然,要不是有奥伯龙,她才不会想要这份天命。
黑婆缓缓从椅子上爬起来,依然惊愕不已。刚才那个是她吗?不可能是她的,不可能是血肉之躯的她,除非黑婆全部都算错了。但她拿来的水果还躺在桌上,还有那些吃了一半的糕点。
但倘若刚才来的人真的是她,那么这些年来协助黑婆祷告施法的又是谁?倘若她还在这里,还跟黑婆住在同一个城市、根本没有改变,那么她又怎能在黑婆的召唤之下帮人治病、指点迷津、撮合恋人?
她来到书桌前,把盖在中央那张图上的黑色丝布拿掉。她差点以为它已经不见了,但它还在:一张满是折痕的老照片,图中是一间跟黑婆的住处很像的公寓,有人办了一场生日派对,有个皮肤黝黑、骨瘦如柴、绑着两根辫子的小女孩坐在她的蛋糕后面(屁股下无疑垫着一本厚厚的电话簿),头上顶着一个纸皇冠,大大的眼睛令人震慑,且异常地充满了智慧。
黑婆不禁猜想自己是不是太老了,老得没办法分辨灵魂与肉身、访客与幽魂?若真如此,这又预示着什么?
她点燃一根新蜡烛,把它立在照片前方的红色玻璃上。
第七圣
多年前,乔治·毛斯带着奥伯龙的父亲熟悉大城,让他成为一个大城男子。如今西尔维也为奥伯龙做了同样的事。但大城已经变了。时值混乱的年代,人类陷入了重重困境,连最完善的计划都施展不开,任何方案似乎都注定遭遇无法解释又无可避免的失败。这些现象在大城最为显著,在大城里造成的痛苦与愤怒也最为严重——这种持久的愤怒史墨基没见识到,但奥伯龙倒是在每一个大城人脸上都看见了。
因为大城甚至比国家本身更加仰赖“改变”:迅速、无情、不断向上的改变。改变就是大城的血脉,是所有梦想的动力,是吵桥棍棒与枪支俱乐部会员血管里窜流的力量,也是让金钱、各种活动和满意度沸腾起来的熊熊烈焰。但奥伯龙抵达时,大城已经衰弱。迅速更替的时尚风潮已变得迟滞缓慢,一波波企业巨浪也成了一潭死水。吵桥棍棒与枪支俱乐部竭力抵抗但却无法逆转的永久萧条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座最大城市陷入了不寻常的停滞困境,接着这份疲弱感又缓缓向外扩散,麻痹了整个共和国。除了一些惯常但毫无意义的小变化之外,大城已经停止改变:史墨基知道的大城已经完全变了样,已经变得不再改变。
西尔维翻出一堆老照片来让奥伯龙认识大城,但她的版本却跟乔治为史墨基建构出来的大城风貌有很大的不同。不管个性多么古怪,乔治·毛斯终究是个地主,也是那些推动改变的伟大家族里的一个老成员(从他祖父那边算的话,甚至算是创始成员),因此他能感受到自己深爱的大苹果正逐渐萎缩干瘪,人们时而怨恨时而不满。但西尔维的出身却大不相同,在史墨基的时代,她的生长环境就像一个华丽梦境的幽暗底层,结果现在反而成了大城里最不萧条的一个区块(尽管依然充斥着暴力与绝望)。大城里最欢乐的街道就是那些穷人的街道,正当大家都陷入萧条与无可救药的困境之际,他们的生活却没什么太大改变,只是历史更悠久、传统更稳固而已:日复一日勉强糊口,还有音乐相随。
她带他造访亲戚们整洁拥挤的公寓。他坐在罩着塑料布的古怪家具上,享用没加冰块的汽水(他们认为喝冰的不好)和难以下咽的甜点,听大家用西班牙语赞美他:他们认为他是西尔维的好丈夫人选。而尽管她反对使用敬语,他们出于礼貌还是不断使用。他被他们那一大堆听起来都很雷同的小名搞得晕头转向。基于某些西尔维自己清楚但奥伯龙始终记不住的理由,某些家族成员叫西尔维“塔提”,包括那个帮她算出天命的黑婆阿姨(不真的是阿姨的阿姨)。后来“塔提”又被某个孩子叫成了“蒂塔”,这么一叫又叫惯了,接着又变成“泰坦尼娅”(一个很长的小名)。奥伯龙常常不知道自己听到的奇闻轶事主角就是他的爱人,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他们觉得你很棒。”离开亲戚家走在街上时西尔维这么说,手插在他外套口袋里让他握着取暖。
“呃,他们人也很好……”
“但宝贝,你把脚跷在那张——那张咖啡桌之类的东西上面时,我尴尬死了。”
“哦?”
“那是很糟糕的行为。大家都注意到了。”
“呃,那你天杀的干吗一声不吭?”他尴尬地说,“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家,大家都随意在家具上东靠西躺,而且还是……”他阻止自己说出“而且还是真正的家具”,但她还是听出来了。
“我试着告诉过你啊。我一直看着你。我总不能跟你说‘喂!把脚放下来’吧?他们会认为我对待你的方式就像胡安娜阿姨对待安立奎一样。”安立奎是个成天被老婆念念叨叨的男子,也是个笑柄。“你一定不知道他们为了那些难看的东西花了多少力气,”她说,“那种家具是很贵的,信不信由你。”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在冷酷的寒风里缩着身子前进。“家具”,他心想,“可搬动的东西”,从他们这家人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既奇怪又正经。她说:“他们全是疯子。尽管有些是疯上加疯,但基本上全是疯子。”
他知道这点。尽管对她复杂的家族有深厚的感情,她却不顾一切想脱离他们那场几乎像是来自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漫长悲喜剧,充满了疯狂、欺骗、堕落的爱,甚至是谋杀,甚至是幽灵。她夜里常翻来覆去、发出痛苦的叫声,幻想那票容易出事的人可能即将遭遇(或者根本已经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尽管奥伯龙认为那些只是夜惊现象而已(因为据他所知,他自己家里从来没发生过任何一件称得上可怕的事),但她这些“幻觉”却经常跟事实相去不远。她讨厌他们遭遇危险,讨厌自己跟他们绑在一块儿,但在他们那片无望的混沌里,她的天命却如同一盏明灯,虽然每次都开始闪烁,或者快要熄灭,却始终亮着。
“我需要一杯咖啡,”他说,“得来点热的。”
“我需要一杯酒,”她说,“得来点烈的。”
跟所有情侣一样,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常去的地方排列出来:一家小小的乌克兰餐厅,窗上总是结着一层水汽,茶很浓、面包很黑;折叠式卧房(这是当然的);一家巨大幽暗的戏院,装潢是埃及风,电影票很便宜、剧目经常更换、播映时间到早上为止;夜猫市场;第七圣烧烤酒吧。
除了饮料便宜、离老秩序农场很近之外(只隔一个地铁站),第七圣酒吧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一扇宽阔的前窗,几乎从地板到天花板,可以看见窗外街道上的人生百态,就像一个展示箱或一面大银幕。第七圣酒吧当年一定颇为气派,因为这片玻璃墙被染成一种饱满昂贵的咖啡色,给外头的风景添了一分不真实的味道,也像墨镜一样让内部更幽暗。这就像置身柏拉图的洞穴,奥伯龙告诉西尔维。她听他阐述这件事,或者应该说看着他讲话,只对他这人的古怪感兴趣,却没怎么仔细听他说话的内容。她很喜欢学习,但她的思绪还是飘到了别处。
“汤匙呢?”他说着举起一根汤匙。
“女的。”她说。
“那刀叉就是男的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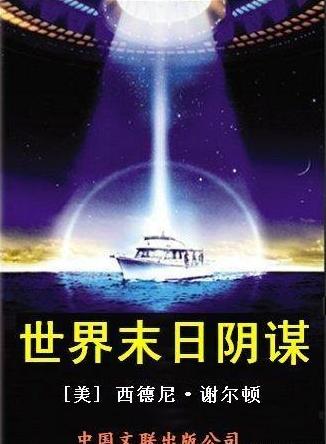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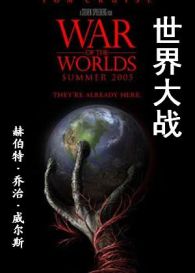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