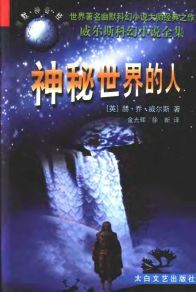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农庄。他们可以在那里栽植作物、饲养牛群。不,养山羊更好。山羊体型较小,也较不挑食。可以挤羊奶,偶尔还可以宰只小羊来吃。乔治没杀过任何比蟑螂大的东西,但他曾在一家波多黎各餐厅吃过小羊肉,现在一想起来就口水直流。虽然他知道史墨基在说话,但他却没听见史墨基说什么。他说:“但状况到底是怎样?到底怎么回事?”
“噢,我们受到了‘保护’,你知道的。”史墨基含糊说道,一边用他的拐杖抠着黑色的泥土,“但要受到保护,总得付出代价,不是吗?”他一开始什么也不懂,他现在还是不认为自己比较懂了。虽然他知道得付出代价,但他并不确定这份代价究竟是已经付出,将要付出,还是暂时延后;不清楚他冬天这种隐约的感觉,觉得自己被夺走了某种东西、被催促、被吸干、做了很多牺牲(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是否代表债主已经满意了,还是说那些透过窗户偷窥、在烟囱里大叫、群聚在屋檐下、在荒废的上层房间爬来爬去的妖孽其实一直在提醒他们大家还有一桩债务未了、一份贡品未收,而且根据妖孽的原则,甚至还要赚取一笔史墨基连算都不敢算的可怕利息。
但乔治却在思考如何透过“烟火秀”来呈现出“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在一本流行杂志里读到了这个理论,觉得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一开始可以先根据理论的诠释方式表达出一场行动的不同元素,呼啸声升高、在最高点光芒四射、一枚彩色炸弹爆炸;然后再透过烟火的组合来呈现“后续”行为,各式各样的多重行为,符合生命与时光之律动的壮阔行为。概念在一片火花中消失。他摇摇史墨基的肩膀,说:“但到底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
“老天,乔治。”史墨基说着站起来,“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了。我冻僵了。我猜今晚就会结冰,圣诞节说不定会有雪。”其实他知道一定会有,这是说好的事。“咱回去喝点热可可吧。”
可可与面包
可可是热腾腾的咖啡色,周围还浮着巧克力泡泡。克劳德姑婆丢进去的那颗棉花糖在里头翻滚冒泡,仿佛正快乐地溶解。黛莉·艾丽斯指导泰西和莉莉如何把它轻轻吹凉、从握柄端起来喝,然后看着沾在唇上的咖啡色痕迹哈哈大笑。在克劳德姑婆小心翼翼的照料下,它没在表面上长出一层皮,但乔治并不介意有皮,反正他母亲的热可可向来都有层皮。万街教堂招待的热可可也一样,从前他母亲似乎总会在这样的日子带他和弗朗兹到那座不分宗派的教堂去。
“再来个面包吧。”克劳德姑婆对艾丽斯说。“一人吃两人补。”她告诉乔治。
“你不是认真的吧。”乔治说。
“我认为是真的,”艾丽斯说,咬了一口面包,“我很能生。”
“哇。这回是男孩。”
“不,”她信心满满地说,“又是个女孩。克劳德姑婆说的。”
“不是我说的,”克劳德姑婆说,“是纸牌。”
“我们会把她取名为露西,”泰西说,“露西·安和安迪安德班班巴纳柏。乔治有两道胡子!”
“谁要把这端上去给索菲?”克劳德姑婆问,她把一杯热可可和一个面包放在一只十分古老的黑色亮漆托盘上,盘上面绘有一个发丝银亮、满身星星的精灵,正在喝可乐。
“我来吧,”乔治说,“嘿,克劳德姑婆,可以帮我算算吗?”
“当然啊,乔治。你应该是我们的一员。”
“希望我找得到她的房间。”他咯咯笑着说。他小心翼翼端起托盘,察觉自己的手已经开始发抖。
他用膝盖推开索菲的房门,当时索菲正熟睡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里,感受到阵阵蒸汽从那杯热可可里冒上来,希望她永远不要醒来。重温这种青春期的偷窥心情(膝盖发软、喉咙干渴)感觉很奇怪,但现在这感觉却是那颗疯狂胶囊和半裸着躺在凌乱床上的索菲引起的。她露出一条修长的腿,脚尖指向地板,地上躺着一件她脱下来的和服式睡袍,一双中国绣花拖鞋在睡袍底下若隐若现。她柔软的乳房已经从皱皱的睡衣里露了出来,跟着她的呼吸缓缓起伏,还因为发烧而微微发红(他温柔地想)。但就在他贪婪凝视的同时,她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因此她在睡梦中拉好衣服、翻过身去,把脸颊贴在一只握拳的手上。她这动作漂亮得令他又想笑又想哭,但他克制自己,既没笑也没哭,只是把托盘放在她挤满了药瓶和一团团面纸的桌上。为了挪出空间,他把一本大大的相簿或剪贴簿移到了床上,于是索菲醒了。
“乔治。”她平静地说,伸伸懒腰,没有任何惊奇之色,可能是以为自己还在睡觉。他把黝黑的手轻轻放在她额头上。“嗨,小可爱。”他说。她躺在枕头间,闭着眼睛,有那么一刻又陷入了梦乡。接着她说了声“噢”,然后挣扎着在床上跪坐起来,整个人清醒了。“乔治!”
“好点了吗?”
“我不知道。我刚才在做梦。热可可是给我的吗?”
“给你的。你梦到了什么?”
“嗯。不错。睡觉会让我肚子饿。你也一样吗?”她从面纸盒里抽出一张粉红色的面纸,擦掉沾在唇上的可可。刚抽出一张,下一张立刻就冒了出来。“噢,梦到好多年前的事。我猜是因为那本相簿。不,你不能看。”她把他的手从相簿上推开,“一些淫照。”
“淫照?”
“我的照片,很多年前的。”她露出微笑,用那种德林克沃特家特有的方式低下头,从可可杯上方偷瞄他,依然睡眼惺忪,“你来这儿做什么?”
“来看你。”乔治说。一见到她,他就明白自己所言属实。但她对这份殷勤毫无反应。她似乎忘了他的存在,再不然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件毫不相关的事,热可可才要举到唇边就忽然打住。她缓缓放下杯子,两眼出神,仿佛专注于某种他无法看见的内在的东西。接着她似乎挣脱了思绪,有点害怕地轻笑一声,突然抓住乔治的手腕,仿佛想稳住自己。“只是一些梦,”她说,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发烧的缘故。”
精灵孤儿
她人生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梦里度过。她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遁入另外那个世界,感觉自己的四肢变得温暖沉重、眼皮后方闪闪烁烁的黑暗变得规律,接着通道就开启了,意识长出猫头鹰的羽翼和趾爪,变得不再只是意识。
她从那份单纯的快乐开始,逐渐熟悉了所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技艺。首先必须学会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当我们在梦境里被虚幻的自我取代时,那一小块残存的自我意识就如同守护天使般陪伴我们,低语着“你在做梦”。秘诀是必须听到它但不予理会,否则你就会醒来。她学会听见这个声音,而它告诉她不管多可怕,梦里的伤痕都伤不到她,她总是毫发无伤地安然醒来,安全无比,因为她就躺在温暖的床上。从那时起她就不再害怕任何噩梦,她在睡梦中化身为但丁,跟做梦的维吉尔一起经历了种种令人欣喜又有启发性的恐怖事件。
接着她发现自己可以醒来,跳过清醒状态,再回到同一个梦中。她也可以建构层层梦境,先是梦见自己醒来,然后再梦见自己从那场梦里醒来,每次都梦到自己说:噢!只是一个梦!直到最后终于带着美妙无比的感觉真正清醒,从她的旅程归来,楼下则传来早餐的香味。
但不久她就开始在旅途上逗留,愈走愈远,愈来愈晚也愈来愈不愿意归来。她原本担心自己若是大半个白天和一整个晚上都待在梦境里,那么她总有一天会耗尽所有能够转化成梦的材料,担心她的梦会变得单薄、没有说服力、重复性太高。但事实恰恰相反。她旅行得愈深入(离清醒的世界愈远),虚构的景致就变得愈发华丽而创意十足,种种历险也更加完整壮阔。怎么会这样?她编织梦境的材料倘若不是得自清醒的人生,得自书本、图片、情爱、渴望、真正的道路、真正的岩石和踩在上面的真正的脚趾,那么会是得自哪里?那些传说中的岛屿、阴郁偌大的库房、复杂的城市、残酷的政府、无解的难题以及令人信服的滑稽配角又是从哪儿来的?她不知道,后来她渐渐就不在乎了。
她知道实际生活里挚爱的亲人都很担心她。他们的关心会跟随她入梦,但一进入梦境就会转变成复杂的困扰和凯旋后的团圆,因此她便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付他们和他们的关心。
现在她甚至学会了最后一项技艺,既能让她的秘密生活变得更有力量,也能压抑真实生活里的疑问。她学会让自己任意发烧,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烧时才会有的那种可怕、强烈、白热的梦境。她一开始还为这场成功兴奋不已,并没看出这样的双重剂量有多危险。她太仓促就抛弃了清醒时的大部分生活(反正它最近已变得既复杂又无望),带着罪恶的狂喜偷偷躲回她的病床上。
只有在某些梦醒时分(例如此刻在乔治·毛斯面前陷入沉思的时候),她才会突然了解这是种多么可怕的瘾:了解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已经迷失在这片领域,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走得太深、无法脱逃。唯一的退路就是继续深入,弃械投降、继续朝内飞去;要缓解这场可怕的瘾,唯一的方法就是继续沉迷。
她紧紧抓住乔治的手腕,仿佛他活生生的血肉可以让她真正清醒。“只是一些梦,”她说,“发烧的缘故。”
“当然,”乔治说,“发烧的梦。”
“我全身酸痛,”她说着抱住自己,“睡太多了。同一个姿势躺了太久还是什么的。”
“你需要按摩一下。”他的声音是否透露了什么?
她左右扭动修长的躯干。“你愿意吗?”
“这还用说?”
她背过身去,在印有图案的睡衣上指出酸痛的地方。“不不不,亲爱的,”他仿佛在对一个孩子说话,“像这样,在这里趴下。用枕头垫着下巴,这样对。我坐在这里,你挪过去一点,我先脱鞋子。舒服吗?”他开始帮她按摩,透过薄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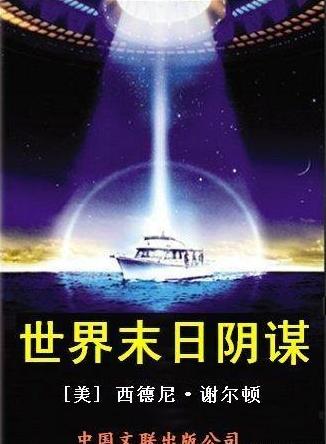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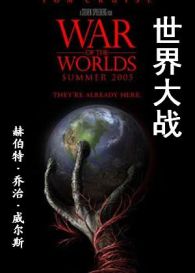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