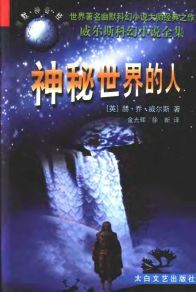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10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们好。”她对大家轻轻点了一下头。接着她在一把椅背垂直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是一位好老好老、老得惊人但眼神明亮的女士,另一边则是一对双胞胎,一男一女,同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您是什么样的表亲呢?”玛吉·朱尼珀问她。
“据我所知,”霍克斯奎尔说,“ 我其实不算表亲。瓦奥莱特·德林克沃特的儿子奥伯龙的生父后来结了婚,那人正是我祖父。”
“哦,”玛吉说,“是那边的家族呀。”
霍克斯奎尔感觉有人盯着她看,于是迅速瞟了扶手椅上的两个孩子一眼、对他们露出微笑。他们带着不甚笃定的好奇心盯着她瞧。霍克斯奎尔猜想他们应该很少见到陌生人,但其实巴德和布洛瑟姆带着惊奇和些许恐惧看见的,却是他们常唱的一首歌里在紧要关头现身的那位有点恐怖的谜样人物:带着鳄鱼皮包的女士。
尚未失窃
艾丽斯迅速爬上楼,像盲人一样熟练地穿过黑黢黢的楼梯。
“史墨基?”来到通往观星仪的那道陡峭狭窄的楼梯底下时,她向上呼喊。没有人回答,但上面有光。
“史墨基?”
她不喜欢爬上去。那狭窄的楼梯、那小小的拱门以及那塞满机械、寒冷又拥挤的圆顶阁楼,总令她毛骨悚然。这东西铁定不是为了取悦一个体型像她这么庞大的人而设计的。
“大家都到了,”她说,“可以开始了。”
她双手抱胸等了一会儿。在这无人使用的楼层,湿气几乎摸得到,壁纸上到处都是褐色的污渍。史墨基说:“好啦。”但她却没听到脚步声。
“乔治和奥伯龙没来,”她说,“他们走了。”她又等了一会儿,接着(由于既没听到工作的声音也没听到准备下楼的声音)她就爬上了楼梯,把头从小小的门伸进去。
史墨基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瞪着那黑色钢壳里的机械装置,就像一个坐在神像面前的请愿者或忏悔者。看见他、看见那裸露的机器,艾丽斯竟觉得有点害羞,仿佛自己刺探了某人的隐私。
“好啦。”史墨基又说了一次,但他站起来却是为了从盒子底部那排如槌球般大的钢球中拿一颗出来。他把它放在盒内一个旋转轮其中一根曲臂上的凹槽里。他松开手,球的重量就压得曲臂往下转。转动的同时,其他有关节的手臂也跟着转动,其中一根咔啦咔啦地伸出来,准备接收下一颗球。
“看懂它的运作方式了吗?”史墨基悲伤地说。
“不懂。”艾丽斯说。
“这是不平衡旋转轮。”史墨基说,“你看,因为有关节的缘故,这一侧的手臂都是伸直的。但一绕到这一侧,关节就会折叠起来,让手臂紧贴着转轮。所以手臂打直的那一侧永远比较重,会一直往下掉,也就是向下转的意思,所以你若把球放在凹槽里,转轮就会转过去,让下一根手臂伸出来。接着下一颗球就会掉进下一根手臂的凹槽里,再把它往下压,以此类推。”
“哦。”他的描述方式非常平板,像叙述一个重复了太多次的古老故事或一门文法课。艾丽斯突然想起他还没吃晚餐。
“接着呢,”他继续道,“从这一侧落入凹槽的铁球重量会让这些手臂在另一侧升高、折叠起来,这时凹槽就会翻转,让球滚出去,”他用手转动轮子示范,“滚回架子上,再滚下来、掉进这一侧刚刚伸出来的手臂凹槽里,带动手臂转过去,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根弯曲的手臂确实释放了铁球,铁球确实又滚到了下一根从转轮上咔啦咔啦伸出来的手臂上。那根手臂被铁球的重量压到了转轮底部,但接着它就静止不动了。
“真了不起。”艾丽斯平静地说。
史墨基背着双手阴郁地看着那一动不动的转轮。“这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蠢的东西。”他说。
“哦。”
“这位克劳德先生铁定是有史以来最蠢的发明家或天才……”但他想不出该如何作结,因此他低下头,“ 它从来没成功过,艾丽斯。这东西什么也转不动。没有用的。”
她小心翼翼地穿过那些工具和拆卸下来的油腻零件,拉住他的手臂。“史墨基,”她说,“大家都在楼下。爱丽尔·霍克斯奎尔到了。”
他看着她,接着笑出声来,是一阵受挫的笑声,因为他很荒谬地被彻底打败了。接着他龇牙咧嘴了一下,迅速按住自己的胸口。
“噢,”艾丽斯说,“你应该要吃晚餐的。”
“我不吃反而好,”史墨基说,“好像是这样。”
“走吧,”艾丽斯说,“ 我打赌你会搞懂这东西的。也许你可以问问爱丽尔。”她在他额头上轻吻了一下,然后赶在他前面走出拱门、走下楼梯,有种被释放的感觉。
“艾丽斯,”史墨基对她说,“ 就是现在了吗?我的意思是今晚。这就是了吗?”
“就是什么?”
“就是了,没错吧?”他说。
他们穿过走廊、下了楼梯朝二楼走去时,她什么也没说。她抓着史墨基的手臂,觉得有不止一种回答方式,但最后(已经没必要再拐弯抹角了,毕竟她已经知道太多,而他也一样)她只说:“应该是吧,很接近了。”
史墨基按在胸口的手开始发麻,因此他叫了声“哎哟”,然后停下脚步。
他们站在楼梯顶端。他可以隐约看见下方客厅的灯光,听到人说话的声音。接着声音就化成一阵嗡嗡声,终至消失。
很接近了。如果已经很接近了,那他就输了,因为他已经落后太多。他连该怎么做都还没想出来,更遑论开工。他输了。
仿佛有个巨大的空洞在他胸口裂开,一个比他本身还要大的空洞。痛苦的感觉在外围聚集,而史墨基知道只要过了这漫长的一刻,那份痛楚就会涌进来填满这个空洞:但在那一刻过去之前,就只有一份可怕的预感和一份初生的启示而已,两者都很空洞,在他空洞的内心交战。预感是黑色的,而那份呼之欲出的启示则是白色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试着不要因为无法呼吸而恐慌,因为那个洞里没有空气,他只能体验预感与启示之间的战争、倾听耳朵里那阵悠长刺耳的嗡嗡声。那声音似乎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吧,虽然你没要求弄明白,况且你一定没料到会在这一刻、在这黑暗的楼梯上豁然开朗,但现在:接着那声音就消失了。他的心脏先是如遭重击般痛苦地跳了两下,接着就开始猛烈地稳稳跳动,仿佛愤怒无比。接着他就被熟悉而令人释然的痛楚给填满。再过一秒钟,他就能呼吸了。
“噢,”他听见艾丽斯的声音,“噢噢,这次很严重哪。”他看见她同情地抓着自己的胸口,感觉到她紧紧拉着他的左手臂。
“是啊,哇。”他终于能说话了,“噢,老天爷。”
“过去了?”
“差不多了。”被她拉着的那条左手臂一阵抽痛,一路痛到了无名指。他没戴戒指,却感觉仿佛有枚戒指被硬生生拔了下来。一枚戴了很久很久的戒指,除非把神经与肌腱整个截断,否则根本不可能脱掉。“别这样、别这样。”他说,结果那感觉就真的消失了,至少是慢慢减弱了。
“好了,”他说,“好了。”
“噢,史墨基,”艾丽斯说,“你还好吧?”
“过了。”他说。他开始下楼梯,朝客厅的灯光走去。艾丽斯抱着他、支撑着他,但他并不虚弱。他甚至没生病,菲什医生和德林克沃特医生的旧医学书籍一致同意:困扰他的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并不影响长寿,甚至不影响其他方面的健康。
一种症状,必须与之共存。那么为何它感觉像是一种启示,一种欲语还休、之后就想不起来的启示?“没错,”老菲什曾说过,“一种死亡的预感,那是心绞痛的人常有的感觉,没什么好担心的。”但那是死亡的预感吗?当他终于得到那份启示时(假如有这么一天),内容会是死亡吗?
“很痛吧?”艾丽斯问道。
“这个嘛,”史墨基笑了,但也像是在喘气,“ 假如有得选择,我应该是宁愿它不要发生,没错。”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艾丽斯说。她似乎把他的发作模式看成跟打喷嚏一样:打了最后一个大喷嚏之后就不会再打了。
“哦,我打赌不是,”史墨基温和地说,“ 我想我们应该不希望有所谓的最后一次。不要。”
他们相拥着走下楼梯,进入大伙儿等待的客厅。
“来了,”艾丽斯说,“史墨基来了。”
“嗨、嗨。”他说。索菲在桌边抬起头,他的女儿们也停下手中打的毛线抬起头。他发现他的痛苦就反映在她们脸上。他的手指依然刺痛着,但还完好无缺。他那枚戴了很久的戒指还没被偷走。
一种病症:但却像是种启示。他第一次感到好奇:他们的症状也跟他的一样这么痛苦吗?
“好吧,”索菲说,“我们开始吧。”她环顾周围那一张张看着她的脸,有德林克沃特、巴纳柏、伯德、弗劳尔、石东、威德家的人,有她的表亲、邻居和远亲。桌上黄铜台灯的亮光让房里其余的空间显得幽暗朦胧,仿佛她是坐在一处营火旁看着周遭黑暗中的动物,而她必须用言语唤醒它们的意识与目的。
“好吧,”她说,“我有了个访客。”
Ⅲ
但你们怎能期望靠心思神游那条小径;
怎能期望借鱼儿测量月亮?
不,我的邻居们,千万别以为那条路很短;
想踏上那旅程必得具备狮子之心,因为路途遥远、海洋深沉;
你会怀抱着惊奇走上很久,时而微笑、时而哭泣。
——阿塔尔,《鸟儿议会》
要在这个夜晚把亲戚和邻人集结在一起,比索菲原本想象的还要容易;但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而决定该跟他们说什么更非易事:这么做等于是打破了一段年代久远的沉默,久远得连艾基伍德的人都忘了最初是发誓要三缄其口的。很多故事都是以这份缄默为中心,而如今它已经打破,就像敲破一个上了锁且遗失了钥匙的箱子。冬天的最后几个月他们都在忙这件事,此外就是把消息传往泥泞的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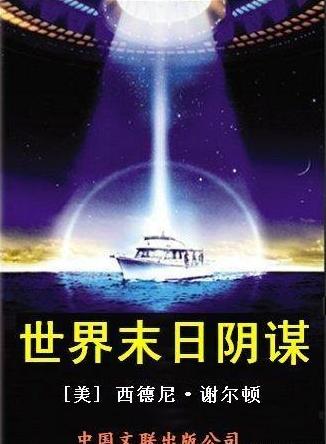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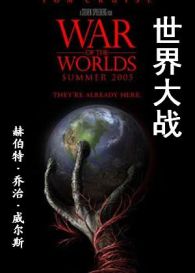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