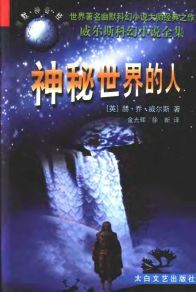他方世界-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美'约翰·克劳利
【由文,】
正文
第一部 艾基伍德
Ⅰ
男人是男人,但人类却是女性。
——切斯特顿
二十世纪的某个六月天,有个年轻男子从大城出发,一路向北,徒步前往一个他只闻其名却不曾去过的地方。此地名叫艾基伍德,有可能是座城镇,也可能只是个地名。男子名叫史墨基·巴纳柏,正要到艾基伍德成婚;他之所以走路而不搭车,是因为他要到那里去就得遵守这项条件。
从某处到他方
尽管他一大早就从城里的住处出发,却到近中午才行经一条人迹罕至的步道,越过大桥,来到河流北岸那些有名称却无明显分界的城镇。他花了一整个下午穿越这些取着印第安名的地方,通常无法跟着那些川流不息、横行霸道的车辆直线前进;他从一区来到另一区,往巷弄间和商店里张望。虽然有骑脚踏车的孩子,但行人却寥寥无几,就算是当地人也一样;他不禁猜想这些地方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他看来似乎极度边缘化),尽管孩子是够愉快了。
正规的商业大道和住宅街区逐渐变得凌乱,就像大森林的外围树木会愈来愈稀疏一样;杂草丛生的荒地,开始像林间空地般穿插其间;不时出现一片片满是尘埃、发育不良的树林和脏乱的草场,立着的告示上载明该地可改建为工业园区。史墨基心里反复玩味最后几个字,因为他似乎确实置身这样的地方:一座工业园区,就在沙漠和农地之间。
他在一张长凳前停下脚步,众人可以在这里搭上从“某处”到“他方”的公交车。他坐下来,放下背上的小包,拿出自己做的三明治(这又是另一项条件)和加油站送的彩色路线图。他不确定条件里是否有禁止使用地图这一项,但前往艾基伍德的指示并不清楚,因此他还是摊开了地图。
好了。这条蓝线似乎就是他刚才走过的坑坑洼洼的沥青碎石路,两侧都是无人的砖厂。他把地图转过来,让这条线和面前的路一样跟长凳平行(他向来不大会看地图),结果在左手边遥远的那一头发现了目的地。艾基伍德这名字并没真的印在上面,但它确实就在这儿的某处,落在图例中最不显眼的记号所标示出来的五座城镇之间。所以喽。有一条大大的双红线通往那一带,还傲然附上交流道出入口,但他不可能走那条路。更近处则有一条粗蓝线(史墨基总觉得所有南下进城的车流都走蓝线,出城的才走红线,就像血管系统一样),还有一条条微血管似的支线通往沿途的小城镇。他目前所在的这条细得多的笔直蓝线就是支线之一;八成会有商业活动朝这儿转移,工具城、美食城、家具世界、地毯村。好吧……但不远处也有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黑色细线,他可以改道从那里走。他原本以为此路不通,但是不对,它一直断断续续延伸下去,乍看之下仿佛是制图师将之遗忘在纠结的路线之间,但到了北方的空旷地带又见清晰,直驱史墨基知道的一个城镇,那里很靠近艾基伍德。
就走这条吧,它看起来像是人行步道。
他在地图上以手指测量自己走了多远,再量量还要走多远的路(比刚才的路程远得多),接着背起背包、把帽子斜戴以遮挡太阳,再次踏上旅程。
长 饮
他走在路上时没怎么去想她,尽管两年前爱上她以来,她就一直在他心里。他心头经常浮现他俩初遇的那个房间,有时一想起来就跟当时一样满心惶恐,但通常是既庆幸又幸福的。他还常想起乔治·毛斯手拿酒杯、嘴叼烟斗,将他那两个高挑的表妹介绍给他:有她本人,还有她背后那个害羞的妹妹。
毛斯家族位于市内的宅邸是整栋大楼里最后一户有人住的房子,一切就发生在三楼的书房内。直棂窗上贴着硬纸板,门口、吧台和窗户之间的走道上铺的深色地毯已经让人踩到褪色。就是那个房间。
她很高。
她身高将近六英尺,比史墨基还高了几英寸,她刚满十四岁的妹妹也已经跟他一样高。她们的小礼服很短,闪闪发光。她穿红色,妹妹穿白色,裹在长腿外的长丝袜熠熠生辉。奇怪的是她们尽管如此高挑,却害羞得很,尤其是妹妹,她面露微笑却不愿跟史墨基握手,只见她转身躲到姊姊背后。
真是纤细的女巨人。乔治温文尔雅地展开介绍时,姊姊朝他瞥了过去。她笑容青涩,一头玫瑰金波浪头发,卷度恰到好处。乔治说她名叫黛莉·艾丽斯。
他握住她的手,抬起头。“好长的一饮'1'。”他说,结果她笑了出来。她妹妹也笑了,乔治·毛斯则弯身往他膝上拍了一下。史墨基不懂哪里好笑,只好露出纯洁又愚蠢的微笑看着大家,始终没松开手。
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刻。
无 名
在那间书房里认识黛莉·艾丽斯·德林克沃特之前,他的人生并不特别快乐,但却刚好适合展开这场追求。他父亲跟继室只有他一个孩子,他出生时父亲已年近六十。当他母亲发现巴纳柏家的万贯家财早已被他父亲败得所剩无几,后悔当初根本不该嫁进来、更不该生下小孩后,就恨恨地离开了。这对史墨基而言是桩惨事,因为所有的亲人当中,最有特色的人就是母亲了。尽管她离去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但他年老时,所有的血亲当中,他能轻而易举忆起的只有她的脸。史墨基自己遗传了一大半巴纳柏家族的虚无气息,只有一小部分承袭母亲的具体感:在认识他的人眼里,那是一种实在的气质、一种存在感,笼罩在某种隐隐约约的不存在感当中。
巴纳柏家是大家庭。他父亲跟元配共生了五个儿女,他们全都住在那几个 I 开头的州里一些不知名的城市郊区。史墨基在大城里的朋友向来分不清这些城市,而史墨基自己有时也会搞混。由于子女们公认父亲有很多财产,而且从来没有人清楚他打算如何处理,所以父亲可以随时到子女家去作客。自从太太离开后,他决定卖掉史墨基出生的那栋房子,带着这个幼子、前前后后几只没有名字的狗和装书的七个特制箱子,轮流寄住在其他孩子家。巴纳柏是有学识的人,但他专精的领域太冷僻死板,没能帮他创造多少话题,也完全无法改善他与生俱来的无特征感。他较大的儿女都把那几箱书视为麻烦,就像洗衣服时把他的袜子跟他们的衣物混在一块儿一样。
(后来史墨基习惯在上厕所时,试图厘清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姊到底分别住在哪一州的哪个城市里、房子各是什么样子。也许是因为往日在他们家上厕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最为平庸,平庸到近乎隐形;反正他会坐在那儿将哥哥姊姊和侄甥们在脑海中不断交互切换,试着把每个人的脸跟某座前廊或某块草坪搭配起来。因此到了晚年时,他总算把一切弄清楚了,并从中获得一种单调的乐趣,跟解字谜游戏一样,连心中那份疑虑也相同——万一他猜出来的字不是作者设计的答案怎么办?只是他永远不会在下周的报纸上找到解答。)
巴纳柏并没有因为妻子离去而变得郁郁寡欢,只是变得更加了无特征而已。对他较大的儿女而言,父亲先是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接着又从中消失,似乎愈来愈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他具体的内涵就是他的学识,而他也只把它传授给了史墨基而已。由于父子俩居无定所,史墨基从没上过正规学校,等到有一个 I 开头的州政府得知史墨基这些年来在父亲身边的遭遇时,他也早已过了强制入学的年纪。就这样,十六岁的史墨基懂的是古典时期与中世纪的拉丁文、希腊文、一点旧式数学,也会拉一点小提琴。除了父亲那些皮革装订的古典著作之外,他没看过多少书,但多少可以精准背出维吉尔的两百行诗句,还写得一手完美的斜体字。
他父亲就是那年去世的,似乎因为把所有的学问都传授给儿子而油尽灯枯。此后史墨基又漂泊了几年。他找工作很难,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学历;最后他在一家寒伧的商职学校(他事后回想认为应该是位于南弯)学会了打字,成了个职员。他在三座不同城市的郊区住了一段时间,每个郊区的名字都相同,而每个地方的亲戚都会以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比如他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史墨基等,由于最后这个名字太符合他的特质,一叫就沿用至今。二十一岁时,一家不知名的储蓄银行将父亲的一笔遗产补交给他,他因此搭上巴士来到了大城,并且立刻将亲戚居住的城市抛诸脑后,连人也一并遗忘。多年后,他还得将他们的面孔跟草坪一一搭配起来,才能重新唤起记忆。一抵达大城,他就满怀感激,完全投身其中,像一滴雨水落入大海。
名字与号码
他住的房子原本是牧师寓所,隶属于后面那栋备受尊敬但也饱受破坏的古老教堂。从他的窗口可以看见教堂的附属墓园,安息在那儿的尽是一些取着荷兰名字的男子。每天早上,突如其来的车声都会把他吵醒,接着他便去上班,始终未能像从前那样在中西部火车的轰隆声中照睡不误。
他在一个宽敞的白色房间里工作,各种细小的声音都会传上天花板,形成某种古怪的回音。倘若有人咳嗽,天花板本身仿佛也会满怀歉意,捂着嘴咳一声。史墨基每天就在那儿拿着放大镜检视一行又一行微小的印刷字,仔细检视每个名字和后面的电话地址,再跟每天送到他手上那一叠又一叠卡片上的姓名、电话、地址进行比对,若有不符合的地方就用红笔做记号。
那些名字一开始对他毫无意义,跟电话号码一样了无特征。一个名字只有在字母顺序排错的时候才会变得显眼(这是无可避免的意外),再来就是计算机犯下愚蠢错误的时候,而史墨基的职责就是找出这些错误。(在史墨基看来,计算机犯错的几率之小还比不上它那诡异的蠢行来得令人印象深刻;举个例子,计算机不会分辨“St。”这个缩写什么时候代表“街”、 什么时候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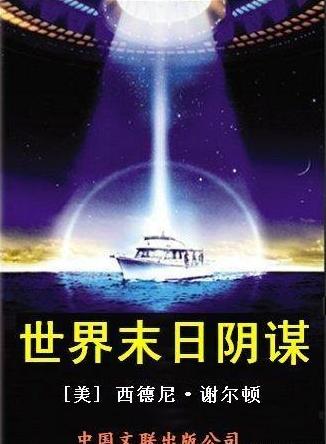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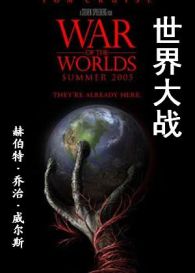

![[综漫]炸裂吧,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