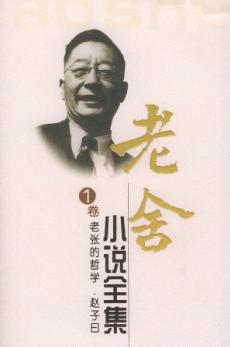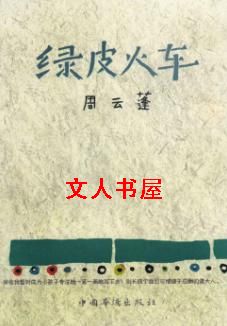绿皮火车-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圈好场地自由表演。我和小河还计划着去那儿唱“嗡嘛尼呗美吽”观音菩萨心咒,大家戏言:“那教堂的尖顶会放出一道神光,把你俩照得现出原形。”
戏剧节结束了,呼啦啦人都走光了,小城空寂无人。你会想,那么多教堂,几乎可以对口到每户一个。也许它就是想空在那儿,即使没人祈祷,没人演戏,也留在那儿一个巨大的空间,让鸟儿鸣叫时有回声,鸽子咕咕叫时有共鸣。
我们乘高铁离开这个比北京天通苑还小的城市,车站很小,没有我们大包小包安检、排队检票的大场面,刚刚紧走几步,就到了站台,火车已经静静地等在旁边。车门口也没有检票员。我们忐忑地猜想,如果恐怖分子来了,可怎么防范?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街上没有城管,警察很少,也没天下大乱。还是那么多教堂,在默默中发挥着不为人知的作用。高铁中人很少,车厢很安静。偶尔也会临时停车,也会让我们惊恐地想到了温州车难。也许这一辈子,每次临时停车,都会想到隧道、高架桥,以及工体几万名球迷举手向天自发的默哀,还有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坐在法国南部的小城的剧场台阶上,捧着笔记本上微博,搜索国内高铁的所有新闻,愤怒地发帖、声讨、追问,感觉中国无处不在。
途穷幕落阿维尼翁
法国南部小城阿维尼翁戏剧艺术节已经结束,在这个艺术节上,我刷新了自己连续演出天数的新纪录,每天一演,共二十二场。最后一场生意惨淡,只有一个法国老太太,看完演出非常高兴,要买唱片,但没有现金,要去提款或者开支票,搞得我们是又高兴又无奈。同行的别的剧团想发洋财,从国内批了桃花扇、绣花鞋、海魂衫,结果纷纷砸在自己手里。外国人买东西是很谨慎的,真正购买力强大的是中国人。由于我们总是去旁边的超市扫货,他们特别为中国人进了“走自己的路”牌方便面,就差卖速冻饺子、油条、煎饼了。
阿维尼翁这个小城除了教堂就是剧场,曲终人散后,一片空寂,满街的海报随风招摇,如落叶满秋山。
最后的日子,人们都开始想念起榨菜、辣酱,甚至地沟油。在国外生活再好,也是无根的生活。很多人集中在剧场的Wi…Fi信号区域里,大家都在关注国内的动车追尾事件,法国的浪漫、蓝天碧海挡不住中国的尖锐现实。我们在遇难者的“头七”夜晚,演出前搞了一个小小的默哀仪式。所有的中国人、法国人一起起立,气氛非常肃穆。那天恰巧也是我们演出观众最多的一天。
8月1日,我们坐上了法国高铁,从阿维尼翁开往巴黎。车厢门口没有检票员,火车是双层,每节车厢都有专用的行李架,坐到自己座位后发现,头上、身后都有隐藏空间可放行李。
车厢中特别安静,乍一上去,以为就我们三四个中国人。没有列车员走来走去推销东西,也没有伴着肯尼基抒情喇叭“一路平安”的广播。我们捏着花八十欧元买来的昂贵车票,心想是不是不查票。后来陆续上来了一些人,但整体上还是很安静,大家都在悄声低语,只有快到某站时,才有一个简短的法语预报。
车速很快,据朋友们目测,时速在二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车窗外,路过一排排向日葵田、薰衣草田,绿妖刚惊叫着举起相机,景色就一闪而过了。
到巴黎时是下午四点,我们被接到一个朋友住的保姆房。首先电梯就非常惊悚,先拉开一个铁门,再推开一个铁压缩门,推门时朋友不住叮嘱:“千万别夹住手。”我们像困兽被关在里面,“咣当”一下,电梯开始上行,等到快停时,又是“咣当”一下。等我们犹犹豫豫地把手伸向铁栅栏,想把它拉开时,电梯又“咣当”一声自己下去了。
保姆房是富人买房时附赠的阁楼,供佣人居住。出去的门都是自己专用的,窄小的楼道,老旧的电梯,据说很多伟大的诗人,如里尔克,当年混巴黎的时候就住这种房子。
有朋友在罗浮宫工作,说去罗浮宫参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像是看画,倒像是在集市上抢购降价大白菜。《蒙娜丽莎》的画前,每天都挤满了人,闪光灯肆无忌惮。我们想去更安静的美术馆,如奥赛,那里是印象派画家的主场。我还想去看一看拉雪兹公墓,也许会邂逅到我曾经非常喜欢的诗人,如兰波或马拉美,还有那个疯狂的“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全世界的嬉皮士、坏青年都云集在他墓前,抽烟喝酒。他在死亡中也醉得从来没有醒来过。
死之静美
巴黎拉雪兹公墓鼎鼎大名,那里有“大门”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还有王尔德,据说他的墓碑上印满了喜欢他的女子的吻痕。本来要去的,但后来阴差阳错,去了蒙巴纳斯公墓,因为这里有我最喜欢的诗人波德莱尔。十八岁时,我买过《恶之花》,主要是冲诗集的名字去的。后来在大学、在漂泊的路上,不断遭遇他的诗,他的诗属于那种一辈子都在滋养你的阴郁华美的好文字。
蒙巴纳斯公墓,人气最高的当然不是波德莱尔,而是萨特和波伏瓦。他们合葬的墓在正门附近,非常好找。前面有许多人合影留念。我心里纳闷:这一对儿一辈子都坚信“他人即地狱”的哲学家,死后怎么会合葬在一起?
继续向公墓的深处寻找波德莱尔。午后的天空飘着小雨,细小的花瓣把路面染成黄色,真是一个逛墓园的好天气。死亡在这里是一个微笑的建筑师或者是画家或者是园丁,坟墓更像是艺术品,有的是一间朴素的房子,开着门,好像主人出去办事,马上就回来。有的墓前是很抽象的现代派雕塑,一个铜像仰望幽冥,如等候,如思念,衣服上生满了青苔。还有一个墓前竖着一只花花绿绿、瓷做的大狸猫,墓碑上写着:这里睡着我们年轻的大朋友。我们为这里埋的是一个小孩还是一只大猫争论了很久。
波德莱尔的墓,低调地隐藏在墓群深处。墓碑上压着好多彩色的小纸条,有一张写着:你是一个伟大的粉红色的诗人。旁边还有一个空酒瓶子,好像有人在这里陪他默默地喝过酒。我们仔细地看了墓碑,他是和几位亲戚合葬,这个一生讴歌死亡、坟墓的诗人,生前那样桀骜,死后还挺随和。
我们按照目录,还想去拜访一下圣桑、贝克特,可墓碑如森林,1768年,1867年,1976年,时间凝固成迷宫,怎么也找不到。最后找到了杜拉斯,她的墓前全是鲜花。我是通过王小波认识杜拉斯的,看到她的小说里写到东北的抚顺,特别惊讶。我的家离那儿很近。那里是个最不浪漫的煤矿城市。一想到杜拉斯《情人》中的男主人公操着一口接近赵本山的抚顺话泡妞,就让我忍俊不禁。
法兰西是个优雅的民族,死亡也如此让人赏心悦目,《人权宣言》是活人的,也属于死者,虽然他们已永远沉默。
新疆西游记
新疆的太阳炽烈炽烈的,就像一个蒙古汉子坦荡荡地坐在云端喝烈酒。可一旦你躲进树荫或者门洞里,立刻是凉风飒飒,仿佛置身于深秋。
新疆是我一直向往但又从未去过的地方。2011年8月13日,我和歌手吴吞要在乌鲁木齐做一个民谣专场。临近演出的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买了昂贵的飞机票,飞往乌鲁木齐。
演出时间很低调地定在下午四点,现场的火热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买票的队伍从二楼沿着楼梯排到了街边。我觉得音乐应该是那种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恐惧的最好的钥匙。
吴吞本身就是新疆人,他们过去组建的“舌头”乐队曾经是中国最好的摇滚乐队,“舌头”乐队是新疆人心目中的摇滚英雄,这次衣锦还乡意义非凡。吴吞现场唱了很多关于这片土地的歌:“翻山越岭,骑马过河,肩上的猎鹰,不论飞到哪里,总听到母亲的呼唤……”台下的人们听到这些歌都由衷地感觉到亲切。
我唱了《中国孩子》,虽然不能亲身去克拉玛依唱这首歌,但这里已经离那个令人伤心的火灾现场很近了。但音乐就是让人心里平和、让人彼此相爱的艺术,演出自始至终都很温馨,有笑声,也有悄悄的眼泪。
第二天,我们搭朋友的车一直向西,目的地是中哈边境的温泉县,那里有“旅行者”乐队的吴俊德和张智等着与我们会合,晒太阳、喝酒、吃哈密瓜。一路向西六百公里,左面是天山,右面是大戈壁。开到半夜,才到达温泉县城。下车后空气新鲜得呛得我们差点晕过去。这个地方属于蒙古族自治州,脚一落地,直接就上了酒桌,大家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疯狂地一轮轮劝酒。
由于我们中间有吴俊德——汉族的冬不拉高手,两个哈萨克族朋友慕名而来,酒过三巡,老吴弹起了冬不拉,哈萨克族朋友心中的热情就被点燃了。然后大家一起唱了很多古老的哈萨克族民歌,一个汉族歌手能把这些歌曲唱得如此深情,让他们感到非常激动。旁边作陪的乡长,是我们中间级别最高的领导,他不无感慨地评价说:“什么是民族团结?这就是民族团结。”
第二天酒醒上街,见到了真正的边塞小城的风貌。干干净净的街道,四周环山,有的山顶还覆盖着积雪。街上的人很少,街道两边的房子色彩鲜艳,不时会有一些皮肤白皙、深目高鼻的哈萨克族美女一闪而过。我们在街边买热苞米,卖苞米的维吾尔族大姐怕我们一个塑料袋会漏掉,一再要求再给我们多套几个袋子,热情得让我们手足无措。
其实新疆是一个最适合人唱歌、跳舞、喝酒的乐园。只要你冬不拉弹得好,只要你喝酒喝得豪爽,只要你马骑得帅,总会有姑娘对你心生爱慕。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坐在一个蒙古包前,眼前是一片大草原,夕阳快下山了。我们刚吃了哈密瓜,喝了奶茶,躺在草地上,等着太阳下山月亮升起。这将又是一个彻夜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