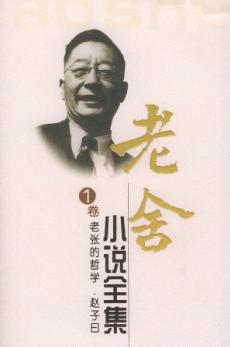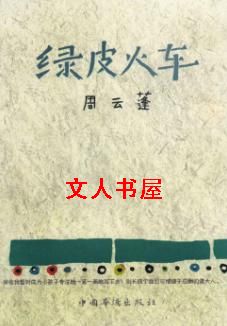��Ƥ��-��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䣬�·�һ�����������սʿ��������ս�ѡ�
С��ȥ���ˣ�����Ϊ�����м������ֻᡣ�����ڡ��ӡ��ư��ݳ����Լ����ݳ��Ķ�����һ�𣬴Ӱ˵�һֱ������ҹ���㡣��Ұ���ӡ��ֶ�Ҳ�����ɢ��
�������ںӱ�����˵/�����ɻ���/���DZ����������������/Զ�а�Զ��
�����Ł����д�ĸ裬�����С�Զ�С�����ֻ��ȥ�����ϣ������������������������DZ�Ȣ�����ӡ��ܶ��������οͶ��������ӵĴ�ʯ�ſ��������Ŷ����������ꡰҰ���ӡ��ĸ衣���������ø�����ʼ���أ����Һ������ƣ������������ҵļ�����Ϊ�����ҵĶ��������Ł��Լ�¼�Ƴ�Ƭ���Լ�װ֡ӡˢ���Լ����������������ȥ�����Ϸ�Ѳ�ݣ���һ�����ֻ��ɡ�����ܸ��ӽ�������ʱ�����롪�����߱߳���
��һ��Ա�������⣬��־Ҫ��һ�����˵��ַ����֡����ȼ�����С�ӵġ�����ҩ�ꡱ�ֶӣ�����������С���䡢��ľ�����࣬�����Ķ����ᷢ�⣬�ų���ҥ��ġ��������֡������Լ����������˺ܶ�裬�����ġ��꡷��������������и衣
�ѹ�Ӣ����Ʈ�������л�Ե�ؾۡ�2011�꣬�Ł硢�����⡢������������Ұ���ӡ�����Ĺ��ų�Ա�����ߵ�һ�𣬸��Դ����Լ���ô�������������������飬��ϳ��µġ��ƺ�ҥ������2011����������ֽ��ϣ���Ұ���ӡ��ֶ�������վ��̨�ϣ����������һ�ˣ�Ȼ�����ߺ����߶�����������ǵ����֣��������ᣬ�������������������������
�������ˣ�����ס�ڴ�����Ժ���ÿ�������������������ڣ�ʱ�㣬һ˿�������ŵ�̫����ɽ����������ˣ��Ł��º͵ؿ���һ�ۣ����������Ҽ��֣�����ط����ˡ�2012�����ǻ��ͬ�������������С�ӡ������ٴβμ���������ڡ�����Ĺ����������������֣��վ����¡�
ңԶ�Ļƺӻ�δ�ɿݣ�������˼�����ǰ��ʱ�ⲻ����ȣ�������Ϊ֤��
��ͷ����������
����Ҫ�������˸�ù�ϵ�������쾭��������������������кܶ��������˵ĺ����ѣ�ΰ��������������������ʵ�й��Ĵ���������˶����������������ܶ���������Ҳ����ʶ�������Ƕ����ֳգ�ÿ�������˶���һ���ӵĴ�ڳ�Ƭ�������������������������������������һ������ڴ��ġ����ڸ����������ݽ�ͷ����������ָָ��㣺������ţ��ǵ����������ˡ������ĵ��̡�����������֡��Ƿ��������ķ�ʽ���ѡ�����˿�ޡ�����ƽ�ˡ��������¡��͵���ǧ����
��������ס��ʱ��ij�죬�ʵ�Ա����������ֽ�䣬����һ����ȫ��һ��һ�Ĵ�ھ��䡣��Щ�������ڸ����ֵ���˵�������������ĵõ��������澭�����Ǿ����������ңԶ�Ĺ��ݼĸ��ҵġ���ʱ���ǻ�û��������������ȥ�����ݳ�����ס��������ĵ�������Ƕ��Ǻܶ������˵�������վ���ܳԹ�˯��
��һ�����ųơ��ְԡ��������ˣ��ֽ�ʱ�������������������ۣ���������һ���������ߣ�������������Щ��ѣ��ڹ��ݹ�����ʱ������ͬ�·�ӳ�������۳Է�����������ʡ����ô��Ǯ�����أ������������ҡ���˳Է��ˡ����������壬�����۽����ˣ���һᱼ����棬���Ŵ��������ˣ������д���ˡ�����˵�����۵Ĺ�����λ�ܱ����ѣ�ij�Σ���С����ӿ㶵���ͳ��˰ٶ�Ԫ�ij����Ʊ��˵�������ۣ��ﱨһ�¡�����ʵ������������������
�����۶���������һ��ĸ�ԵĴ��飬�����������������ӿ�����ĵı�ķʽ�ĺǻ�����һ��С���ڹ����ݳ�����ҹ�ȶ࣬�����Ҫȥ��ݸ�����ȡ�������һ·�绰�٣�������Ȼ������˾����ǿ������С�����ع��ݡ�
�Ϻ������������Ͻ���Ҳ���ҵĺ����ѣ�����һ��ȥ�¹��μӡ����������ֽڡ��������ڶ������ֶӷdz���Ϥ�����Գ�Ϊ���ǵ����ֽڻ�ָ�ϡ������и������Ϻ����˵ı�Ƣ����ij���������������ҵ�ר����ţ����ɽ�����������۳������������������˶�������Ͻ��鶼Ҫ���ˡ���������������������������ҵ���������������������С����������£��������ֺȵ�һ����ˡ�
����һ�������������վ����ö���ǰ�������ڡ��ӡ��ưɵ������ij�ξƺ���������һ�ܣ�Ϊ��ɶ�����ˡ��Ӵ��������������ӡ������վ�д��һƪ�����ҳ�Ƭ��������������ֽ���ҿ��ˣ�������µû��ˡ���ʵ�����˾�Ӧ���а��бᣬ���Ǻ������ġ��������ͻȻ���˸��绰������̨���ʫ����������ҽ�����ϵ������һЩ��Ʒ����Ȼ��һ������ͨ��̸���µĵ绰���������Ժ��Ҿ��ñ˴˼�Ҳ����ǰ���ˡ��ٺ���������������ġ�ŭ�Ӵ��ѡ���һƪ�����ֳ��ģ������վ���������֯����ҡ���ݳ������������յ�Ӱ�������˴����ҷ���������һ���������İ����ֵ��ˣ�����㹲�ԣ���ľͶ�����ʲô�ˡ�
�⼸�������˸���һ�����·����Ӣ�۴�����Ķ�а�������ϵ۱�ؤ�������и��Ե������ң�ÿ�������˶���������ij�����֣��й�ͷһ����ʳ�������۾����Ա���С���䣬�����������С�ͳ�������Ƶ�������Ĺ�ͷ���ֶ��˳����������������һ��̨��أ�����Ĥ�ݺ��·��Ӵ�����˼�١������顢���Ρ��½����̨������������֣�����ij��������ػ��䣬������ʦ��һ�𣬾������һ�������Ͻ���ֱ�ӣ����Ϻ������ġ���¥����Ϸ�š��ļ�����÷���ӻ����Լ������¡���ʱ÷�������ݳ����뵽��λ�����������ţ��ͺ�̤ʵ��
��Щ�����˲������Ǵ������ʲ������֣������������綼�����ɡ���������굥������ΧҲ�кܶ�Ů��˿����w��n��r��n��sh����w���������Dz���Ů���ѡ�����������־���������è���μ������ɳ��ܱ���������������Ǯ��������ȥ��ۡ�̨�忴�ݳ�����Ʊ�ͷɻ�Ʊ�ϡ�ǰ����մ������λ���ϴ�ְ��Ұ����Ϊ����������Ҫд���ġ�
�����ۣ���Ϊһ��ʱ�д����ʣ�������Ů���ƣ����Ǵ���ûЯŮ�ѳ�ϯ���ƾ֡������������Ķ�����Щ������צ�ļ����֡���˾�֡�ij��ȥ�ɶ���������������һ�£���������һ���ưɣ�����һ��ȥ�۾������ˣ��ɶ�������Ư�������ȵ��˼ҹ�����ڨʱ����ȴ���ڽ����װģ�����ؿ��顣
�������ң��й�Ϊɶû��Ů�����ˡ�����˼�õ��𰸣�����һ�����֣��ͱ������ձ�ΪŮ���Ѽ������ˡ���Ϊһ���ֶӳ��裬Ҳ�ͳɲ��������ˡ�
���ڣ��������˶����Է��ԣ�ָ�㽭ɽ���������������Ҳ��������û����������ϵ��и��Եľ�ʣ����ô����ļ�����ϣ�����������èһ���������ǣ���֯ҲӦ�ö�������ǵĸ������⡣�����Ǿ��ʵ����ֽ�˵�ߣ���ʵ��������������Ҳ��Ҫ��˵�����ǵ����������һ�����ӡ����ء���ʡ�
һ���˹�����
һ�굽ͷÿ��Ҫ�������˴��������ھ�����������ģ�һ���˹���
�����걱���Ĺ������������ɻ����������ص������IJ�ɽ�¡��о������ں����ţ����ڴ����ķ�����û�е��ӣ�û�ж����Ӧ�ꡣ��������һ������⣬�������Ψһ�������
��Ϧ���磬��������̨��ɹ̫�����ڱ����������һ���ݳ�Ʒ�������ϵ������ֱ��ͨ�����͡����ϲ裬����ůů�ģ������ھӼҵ����㣬���������ֺ���ʲôҲû�롣
ȥ�괺�ڣ����ڱ������ġ���һ������ȥ�ưɺȾƣ���Ϊ����ʲô�����أ�����Ǵ�������Ƕ���������һ���ҿɹ�������ڶ������룬�ȴ��������֡��������ҹʵ�����ģ��ؼң�����Ҳ���Կ�ס����ڳ��صķ������ⷢ���������ʲô���ڣ��ѵ�Ҫ���˽�ͷ�𣿺�����绰�������������ˣ��������ʣ�����������ȷ��������ӵ��������ң����������Ƕ������۵����ţ����賿�˲Ž��ݡ���Ҳ�Ͱ��ˣ������Ƶ��ǣ���ȥ�ŷ��֣�Կ��ʹ��������һ���ڴ�������˺ü��ٿ�������ѡ�
��������ڴ������꣬�¾��ľ������š�
��Ϧ֮ҹ��һ�������������Ѿ������ˣ�һƿ��ƣ���ƿ�¹���ơ�ơ��о����⣬�������֡��Լ����٣������Լ�����
��Ӳ�ɽ�Ϲ��������纣���Ĵ���������ӿ�������������е�ҹ������������Ұ�ķ簡������Щ�ߡ������������Լ��Ĵ�����
���������������DZߵĴ����ݵ��Ķ��ˡ�˵�����Ѿ���̨�ˣ������е��ܵ��������ţ��ֻ���ʼ����ž���ؽ���������ף�����š���ʵ�Ҹ�ϲ��������ġ���Ȥ�İ��껰�����������˶�����̫���ˣ������ӵ��Ķ��Ŷ���Ⱥ���Ĵ��������ص��Ҹ���С���ӡ�������һ���õģ��Ͽ���Ū�ط������ѣ�����������գ����β��벻����
��ҹ���ˣ�����̨��ҡ�������µ�������ţ�壬�������˵أ��о��Լ�Ҳ�ű����ˡ�
�ڶ�����ѣ�����������������̫�����Ұ��ꡣʢ����ȴѽ�������ɻش�������ĵ�һ�죬��һ�Ű�ֽ������дʲô�ϻ������������������¿����ġ��׳�һ����ʱ�⡣
��һ��������������һ�����⿰�����ꡣ�����������ּ��ְ��������ָ��������������Լ������˺ü��ء�
�����ˣ�Ҫ���塣�����Ł硪����Ұ���ӡ��ֶӵ��������ڴ����ġ����¡�����ר��������ů���α���һ���ųǣ���һ�������ֶ����ο͡��ݳ��Ǿŵ㿪ʼ����һ��������������͵��ˡ�������˵��Ҫ����ռ����λ�������ﰵ����Ц��������˭�������ݳ�����
����������ϣ�����Խ��Խ�ࡣ�ұ����ó���λ�ã����ڰ�̨�ԡ���һ�����̨��Ҳ�������ˣ����Ұ��ŵ��ź�Ľ����������Ʊ���˽��ͣ�������ֻ��С��ʿ������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