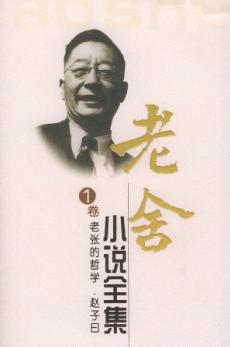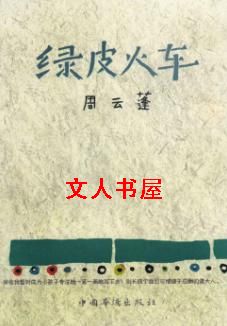��Ƥ��-��1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2
����ȥֲ����·�����ϣ�����һ�������۵�������գ�����һ�����£�����������ɽ��С���ӣ�����һ����ʮԪ�������Լ�߰�ƽ���ף������к����������������˼��ڣ�һҹ��磬�������أ�����һ�ص����ӣ������١����峿�������������۵�������һ�����ؼ��ȥ����������ʱ����ֻʣҶ���ˡ��ݺ���һƬ�صأ��и����й�����ǰ�Ĵ�������������һ�������Ů֪�࣬��֪�����������ˣ�Ϊɶ�������磬��˵���к���һ���ӵ�����������������Ƿ��������Ǹ��Ǹ���ٿ��صģ��������Ը������ŷ��ӣ����������ˡ����죬�����ڷص�������һ����ʱԡ�ң����ϸ����ӣ����ϼ�Ͱˮ������Ŷӣ�Ů����ϴ�����Ż�����ˮ����������������Ƿǡ������и�Ů�������ú�Ư��������Щ�˼�װ̽������������������Ȼ���������ǰ�������Ź�������ù���
���ϣ������ܿ��������ij�����Ů��ȥ�ϲ��������Ƿ���һ�������ֵ�Ͳ��һ�����Ų˵����������ǰ�滤�ݿ�·��
��ɽ��ˮ�������˵ľ����ҵĴ�ʫ�趼����ɽ��д�ģ��������ڱ����Ľ��ǣ������������������֡������ѡһ����ʱ����ռǣ�
�ҵ�С�ݺ�������ľ������Ұɽ�£�������һƬĹ��Ĺ�ڷ���ʮ�������䡣�����õ�ʱ���۷���������������⣬��һ�ִ��ߵ����á�һ�������ϸ���Сʱ��ʱ�仺���������̡�w��n��r��n��sh����w�������о��Լ�����һֻ��������е����档����һֻè��һֻ����ÿ���Ҹ���������Ƕ�����Ե���������������ˣ����������ƿ����ǣ����������һֻèͷ�ұ�һֻ��ͷ����ԾԾ���ԡ�������Ȼ������ҡ��������֪���������ִ����ֿ��ֵ�������
����������Ϊ�˶�����룬������ǰ�ָ���һ���·����������۵������˺�һ���ۿ���Ҫ�����ˣ���ٵĺ�������ӳ������ˡ�һ��֮�£���ŭ���������ǸϿ���ˣ���Ȼ��Ҫ�ջ�����ʹ��Ȩ�����ǵģ�����ͷ�ϻ��з�����������ֶ������۵��Ƶ��ˡ���ɽ�Ǹ����˻��˶�Ը�ⳣס�ĵط��������ݺ��Сɽ����÷��������������λ������Ĺ��������ʯ��ͨ��ȥ�������ɡ���������Ĺ��������һ��С�֣�һ�����嶼˯�����棬һ�������į������ũ�����컪����˯��ɽ�������ԣ�Ĺ���߲������������˼��롣����Щ��ͨ�˵ģ������۵�С����������ʯ�IJ��У�ż�����ᱰ��̽��ͷ�����������ű����Ƶġ�����һЩ���صĸ�ǽ��Ժ���������ľ�����������ָ�㣬�Ǹ��ط���ʲô�׳�ס���ģ����ȴ��ţ����ܿ�����
3
1995�궬�죬�Һ�Ů��ȥ�ൺ���ڸ�ɽ�����˸�ƽ������Ϊ�Ƕ�������������Ԫ����ˮ��ѡ�
�����Ǹ���������ɽ�����裬�ϸ��������Ƕ�ˮ���ʹ�ã����ڷ����ǽ��д�Ͼ�ʾ��˷��Ƿ���ൺ�Ķ����ֳ����䣬����Ҳ����ס�̹ǵĺ��硣������û���κ�ȡů�豸�������������ڷ��������£�����������û�ˡ��ҿ������и���Ů�������ֽ�ٻٻ���������ǿ�����͵͵���������˸���¯�ӣ����Ƿ������ý����ĸ��ð���������ٻٻ����������ţ����������ǵĴ�������¯�Ӻ������ˣ�����һ���裬�����Ƿ�����ģ���һ���ǡ����ں�����ߡ�����ʾ�ŷ��������ˣ����ǸϿ�β�ͷ���������Ǻ����������裬����ζ����ů����ʧ��������Ǯ�����ˣ���Ƿ�˼��췿�⡣����ٻٻ�����������裬�����������˿����Ϻ����ִ��������´���ʱ����һ�䡰���ں�����ߡ����������ٱ���Ц�ģ��ɻ�û���꣬Ů�Ѿͺ�������һ����ˡ�
4
�����������˸����涼�Dz����ķ��ӣ�����һ����ˮ���������һ���塣��������������������У�����̫�����տ����ת�����������⣬�ƽ�һ�����أ�̫��һ����������һ���������Ļƽ��������飬����ʲôҲ���롣�����и��������ǰ�ǵ��˹�����������д��ƪС˵���������dz�����Լ������˵������д����ġ��Ҹհ�ȥ���ã�����С˵д���ˣ�Ҫ��ȥ�ˡ���˵�����������д�裬�������н����ס�����¡����и����ѣ��Ł磬��������һֻ���н����ֺ����ᣬ����ȴ�ܱ��������˼����ñȶ�è�����ӣ����ˣ�����һ�ڱ������������������������������������ţ�Ҫ��������Ԫ���ʣ�����ô��ô������˵��������ֻ���µ��ĺ�ĸ���������µ����Է�С��������������������һ�㣬���ٻ����𣿡����ԣ�ֻҪ�Ł��к��ҡ����ܣ����ȼ��������Ҿ�֪�������ִ����ˡ�
5
���ڱ������ӹ���·�¡��������ԭ���Һ�Ů������2010��ᵽ�����ˡ����˸�Сľ¥���Ա��и��ţ����������ţ��ⲻ����������ʾ��Ҫ��������ɺȻƾƵ����������ס��С���ӽ���Ҿ�������⣬�Dz�������С�ӡ����ϣ����ڴ��ϣ������л������������Ͳµ������������������ο�����ȥ³Ѹ�ʾ��ˡ����ҼҲ�Զ������μ���������ݣ���Ԫһ��Ʊ��������ľ������쿴����һ���ο͡��Һ���������ȥӦƸ�����˵Ĺ�������Ҫ���ʣ���ס���С����������������ƾƣ���������ţ�����ε������滹��һ���Ƥֽ���ҿ�ֽ�������籡�������þƵ�����һ������һ�ȣ������죬���ڴ�ǰ���ȸ�����Ȼ��������Dz�֪��Ϧ�Ǻ����ˡ����ڿ���һ����Ϻ�꣬ż�о���һ������Ϻ�������Ƿ��䣬����������ǷŻ��뷹��ԶЩ�ĺ����������Ϻ�����ˣ����������Ϻ��ͻȻ�����ˡ�ԭ�������ϵ�����������Ϻ�ùֲ������ӣ�Ū��˭Ҳ���ҳ��ˡ����룬��һ����ij��Ϻ���˾��������Ʋ�����������һ��������Ϻ������ˮ��֮�еľ�������
6
����һ�������ķ��ӣ��DZ��˵����塣��˵����Ϊ����֮������������ӣ��������ˣ��ɹⲻ�á��ҷ������ۣ��ҵ���С���ҡ���ֻ���������װ�ϼ�յ����ǿ��������ʵ�����������õ�Ҳ���ã������������Ρ������Լ��ڰ�������������磬д����Щ���֣��ִʲ��������ε�ͼ��������һ�������ڣ��������˵ģ�����ҹ���ô��������������ˣ�˭����������Թ���еط�ס�Ͳ����ˣ��ܻ��ž�ͦ���ˡ������뿪��䷿�ӣ���������ʱ���ǽ�����һ��ո�µ����С��Ķ������з������Ķ������пշ����⣬�����߲��ص��ģ�����Ҳ���ص����������ҽ�������������������֮���
�ܵ���ô��ȥ�Ķ�
ΪɶҪ̫����
�丸˵����������������������������Ҫ��й�����ڿ��ˣ��ѻƺӺȸɣ��㶼��������ˣ����ߵ���Ҳ�������٣�������Ҫ��̫�����ܣ�ֱ��·�ϵ�С��Ҳ�ɺ��ˣ��Լ�����ǰ�����ȿ�����ȥ���Ⱦ����ˣ����������֣�������������ֹ�ʡ�
����ȥ����ȡ����
�����˵����ʮ���ǧ�һ����ͷ�͵��ˡ��������ʣ�������ʦ����ô�죿��Ҫһ����ɽͷ����������ÿ�����ֶ�Ҫ�¸���ԣ�©��һ��������һ��ծ���Ժ���������������������ԣ�һ·�����ᄀ��û�ͷ���һ�������������һ����Ϻ����ӣ�������ص��ҷɣ������ջ��ûص���һ��������һ��Ҳ���У�һ��һ�ݶ�������Խ��
���������ķ���Խ��Խ�죬�����������һ������һ����������ȥ����ɽ��һ���ڿն����㵨�������������ٵ�Ҫ��Ǯ������һ����������˦��վ̨�ϣ���û�ع�ζ���������ž͵εδ����ſ��˴��죬��ܺ�����Ů��ȫ����ȥ�������������ͺ�¡¡�ؿ����ˡ�
�����ķ��ۣ�����������һǧҹ�߰˰٣���������Ĵ���Ѫ������Ǯ����ѽ�ϣ��������Ӱ�Ӷ��������ˡ���ת��ȥ�����߳�����ɣ����ˣ��ۿ��š�С�ֵܡ��Ƚ�Ҳ�����������ܵý����ڱ������ϴ�硱����ת��ȥ�����Ǹ�����Ī����
�иǾ��в�������һ�꣬�ؼҷ���ס�˴�뱲�ӵij��������ˣ��ܲ�Ķ���⣬����ڼ��ſ���·��ֱ���������Ŷ��������裬��֪�������ˡ���������յ�Ѱ�Һͳ���Ů������·��С�ֵ������Σ�����·���һ���ذ�����������������汲����С���ݡ�������Ϸ��ӡ�˭˭���˵Ĺʾӣ��������Ƶ�Ų��һ��ͳһ���ܣ��˴˼�Ȯ���ţ�����ţ���༰��
�տ졢�ؿ졢���������������Ѿ�ʧȥ�������˵���Ƥ��Ȩ������;ûʱ�䷢�����£����ǻ��ౣ�־��룬�·����л���β��
Сѧ�����С����С���ѧ��һ�����µĸ�Ч����ˮ�ߣ����»���ţ���ӣ�������ŸϽ�ȥ������ǧ�����Ծ��Ĵ�ĥ��ǧ����������٣���Ȼ���ף�Сţ�ѳ��˲����ϵ�����������ţ���ͷ��
������ᣬ�Ӱాҹ�ϸ��ӣ���ɥʧ�˼��ں�˯�ߣ��ܴ��ԡ�������������ҧ������Ǯ������֪���ļ�����������֢����������Ѫ������ǹ�����������ֵø���ʦδ���������������ͺڷ��ˡ�
ȫ����˻ᣬ������߸�ǿ�����꣬��������ںš���Ӣ�������ܲ����빲�����塱����ü�ǧ���˵��ӡ������ܵö�����������ˣ���˭Ҳ��֪��Ҫȥ�Ķ���������ͷ���ܣ���Խʨ�ӡ��Ա������������DZ��ˮ��粻����˼��ԭ�ش����������DZ����Űѵ�����������Ժ����������������������˻�δ�����������ǣ����Ǿ��ȵػ�ͷ����үү�����ǣ����㡣��
����Ҫ֫���ˣ�ʱ�����ѽ��ˡ��������˲�����ô���ˡ�����ʵ���˹�������ۣ��ѹ�˦���������ۺڰ����������˺���ı������ˣ��ù������ǵ����أ�֧�����ǵĺÿ�������̣�����ǵĴ���ˮ����������̫����������֮·�ԣ����dz����������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