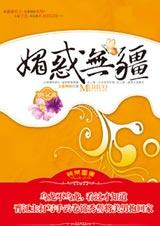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转弯,还有几个座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眼神奕奕,面容雅静。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我对导演刘璐说,谈话节目请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实我哪里在想谈话。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朗声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避注视,劝阻噪音;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闷。因此,即使我们这批早已对拍摄现场失去兴奋的人也无法想像别人对拍摄现场的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这事说来话长,但呈现方式却极具感性。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还曾以此命题一个作品,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早已成为一种公约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担忧市民来这里探访名家,形成围观。
但是,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倒逆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想到这里,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对导演刘璐打个招呼,便对着镜头说:“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
法国胃口
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我和一位现在很出名的旅法作家朋友从下榻的京华饭店步行很长的路去动物园游玩,一路听他在讲法国美食。后来还是在新加坡,当时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陈瑞献先生请我到一家以马可·波罗命名的法国餐厅吃饭,但陈先生自己却已经只用素食,而为我点的法国餐食却格式完备、程序整饬。他原是一个有资格的美食家,闲坐在一旁慢悠悠地讲述着法国餐食的奥妙,这一切,是我在法国美食上的启蒙。
法国文化部在一九九〇年发动了一个“唤醒味觉运动”,而法国教育部也批准向小学生开设烹饪艺术的系列讲座,教师则需要接受高水准的烹饪专家的培训。这架势,无疑是以国家力量把传统的美食文化推到主流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普及,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作为世界顶级的旅游大国,法国的学者们又在考察“烹饪遗产”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条条以吃为主题的线路,使他们的美食文化进一步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从历史看,罗马人战胜高卢(古代法兰西和周边地区),实在是把欧洲的胃口狠狠地撑大了。高卢人强蛮尚武,胃口之好把罗马人吓得不轻,而罗马那时已经讲究奢华的排场,于是把排场和胃口融为一体,后果不难想像。一切荒唐的构想都与吃连在一起了,有时宴会上推出的蛋糕之大,居然藏得下乐师、雕得出喷泉。十分壮观却十分粗蛮,那口味其实很难说得上。
在这里又要提到我以前在意大利仔细查访过的美第奇家族了。十六世纪这个家族与法国王室通婚,带来了佛罗伦萨的优秀厨艺,巴黎的饮食开始从排场上升到精致。巴黎人聪明,本来也早已厌倦了那种与口舌需要相去甚远的奢华吃喝场面,于是在佛罗伦萨厨师的启示下用心创造,很快就超过了老师,逐渐形成更讲究滋味和情调的法国美食。
当然胃口还是好,排场还是大,尤其在王室、贵族中更是如此,当时的高层厨艺主要也是为他们服务。例如那个路易十四,宫中为他安排饮食的多达三百多人,吃的时候各种亲信大臣围坐,看他用优雅的风度和规范的礼仪把大量的食品吞咽下去。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他一次吞咽的食物数量,简直难以置信,可称之为“非人的胃口”。明明是非人的胃口还表现出优雅,就便是法国宫廷贵族的作态。联想到慈禧太后用餐时也上百余道菜,但她只是就近拨几筷罢了。明明不吃还天天照上,这就是中国式的排场。两种排场都令人腻烦。
路易十六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之后,居然还当场吃下了六块炸肉排、半只鸡、一堆鸡蛋,胃口好得真可谓“死而后已”了。
对于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实有点浪费。法国路易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