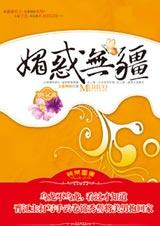行者无疆-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又不愿意走马观花,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酒窖。”我说。
“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
“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何况这个秘密还在传递。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而且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天然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足凉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安静。几百年前,这么一个小城,光酒窖就长达十五公里!那当然是延伸到了城外的地底,而且供应的范围也几乎没有疆界。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它们与地上的世界息息相连,却从来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述。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稳稳地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座,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瞭了玻璃壶一眼,像激光扫射,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洒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说完便示范,平平地端杯,轻轻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后人口,嘴部动了两动,便伸手拉过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来,更惊人的是,把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红酒也倾倒进去了。
由于这杯酒出现前经过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我们眼看着这种倾倒深感心痛。厂长知道我们的心意,说还要品尝多种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这当然是对的,但出于痛惜之情我还是偷偷把那口酒咽下了,却又不得不把杯子里的酒倾倒在陶桶里。
倾倒时尽量缓慢,细看那晶莹的琥珀红映着烛光垂直而泻,如春雨中的桃花屋檐涓然无声。
接下去,光头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杯上来,厂长一次次瞭过一眼报出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我们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倾倒,开始时还偷咽几口,后来连最清爽馥洌的也不敢咽了,因为已经感到身热脸烫,酒窖似乎也变得不再阴凉。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磐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我们相视而笑,每人脸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红。
走过长长的巷道我们又回到地面。厂长细心,在品酒过程中看出了我们最喜欢的牌子,一人送了两瓶,那种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铁门轻轻地关住了,外面,骄阳如火。没有下窖的几个伙伴,奇怪我们为什么耽搁那么长时间。为了抚慰,我们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给他们。
又是寻常街市,又是边远小城。如果没有特殊提醒,实在很难看出在这番景象的地底下,有如此深长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谁也不能说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你看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下竟然秘藏着如许醉意。连裴多菲和纳吉的热血都没有改变它的恒温,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干扰它的酣梦,那是一种何等的固执。欧洲有太多炫示在外的东西,但炫示在外的,未必重要。
大哉酒窖。
布拉格不后悔
1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厉,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我们没有赶上,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先已游荡了远近很多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总是懒洋洋的,令人恼火;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国家的整体环境彻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而且不仅是苏联,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容不得这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那种包围阵势恰恰反证了它的骄人风采,轧轧的履带声显得那么无聊。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时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听起来却并不反感,特别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每小时鸣响之时,钟下总是人群如堵,因为钟盘上会展现出一系列机械人形,生动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个景观。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礼在古钟下举行,让人遥想这几百年的钟声开启和闭合过多少人生。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传说由于这钟精美得举世无双,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人类最原始的保密法则居然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执行,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帝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杀的暴行。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后来到了布拉格蜡像馆,进门是城市历史部分,抬眼就见到那位机械工艺师,用白布包着被刺瞎的双眼,还在机械堆里不懈地摸索。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怀疑是否也像这钟声,在达观的欢悦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2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胡斯烧死时,古钟的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