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于坚定,不妥协地怀疑,你就会错过(或不满)正在转变中的科学发现,两种情况下你都在阻碍理解和进步。仅仅有怀疑主义是不够的。
同时,科学要求最强有力和最不妥协的怀疑主义,因为大多数的想法完全是错的,唯一把麦子从谷壳中筛出来的方法是批判性的实验和分析。如果你头脑开放到了盲信的程度而没有一点怀疑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能区分有前途的想法和毫无价值的想法。不加批判地接受别人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想法和假设就等于是一无所知。许多想法是彼此冲突的;只有通过怀疑性的调查才能辨别,某些想法确实好于别的想法。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明智混合是科学成功的关键。好的科学家两种思维方式都具备。在独处中,在自言自语中,他们产生了许多新想法并系统地加以批判。其中大多数想法永远不会向外面的世界公布。只有那些通过了严格的自我过滤的想法才被公开出来接受科学界其他人士的评判。
由于将这种固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适当地依靠实验,作为各种假设之间争论的仲裁人,许多科学家在大胆的设想即将来临时仍然缺乏自信,不愿讲述对奇迹的亲身感受。这很遗憾,因为恰恰是这个少有的狂喜时刻使得科学工作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显得更人性化。
没有人可以完全头脑开放或怀疑一切,我们都必须在某处确立一条界限。一条中国古代谚语建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来自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在那里稳定比自由更受重视,而且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不想受到挑战。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会说,“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但是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负责的、全面的、严格的怀疑主义要求一种需通过实践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坚固的思维习惯。轻信——我想这里一个更好的词是“开放”或好奇——同样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真的对物理学的。社会的或任何别的什么组织的反直觉的想法开放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必须领会那些想法。接受我们不理解的主张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好奇都需要磨练和实践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作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我将很乐意在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家庭式的幸福:人们真的在创造融合——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而同时,作为第二个特性,要求证据符合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应用于他们珍视的观点时的严格程度至少应与评判他们企图不受惩罚地拒绝观点时的程度相当。
第十八章 风扬起尘土
风扬起尘土是因为风想要吹拂大地,带走我们的足迹。
《澳洲丛林民间传说》
收藏家W·H·I·布里克和L·C·劳埃德
编辑L·C·劳埃德(1911)
当一个原始人追踪他的猎物,每时每刻他都在使用细致的观察,准确的归纳和演绎推理,如果将这些应用于其它事物,将使他获得懂科学的人的声望……一个“好的猎手或战士”的脑力劳动大大超过了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托马斯·H·赫胥黎
《散文精选,第二卷,达尔文:散文》
(伦敦:麦克米兰,1907)
选自《达尔文先生的评论》175-176页(1871)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发现科学既难学又难教?我尝试提出几个原因——它的精确,它的非直观的和令人不安的外表,它的被误用的前景,它的独立于权威的特性,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呢?阿兰·克鲁默是一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在课堂上,他惊讶地发现如此之多的学生不能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在《不平常的观念:科学的异端性》(1993)中,克鲁默提出科学之所以难是因为它不断推陈出新。他写道:我们,一个具有几十万年历史的物种,仅仅在几百年前才发现了科学方法。例如书写,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它的诀窍——或至少是因为没有进行非常严肃和积极的研究而未能做到。
他认为,如果排除历史事件的巧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科学:
面对科学的诸多显而易见的成就和益处,我们仍然敌视它,……仅此即可证明它是处于人类发展的主流之外的一个事物,也许只是一个意外和侥幸。
中华文明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火箭、指南针,地动仪,还系统地对太空进行观测并将其载入史册。印度数学家发明了零,使算术得以顺利发展因而推动了关于量的科学的进步。阿兹台克文明建立了比欧洲文明还要先进的历法,他们能更为准确地长期预测星球的位置,而他们自身却被欧洲文明淹没和毁灭了。但是这些文明中没有一个,克鲁默说,建立了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所有这些全都来自古希腊:
希腊人客观性思考的发展需要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首先是议会制。在那里,人首先学会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说服别人;其次是一种海洋经济,防止了孤立和狭隘主义;第三是周围一个广大的希腊语世界的存在,旅行者和学者可以周游四方;第四是独立的商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雇佣自己的教师;第五是《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文学杰作本身就是自由的理性思维的缩影;第六是宗教文学并未控制在教士手中;第七是将这些因素坚持了1000年。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伟大的文明是非常幸运的;它没有发生第二次。
我赞成其中的部分论点。古代爱奥尼亚人,就我们所知,最早系统阐述了是自然律和自然力,而不是神,决定了世界的秩序甚至世界的存在。就像卢克莱修所总结的他们的观点:“自然生而自由,摆脱了她高傲的主人,可以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发产生的,没有神的干预。”然而除了在第一周的哲学引论课之外,早期爱奥尼亚人的名字和观点几乎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提到。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似乎易于被人们遗忘。我们并不渴望保留对这些怀疑论者的记忆,更不要说他们的想法。试图以物质和能量的方法解释世界的英雄们在许多文化中出现许多次,只是被教士和垄断传统智慧的哲学家从历史中抹掉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之后爱奥尼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失传了。许多种文化,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尝试,但只有在很少的机会下这种思想能生根发芽。
仅仅在1万或1.2万年之前,植物和动物被种植、驯化,文明才开始。爱奥尼亚人的尝试距今有2500年了,而它几乎完全被抹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印度和别的地方通向科学的足迹,尽管是蹒跚的、不完全的和少有成果的。但是,假设爱奥尼亚人从未存在过,希腊科学和数学从未兴盛过,是否可能科学便再也不会在人类历史中产生?或者,考虑到许多文化和许多其他的历史进程,在某个地方,或早或晚——比方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或在未被征服者干扰的中美洲文明边沿的加勒比,或在黑海岸边的挪威殖民地——难道不会出现各种因素恰好汇集使科学登上舞台的情况吗?
我认为,科学思考的主要障碍不在于问题本身的困难,即使是受压抑的文化也要依赖复杂的智力成果。萨满教巫师、术士和神学家在他们复杂而神秘的技艺中也有高超的技巧。不,阻碍来自政治或僧侣的统治。在那些缺乏新的挑战,不管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文化中,也就不需要根本的变化,因而不需要鼓励新颖的想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可以被宣布是危险的;思想可以变得僵化;对不允许有的想法的制裁可以强化--都不会有太大损害。但是,在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生态或政治条件下,只是照搬老一套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那些不盲目遵循传统,也不试图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自然的或社会中的一切,而是乐于接受宇宙教给人们的东西的人将得到奖赏。每个社会必须决定,在开放和僵化的连续统一体之间,安全点存在于何处。
希腊数学向前迈出了光辉的一步,而另一方面,希腊科学——它最初的发展是很幼稚的并且通常对实验蒙昧无知——充满了错误。他们相信视觉依赖于像雷达一样从我们眼里发出的一种波,在我们看到的物体上反射回眼中,却无视我们在夜里看不见东西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在光学方面有了重要的进步。)不考虑孩子和母亲明显的相像,他们相信遗传特征只由精子携带,女性只是被动的贮藏所。他们相信一块水平抛出的石块会得到某种浮力,因而比同时同高度垂直下落的石块在空中停留时间长。对于简单几何图形的迷恋使他们认为圆是“完美的”;不考虑“月中人”(月亮中的暗影)和太阳黑子(偶尔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可以用肉眼看到),他们坚持天空也是“完美的”;所以,行星轨道一定是圆的。
仅仅是脱离迷信还不足以使科学成长。人们还必须想到向自然提问,并通过实验验证。这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例子——如厄拉多塞对地球直径的测量,或恩培多克勒阐释空气物质性的漏壶实验。但是在一个手工劳动被认为是低下的,是只适合奴隶干的社会中,比如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实验方法是不会兴盛起来的。科学要求我们既摆脱严重的迷信又摆脱严重的偏见,教会和世俗政权强加的迷信和偏见常常是狼狈为奸。毫不奇怪,政治革命,对宗教的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兴起会同时发生。从迷信中获得自由是科学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同时,不可否认,从中世纪的迷信转变到现代科学的过程中,像受到了一种最重要观念的深刻影响,那就是,一个创造了宇宙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只创建了人们赖以过活的戒律还建立了自然本身必须遵循的法则。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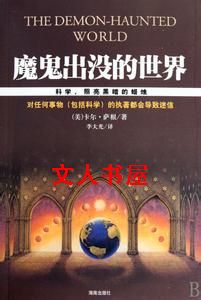



![[综]有村民出没请小心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4/4603.jpg)
![[综恐]这坑爹的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4/460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