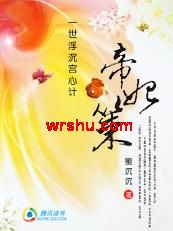唐宫妃策-第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此一来,反倒像是王叔文夹在陛下和太子之间作梗一般。
李淳想了想,又道:“王翰林办理此事,劳苦功高。着兼任盐铁转运副使一职,监督此事!”
满殿的官员口称“太子殿下英明”,其中却仍旧不乏有人心里打起了小九九。王翰林既然已经亮明了身份,说是圣上叫他去查的,那么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打着圣上的旗号来上的折子。
实际上,应该说折子不是上给太子的,而是上给圣上。然而,太子虽然处理了问题,却直截了当的,当着群臣的面驳回了他的折子。
摆明了,太子羽翼已丰,即使圣上病愈,这两位恐怕也未必是一条心的了……
为朝廷尽忠,是每一个臣子都必须兢兢业业做好的。然而,在朝廷里又是该为谁尽忠呢?皇帝是皇帝,自然要尽忠;可眼下皇帝体弱多病,太子正青春年少。除了眼前这位太子之外,其余的皇子,还真没有堪当大任的。
太子便是未来的皇帝,倘若一个不慎站错了队,岂不是就此葬送了仕途?
圣上的身体似乎确凿有了好转,渐渐的有了些政令传出。据说,这些政令是由陛下亲授身边伺候的宠妃牛氏,再由牛氏告诉内监副总管李忠言,李忠言再传递给王叔文等人的。有时,圣上的诏命也直接写在白麻布上,由李忠言递与王翰林,外面皆称作“白麻内命”。
由“白麻内命”传出的政令越来越多,王叔文等人先后上了数十道折子,历陈时弊,进行变法革新。
第一件事便是宫市的五坊使。此事早在昔年念云初进东宫、陈明东宫积弊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李诵和李淳都十分清楚。
只是碍于当时李诵在东宫一向韬光养晦不愿出头,又怕先帝以为太子四处收买人心,故一直未能向先帝上表陈明。
当时念云便在东宫立下规矩,明令禁止东宫采买欺压百姓,亦不许虚报价值。因东宫规矩严苛,赏罚又十分分明,因此十余年来维持得极好。
如今圣上即位了,李淳又监国独揽大权,罢免五坊使一事自然是按照东宫旧制订立规矩,严令禁止内监鱼肉百姓。
接着是进奉。
按照先帝时订立的规矩,除盐铁转运使以外,各州县地方官员每年皆有进奉,即私下向皇帝进贡财物、金银珠宝等。节度使多数每月进奉一次,称为月进,州刺史、地方幕僚等人闻之,为了取悦先帝,每月或每半年也都有所进奉。
更有甚者,每天都有进奉,称为日进。先帝每年收到的进奉约有三十万缗,最多的时候能达到五十万缗。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地方官员甚至于节度使的月俸都不高,不过勉强维持一家人的中上等生活而已。
这一笔财物,自然也是民脂民膏。有这进奉的制度,一切减免税收、休养生息的政策,都会变成一纸空文。进奉是皇帝要的,又没有其他正当的来源,压榨百姓、收受贿赂在所难免,官吏的贪腐也就相应的根本无法整顿。
柳子厚上表,请求取消进奉。李淳代圣上拟旨,准奏,并规定佃租税、课税之外,不得以任何名目征其他杂税,且不得以各种方式向朝廷进献财物,并免除之前数年里百姓所欠下的佃租税和课税及各类苛捐杂税。
取消了进奉之后,便是对全国上下宣告,圣上不喜欢贪官污吏。吏部及御史台便开始整顿官员收受贿赂、贪污等事,不断有弹劾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折子上上来,太子一一认真批复。
便有一批小官吏因此而被贬——自然,被贬的官吏中亦颇有一部分曾经与舒王过从甚密者。
前边朝堂上改革,后边这内宫,李诵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李诵命王良娣和牛昭训两个查了宫里的开支账薄,发现每月伙食和月俸开销十分惊人了。
李诵姬妾数目不少,有二十余人,但是对于皇帝来说实在算不上多。况且除了其中十多位有名分的,剩下十余人不过是通房丫鬟,属于半妾半婢的身份,便是以后册封也不会高于六品宝林,后宫的正殿大部分都会空置出来。
在东宫时上下都奉行节俭,因此使用的丫鬟奴仆也相应的比较少。如今搬至大明宫中,宫里丫鬟内监众多,甚至无人居住的宫殿都安排了七八个人,人员冗杂。
但那些无人居住的宫殿,每月打扫一次,清扫一下落叶和灰尘也就罢了,平日里根本无事可做,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
先帝宫里更养着教坊乐女千余人,虽然圣上初登基,龙体欠安,太子又忙于政务无暇取乐,但那些教坊乐女们却日日拿着俸禄,清闲得很。
李诵遂以白麻内命下诏,令裁减宫中冗杂人员。
不想,此举却在宫里引发了轩然大波。
第一百零五章 一朝有二君()
早朝的朝议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六福拖长了嗓音:“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众臣都无要事,并没有人站出来。李淳抬头看向六福,他此时应该宣布退朝的,然而六福却不知为何避开了他的目光,而是望向了大殿之外。
这时只听见殿外有人大声道:“奴才等有冤屈,特来面见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是个太监的声音。李淳一愣:“进殿来说话。”
外头那人道:“奴才等身份卑贱,不敢进殿。”
嘴里这般说,可若真是觉得自己身份卑贱就不至于闹到朝会上来了。李淳于是吩咐道:“无妨,进来罢。”
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竟是大明宫的内监总管刘贞亮带着一大群徒子徒孙,浩浩荡荡数百人,躬着身子迈着太监的细碎步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来,队伍太长,以致于从宣政殿里一直站到了殿前的台阶和广场上。
待刘贞亮在最前头跪下,所有太监亦跟着跪下,齐齐整整地磕了三个头。
这刘贞亮乃是这次发动宫变、扶陛下登基的首功之臣,李淳连忙起身去扶他,“刘公公请起,不知何事要鸣冤?”
刘贞亮倔强地伏在地上不肯起身,大声道:“陛下嫌弃奴才等残缺之身伺候不周全,要大肆裁减宫中内监,还请殿下劝陛下收回成命,给奴才等一条生路!”
李淳两条眉毛都快要拧到一起去了,他这父亲是怎么回事,如今终于当上了皇帝,就以为真的能随心随欲了么,丝毫不会顾念全局,光顾着添乱!
既然闹到这宣政殿里来了,叫他来收拾烂摊子,那就该叫陛下付出点代价才是。
李淳于是道:“刘公公言重了。陛下也是好意,宫中既然使唤不了那么些人,便也好叫众人都自谋个前程,如何说是不给生路了?”
刘贞亮会意,又“咚咚”磕了几个响头,声泪俱下,大声奏道:“宫里的公公们都是穷苦出身,自幼进宫,与家人早就失去联络。上无父母兄弟可倚靠,下无子孙儿女可傍身,都是断子绝孙的人,身子骨也不成,出去到了外头,连猪狗都不如!这做了宫里的奴才,就只能盼着到死都是宫里的人,半路离宫,可哪儿还有活路啊!”
后头跟着的一众徒子徒孙都跟着哀哀戚戚,潸然泪下。
内监都是受了宫刑的,并无生育能力,因生理不全,或受宫刑时留下些后遗症,年纪略大便多半都疾病缠身,尿失禁、腰酸背痛基本上个个都有。
一般人都不愿入宫做内监,但宫中旧例,每隔数年都强制地方进献一定数量的内监入宫服侍。因此地方官便强制一些交不起赋税或欠高利贷的穷苦人家的男孩受宫刑进宫做内监以抵债。
内监受刑时大多年幼,因此并无子嗣奉养,晚景多少都有些凄凉。若一辈子在宫中伺候也就罢了,便是老迈,宫中好歹还能找人医一医,死了也能赐一口薄棺装殓。
但皇上此时下令裁减冗员,这些内监离了宫,可怎么生活?外头百姓怨恨五坊使已久,难免不把敌意转移到这些出宫的老太监身上。
身体缺陷带来的病痛,外人的歧视嘲讽,加上又无子嗣可倚靠,入宫多年,家人早已寻不到了,他们将何以养身?
刘贞亮偷眼见一众文武大臣都有些动容,又继续说道:“奴才等对先帝和陛下忠心耿耿,倾尽全力拥护陛下登基,不说功劳,也该念奴才等的苦劳啊……”
李淳发动宫变时便是找了神策军的首领来护驾,又联合内廷宦官里应外合才成功助陛下上位。神策军一向是掌握在内监的手里,可以说这桩事里宦官功不可没。
李淳等他说完了,方才环顾四周,问道:“众卿以为如何?”
众人心里都打着小九九,明知此时是陛下的旨意下得太草率,可又不好直接反驳,更怕话没说好得罪了刘贞亮,因此都面面相觑的不说话。
李淳看向王叔文:“王先生以为如何?”
王叔文向来是瞧不起宦官的,自然是乐得看见陛下削减宦官的人数和势力。可现下闹到宣政殿来了,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叫刘贞亮这么一说,倒是叫人人都瞧见了是陛下过河拆桥。
他只好上前一步奏道:“陛下素来节俭,如今有意缩减宫中开支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臣以为,不必骤然裁减,可令各州府逐年减少进献的内监人数。”
李淳点点头:“王先生说得有理,既然如此,不如王先生和本殿一起去太和殿面见陛下,陈明利弊。”
王叔文只得答应。
次日,听说太子亲自上表,为内监求情,力陈其晚景凄楚、身世飘零,陛下深受感动,怜悯宦官离宫后生计无着,于是收回成命,另外下旨,将自愿离宫的宫女三百余人、教坊乐女六
百余人赐钱放归。内监之数除个别自请离宫者外,基本没有变动。
陛下已经不甘于“病倒”在太和殿了,他正在慢慢的“病愈”,白麻内命的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开始慢慢的全面施行他的“新政”了。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