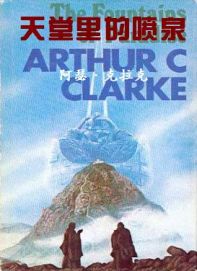时光里的欧洲-第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典时代,而是一战之前维也纳古典时代的终结。这是书写那个时代的最好的书。
“每一个不把一个经历看作一种仅仅是个人的事件而看作一种对自己智力的挑战的人所揭示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一个经历因其在一系列合乎逻辑的行动中的地位才获得自身的意义,甚至自身的内容。然后他也会对他所做的事产生较淡漠的感觉。”
巴黎·浪漫主义·公元1848年
之前走过很多站,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些出名,有些不那么出名。在很多站只有一两个对现代人来说熟悉的名字,比如莎士比亚,比如塞万提斯。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卓越人物零星出现,每隔几个世纪才有一位足够照耀历史的天才人物。可是在这一站,我们能见到的著名人物比前面加起来还要多。
今天我们说起古典艺术,作家能想起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画家能想起莫奈和凡·高,音乐家能想起瓦格纳和肖邦。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古典的,他们的创作方式与今日不同,他们生活在被两次世界大战所隔绝开的古典世界。我们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画作,去音乐厅欣赏他们的乐曲。我们把他们统称为古典艺术,将他们高高挂在古典的殿堂。
然而,对真正的历史来说,他们绝不古典。他们都是大革命之后的现代艺术家,一出场就是反古典的、革新的。他们是各种现代革命的参与者,其激进的姿态远非平庸的我们所能及。他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非都生活在高雅殿堂,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生活在高雅殿堂。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他们当作古典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艺术爆发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艺术爆发绽放出来的光芒太过炙烈,遮掩了在那之前的20个世纪。当我们回头看时,只看到这片光芒,看不到光芒背后。于是革新者成为标杆,反古典者成为古典的代言人。
19世纪风暴的中心在巴黎。巴黎是历史的屏风。
【大都会】
19世纪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代与古代的真正转折。“现代”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指的就是19世纪。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转折的世纪。大航海从15世纪开始,金钱经济16世纪兴盛,殖民地17世纪打得热闹,民主政治18世纪走到台前,但是人的生活并没有进入由工作与购物所组成的现代世界。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将以往这些变革汇集到一起之后,世界才有了彻底的转变。
商品和大都会完成了这最后的一步。
商品,哦,那琳琅满目的商品!19世纪是人开始相互依赖的世纪,没有人能独自生活,如果不购物,人们就活不下去,衣食用度不再靠自己,街道成为索求的摇篮。商店开始充满街头巷尾,都市建起玻璃拱廊街,拱廊街里充斥着购物的人们,用重复劳作一天所得的硬币换衣服和面包。人们开始在路上生存,路上有了咖啡馆、酒吧、舞厅和剧院,人们劳作之后并不在炉火边围坐,开始到街上到咖啡馆快活。一切都有了价格,谁的衣服优美不再取决于母亲,手里有支票的人受到一切人的礼遇。航船在港口吞吐,轮渡载满货物。人们到公司找工作,为千里之外不相识的人锻造自己永远用不到的零件。
所有这一切都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它们属于且只属于大都会。
19世纪见证了大都会的诞生,人们进入工业的世界,不再有世代相袭,不再有贡赋,人们用金钱支付所有服务。雇主与雇员算得清楚,陌生人与陌生人在商场的转角擦肩而过。这是形形色色的人出没的地方。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戴礼帽的体面绅士,他们赌马谈政治,做债券投机,左右商业,认为没有工作的都是懒汉。工厂老板在轰鸣的车间跺着脚喊加快。经纪人开始出现,他们转着眼珠拉拢机会,像给抛媚眼的美女寻找客人。流浪艺术家开始在街上散步,相信自己才是时代的主人,是新的贵族,精神贵族。孩子为硬币工作。女人开始走出深闺,展示华丽衣服,在香榭丽舍大街一掷千金,顶着树荫走模特步子。
所有这些都是巴黎的剪影。巴黎是大都会的典型,商业文化的中心。它不是最早工业化的地方,却是现代商业最蓬勃的地方。19世纪的巴黎是世界商品会聚的焦点。巴黎承办过6次世博会,1855年磅礴的水晶宫为世博会所建,号称能容纳万国产品;它喜欢现代美学,埃菲尔铁塔在1889年落成,以钢筋铁骨的怪模怪样俯瞰着巴黎街头数百年巨石雕筑的街巷;它享受大都会的乐趣,在玻璃打造的拱廊街下,人们的眼睛应接不暇,充满热切的评论与攀比;在夜幕降临后的私宅宴会厅中,出版商、记者、钢厂老板、法律学生、高贵和不高贵的女人开彻夜聚会,欢声笑语,打情骂俏。再没有哪里比巴黎更容易见到时代的交错,古代信仰与现代享乐的共存,钢筋玻璃与巨石堡垒的对立,高耸铁塔与沉厚教堂的交锋,各自骄傲,各自保留一片天地,在同一座城市,各自达到美的极致。
大工业的世界终于到来了。人们成为机器的宠物。人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在城市的世界里漂浮,如同一根羽毛随风波动,染上尘埃再坠落深谷。
这是属于轻浮者的世纪。轻浮者在城市闲逛,在琳琅满目中兴致勃勃。波德莱尔是巴黎最伟大的诗人。他敏锐地发现这些城市的闲逛者:一个全新而充满好奇的城市阶层。他同样发现那些困顿的人,被城市挤出的边缘人们。他为这些人著诗立传,写下时代转折的声音。“两手托着下巴,从我的顶楼上,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这样的观察中,他看到其中的繁华:“楼梯拱廊的巴别塔,成了一座无尽的宫殿,静池飞湍纷纷跌下,粗糙或磨光的金盘。”他也看到其中的破败,“是啊,这些人饱尝生活的烦恼,被劳作碾成齑粉,为年纪所扰,巨大的巴黎胡乱吐出的渣滓,被压得啊弯腰驼背,精疲力竭。”他从不美化任何人,那些穷苦残缺的人们各有其丑陋的面孔,而那繁华万象的景色不过也是黄粱一梦。他冷眼旁观,用韵律的刀锋写作,在纸上刻下诡谲的《恶之花》,巴黎在刀痕中获得了永恒的面容。
“作为私人的公民走上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哲学家本雅明这样形容波德莱尔的巴黎,“在波德莱尔笔下,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这种诗歌不是家园赞歌,当这位寓言家的目光落到这座城市时,这是一种疏离者的目光。”
这个时代的人们将自己托付给金钱。这种习惯如此强大,甚至超越时间,流传给我们。没有中世纪信仰的狂热,也没有骑士简单的忠诚,人们开始理智而计算,并相信这是真理。19世纪的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这历史的变革。巴尔扎克写梅莫特与魔鬼交换灵魂,写葛朗台老头临死时用眼睛盯着黄金,福楼拜写债券经纪人骗光包法利夫人的所有钱财。这是艺术家对时代的回应。当一个时代到来,艺术家有能力冷笑它的繁华,撕下它的虚荣,写下它的矫饰与愚蠢、奢华与破败。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沙龙的涌动和沸腾】
巴黎是一座充满诱惑的城市。波兰政论家弗兰科夫斯基在描述巴黎的时候认为,巴黎是一个以超乎寻常的创造性机能发展的城市:“巴黎在飞奔,巴黎在涌动,巴黎在沸腾。”
沸腾的城市中,独特风景是艺术家。躁动的灵魂充满表达的欲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城市里充满流浪艺术家,每一个流浪者都梦想着将自己表达给世界。他们在大声喊,用喊声穿透历史。如果说18世纪属于革命,20世纪属于战争,那么19世纪就属于艺术。19世纪既有革命又有战争,然而革命和战争都不是主导。19世纪的战斗是局部的和细节的,19世纪的艺术却是宏大的和全景的。这一个世纪,艺术超越战争。
19世纪的巴黎是艺术家的中心。它有一样独特的事物,改变了艺术史,也改变了政治,那就是沙龙。沙龙是这个时代发展出来的特殊的产物,它源自宫廷贵族的宴会厅,到了这个世纪,演变为普通身份艺术家的聚会。在沙龙中,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学者聚在一起,秉性相投,火花碰撞。私人的沙龙属于圈子和知己好友,常常在富有、好客的主人家里,伴随宴会、辩论和作品朗读。学院沙龙在美术馆,发布艺术家的新作,邀评论家参观,这是新人想要出类拔萃的必经之路。沙龙是催生作品的地方。在沙龙中,有僵化有偏见有权力斗争,也有创见有思想有慧眼识珠。竞争多于僵化,碰撞迸发出焰火。
波德莱尔曾经记述过德拉克洛瓦的沙龙,此时的诗人还年轻,大画家已经是名满天下。诗人是画家工作室中的一位新客。他敬仰德拉克洛瓦,喜欢他的风格和他的色彩。波德莱尔充满感情地记录下沙龙里的一切:“‘我们’不只是意味着写这几行字的谦卑的作者,也意味着其他几个人,年轻或年纪大的,记者、诗人、音乐家,他在他们身旁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随随便便。”德拉克洛瓦是19世纪法国绘画的另类,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诗歌的另类,沙龙让这样不同的艺术家结合在一起,获得生命力。从德拉克洛瓦的色彩中,波德莱尔领悟到激情的浓郁与深邃。他的诗歌也有着相似的浓郁与深邃。
德拉克洛瓦是法国绘画中的英雄,也是最杰出的开创者。他以反学院的姿态走进沙龙,最终获得学院的认可。19世纪的法国经历着美术的黄金时期,从大卫到格罗,从安格尔到库尔贝,从杰里科到德拉克洛瓦,一连串名字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起来,各自推到一个顶点,法国美术从来没有哪一个世纪像19世纪这样蓬勃旺盛。
从罗浮宫的法国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