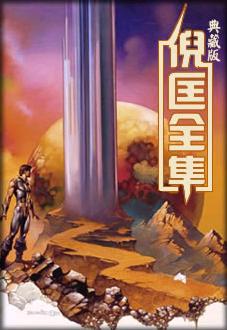非常水浒-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少把我跟卖烧饼的往一起扯!”大郎假装生气地说,“我现在的身份是职业打假人!”
“还职业打假人呢!”翠花鄙夷地说,“小心哪天把你给打残废了!”
“残废了我也要打!”大郎斩钉截铁地说,“我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要识骗、防骗、拒骗、打骗!我要成为职业打假人!我要成为维权高手!我要成为打骗专家!”
“既然这么聪明,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掐算出你身上的钱和中午吃的饭?”翠花嬉笑着问。
“不知道,”大郎实话实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都不知道,还说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呢?还要识骗、防骗、拒骗、打骗呢?”翠花嘲弄道,“要不要我告诉你秘密?”
“快说!”大郎饶有兴趣。
“那你给我20块咨询费!”翠花嬉笑道。
“给就给!”大郎说着麻利地从身上掏出100元递给了翠花,“80块洗脚,20块咨询费,刚好不用找了!”
“其实呀,你今天中午吃饭时我就坐在你旁边的桌子上!”翠花高兴地说,“就连你跟王婆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婚拖同志!”
大郎倒吸一口冷气。
他站起身,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翠花,悻悻地出门了。
出了发廊,大郎又颠三倒四地逛起街来;逛着逛着,逛到街心花园时他又想喝酒了;喝着喝着,他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商场,开始晕晕乎乎地逛起了商场……逛了多久,逛了什么地方,他都记不清了。只是当他稍微清醒的时候,忽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焕然一新:衣服是新的!裤子是新的!皮鞋也是新的!他大吃一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买的衣服?又是在哪换的衣服?他伸手一摸裤裆,天哪!内裤也是新的!他倒吸一口冷气,酒也醒了大半!他摸了摸口袋,谢天谢地,钱包还在;打开一看,却傻了眼,里面只剩两百多块钱了!大郎急忙蹲在马路边拣了根树枝,开始凭着记忆算起帐来,算来算去,始终凑不到2000块钱!算得头晕脑账的大郎慢腾腾地站起身,缓缓地抬起头,静静地看了看这个夏日酷热的午后,又看了看自己一身的新衣新裤新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了出来。这一刻,千种滋味,万般感慨,忽然都不可压抑地涌上心头,他的心里开始翻江倒海起来。他感觉不出是喜还是悲?他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着什么?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的心中开始疯长起一些乱七八糟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大街上,骄阳依旧似火,热浪依旧滚滚。
街道旁,商铺依旧林立,行人依旧稀少。
走在马路上,依旧像走在熔化的铅上面一样,感觉滚烫和灼热。
大郎又想喝酒了。
他依旧买了两瓶酒,一瓶是冰镇啤酒,另外一瓶也是冰镇啤酒;他依旧像个老猴子一样蹲在马路边茂密的梧桐树荫下的石台上,一边百无聊赖地抽烟喝酒一边胡乱地想着心思。此刻,有两个叫花子正翘着二郎腿躺在旁边的另外一个石台上唾沫星子乱飞地聊着天:他们时而从雀巢奶粉里的碘超标问题扯到肯得基的“下跪”广告;时而从圆明园湖底铺防渗膜扯到三陪女的“人造处女膜”;时而从伊拉克战争扯到靖国神社……他俩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俩东扯西扯胡乱扯无所不扯。
“如果我们现在能把拉登扭送给布什的话,我看肯定能得到不少的美圆哪!”一个脸上垢甲至少有两页青砖那么厚的叫花子不无憧憬胸地说。
“我看如果把布什扭送给拉登的话,肯定得到的赏钱会更多!”另外一个长头发锈得比烂粘帽还烂粘帽的,看样子像个艺术家的老叫花子胸有成竹地说。
“花几十元就可以偷偷摸摸地‘再造’处女,你说这是挑战医学还是拷问道德?”“垢甲王”一脸疑惑地问“艺术家”,“还有花几千万在圆明园湖底偷偷摸摸地铺防渗膜,你说这是保护世遗还是腐败问题?”
“人造肉能跟那真肉比呀?偷偷摸摸做的事它能光明了吗?”“艺术家”一脸不屑地说。
“你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事件是9·11还是伊拉克战争?”“垢甲王”纳闷地问。
“一个死了几千人,一个死了十几万并且还在死,你说哪个是最恐怖的事?”“艺术家”一脸鄙夷地反问道。
“如果徐霞客生在现代的话,估计能活活气死!”
“如果10万元能再造神童的话,估计猪都能上树了!”
……
他们怎么那么无聊?和我一样的无聊!大郎摇了摇酒瓶里那些泡沫丰富的液体在问自己,一遍一遍地问自己,那个绿色的可以卖五毛钱的玻璃容器里就是摇不出他想要的答案。
大郎感到了心烦意乱。
心烦意乱的他唉声叹气地站起身,穿上那压在屁股下新买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的保健按摩拖鞋,拿起空空的可以卖五毛钱的玻璃容器,朝马路那边潇洒地挥了挥手,他很想听听某种东西破碎的声音,甚至,他想看到某种带着警报的东西“哇呜哇呜”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将他带到一个有着铁门铁窗铁锁链的地方,然后他就开始唱那个什么铁窗泪!大郎感觉自己真的有点乱了,或者说真的有点神经了。
那个空空的玻璃制品在热浪滚滚的空中划了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后轻轻落下。
清脆的碎裂声清脆地传来。
碎裂声中,警察没来。
大郎感到了沮丧。
他需要看到某种东西的破碎和某些人的到来!
大郎颠三倒四地回到了家。
家门紧锁。
打开门,冰锅凉灶。
再一摸桌子,上面落了一拃多厚的灰。
潘金莲同志呢?大郎嘀咕着在家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潘金莲同志的半点踪影。
大郎走到隔壁王婆家想打听打听,王婆不在,老婆也不在。
大郎来到巷子口的小卖铺前打听起来。
“你找不到老婆,问我干啥?”小卖铺老板打趣道,“你该不是怀疑我吧?”
大郎没有吭声。
他又上街开始寻找起来。
这时,他忽然看见郓哥迎面走来。
“喂!卖梨的!”大郎大声喊叫道,“你小子现在怎么不卖梨了?”
“哈哈,都什么年头了,谁还卖梨呀?”郓哥哈哈大笑,“我早就开网吧了!”
“哈哈,不倒腾梨了,倒倒腾起王八来了!”大郎嘿嘿一笑,“这扯蛋(淡)的生意怎么样啊?”
“什么扯淡?什么王八?”郓哥鄙夷地说,“是网吧!是高科技!”
“嘁!你当我还真不知道呀?”大郎同样一脸的鄙夷,“我研究网络骗术都已经研究了好几天了!”
“你不上网怎么会知道呢?”郓哥疑惑地问。
“研究老鼠药的难道还非得去亲自尝尝老鼠药吗?”大郎反问道。
“都已经搞起研究了,那你不打算再卖烧饼了?”郓哥漫不经心地问。
“你都搞起网吧了,我还能原地踏步走吗?”大郎催促道,“快走,看看你的王八(网吧)去!”
郓哥带着大郎朝背街走去。
“你那网吧叫什么名?”大郎边走边问。
“我那叫‘一坨屎’网吧,”郓哥认真地说,“之所以叫‘一坨屎’网吧,就是因为它地处偏僻,网吧里没有厕所,外面又没挂招牌,门口经常会被上夜机的网友屙上一坨屎而得此名。”
“这名字倒挺个性的嘛!”大郎嬉笑道,“人气怎么样?”
“还可以吧,”郓哥嬉笑着说,“在网吧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间都有人,无论是清晨,中午,黄昏,还是深夜;什么事都会发生,有些人玩着玩着都能睡着,有些人睡着了嘴里还叨叨着,有些人即使挺不住了也会像创作中的马克思一样用疲惫无神的双眼仔细地注视着屏幕,有些人比铁人还铁人,电脑需要休息了他们还不想休息,史瓦辛格死了他们都死不了,马克思挺不住了他们都挺得住,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觉得饿了他们都不觉得饿,沙漠里的非洲土著渴了他们也不会渴……他们都是神的化身,是精神力量的体现!”
“一坨屎”网吧很快就到了。
网吧里乌烟瘴气。
浑浊的空气里在弥漫着烟味酒味和脚臭味的同时,也弥漫着变味的香水味以及许许多多来路不明的气味。这里果真是一个好地方,很适合上网,也很适合打游戏,当然更适合浏览黄色网页了。一进网吧的门,大郎就惊讶地发现他的老婆潘金莲正姿态优雅地坐在最里边的那台机子前,一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屏幕,一边用她那涂着粉红色指甲油的纤纤玉手飞快地敲打着键盘,敲得键盘“噼里啪啦”地响。
大郎悄悄地走了过去。
他悄悄地站在金莲的身后。
潘金莲聊得很是投入,就连她的袖珍老公站在她的身后居然都没察觉出来。她依旧一边把泡泡糖吹得“吧嗒吧嗒”地响,一边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地响:
……
西门大官人:俺好几天馍(没)见你了!
阿莲: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西门大官人:最近,俺想你都想得水(睡)不着脚(觉)了!
阿莲:相思一夜情多少,天涯地角思量遍。
西门大官人:最近日子过得咋样?
阿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西门大官人:我也在瓮(梦)里头见过泥(你)!
阿莲: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西门大官人:今天我上网碗(晚)了点,馍(没)想到你也碗(晚)来了。
阿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西门大官人:平常这个时间你在忙啥?
阿莲: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西门大官人;这么谗(惨)?
阿莲: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
西门大官人:那三寸丁呢?
阿莲:行同虚设。阿炳的眼睛。贝多芬的耳朵。
西门大官人:你啥时有空?咱俩好好见面了了(聊聊)!
阿莲: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挪残蕊,更拈馀香,更得些时。
西门大官人:我得瞎(下)了,回去还得给人看病呢!你呢?
阿莲: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
西门大官人:不忍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