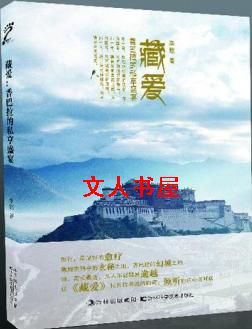藏爱:香巴拉的私享盛宴-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俗话说,酒醉话多。老板喝着喝着,对我们说起了一段往事。
还是少年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位门巴族的女孩。女孩的声音像银雀,摇摆的腰肢如细柳扶风,见到她的第一眼,他就被深深吸引。从那天起,她所驻足的每一处,都可以看见角落里他关注的目光。
等到他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与她交谈,却得知,她早已与姑家的儿子有了婚约。
门巴族的婚姻是自由的,有歌唱道“东北的山再高,遮不住天上的太阳,父母的权再大,挡不住儿选伴侣”。尽管这自由的婚姻不受父母约束,不受贫富等级影响,却有着不成文的规矩,认为舅舅的女儿被别人娶走,就是姑家的儿子无能。因此,姑舅家早已结为秦晋之好。
姑娘没有接受他的爱情,但他却留在了此地,不愿目光离她而去。
老板说的往事,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泸沽湖遇见的摩梭族导游。他说,摩梭族是母系氏族,谁看上了某家的姑娘,就得约好一个晚上去爬她家的墙头,晚上摸着进去,早上偷着出来,姑娘未婚怀孕,不是稀奇事儿。
这在外人看来有些混乱的感情关系,摩梭人自己却非常有规矩,一旦认定了对象,就会上门提亲,也不会再去爬其他姑娘的墙头了。
如今听到,门巴族亦如是。舅舅是女儿家最有权威的人,一旦女儿出嫁,新郎家是要把舅舅招待得周周到到,让他非常满意。婚礼中,哪怕准备再完美,舅舅依然会挑事,指责这里那里没做好,表达的是不舍女儿离家,希望她在婆家受到重视。
然而,当夫妻不和,要离婚的时候,就由不得舅舅了。只要村里的头人调解不成功,就可以离婚,财产物归原主。若一方不同意离,则由另一方支付大牲畜和钱财,并且提出离婚的一方得不到子女。寡妇再嫁,亦是自己说了算。婚恋非常自由。
这样自由的婚恋,却有着隆重而独特的婚礼仪式。
听说,婚期一旦确定下来,新郎家就开始做各种准备,到了吉日,则早早派出口若悬河的媒人和伴郎、伴娘以及男方的两名亲戚。他们到女方家向新娘父母和亲人献哈达、敬酒、祝福,要接新娘早走。
接走盛装的新娘之后,往新郎家走的路上有“三道酒”。能说会道的敬酒人分别在新娘家的村口、半道之中、新郎家的村边等候着。
到了新郎家,新娘喝完洗尘酒,就要换下所有衣物首饰,从内到外换上婆家准备的东西。据说,这一仪式象征着母权向父权过渡的历史。
婚礼期间,将不断出现闹剧,参加婚礼的客人通常是自带酒食,到饮罢唱罢的第三天,娘家人要回去了,除了告别,新娘的母亲在开导了女儿之后,通常会呵斥女婿。待他们都走了,留下新娘哭泣时,她的母亲会忽然带着亲人一起将新娘拉走,让她一起回家。直到媒人调解,婆家人应承会待媳妇如亲闺女,突如其来的婚变才落下帷幕。
婚恋的话题对于老板来说,显得过于残忍。他的酒量倒是海量,接近两斤酒下肚,人还清醒,不过是话多了点儿。
想来也是,多少年独守空房,过往的旅客也许是最好的听众,说罢,人走,也就什么都不曾改变地继续生活着。
蓝小心翼翼地向老板打听门巴人放毒是不是真的。我和陶伟都不吭声,想起老板单恋的门巴族少女,多少是有些心疼的。老板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放毒的人家是可以辨认的,他们的门前会挂大黑蜘蛛,传女不传男。而其他的人家,会在门口挂上成串的鸡蛋壳,这样人家就是安全的。但是,你们最好不要去不熟悉的门巴人家里吃饭和喝酒,她们有时把毒藏在长指甲里,一碰就落了进去。”
据说,毒分为热毒和凉毒,热毒即刻死亡,凉毒则使人慢慢枯萎而亡。因为墨脱身处热带,在原始森林中有很多的毒果和毒树,将之晒干磨成粉就是毒。
老板说起话来,有种让人安全的感觉,一字字一句句都非常沉稳。真的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个人,居然可以为爱留守如此多年。他告诉我们,这里气候炎热,所以有时候是食物坏了,吃的人死去,正巧死前在某人家里喝了酒或吃了饭,于是那家人被认为是放毒人家。这样的人家会被村庄驱赶,甚至被牛皮裹住,扔进河流。
原始的生态总是残忍的,这些冤死的人,不知还会否惦记着墨脱这片神秘的土地?
夜晚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点打在矮小的竹楼,打在屋顶的铁皮上,叮叮当当,像一首催眠的夜曲。
蓝走到我的床边,小声问道:“今晚,我可以跟你睡一张床吗?”
我点点头,她躺在我的身边,挽着我的手臂,整个人蜷成一团。
再见,背崩
蓝问我:“修,为什么都市一夜情泛滥的时候,这里可以有那么多为爱留守的感人故事?”
也许,是因为这里潮湿的气息,各种奇异的花草树木,还有门巴族和珞巴族奇特的生活方式和坚守的土地。
就像我们听到的那样,为爱而留在此地的都市人应该是受到这气息的感染,比如那个留在背崩的汉族男子。
背崩是墨脱地区最大的乡,乡里唯一的一座都市建筑,是一所传来琅琅读书声的希望小学。
那个有着亚热带风情和感人故事的地方,催眠着我们的疲惫,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往那个毗邻印度的地域。
从县城往背崩方向的人较少,大多都是从拉萨方向过来。天蒙蒙亮,徒步的人们就都出发了。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三五结伴的人,因此不觉孤单。
泥土之上落英缤纷。潮湿的土地如温暖的怀抱,朵朵粉色的野花,似袖扣,也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们没有听旅馆老板的意见,不怕死地驾车前往。因为雨季已经过了,大家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路上不会遇见大塌方。
尽管雨季已过,路上的泥土却总是潮湿的,车轮一过,留下深深两道痕迹。就像人们常说的,每一个戒痕都有着专属于它的故事,每一道车轮也都记录着旅人的故事。
路途之上,车子摇晃在土路上,沙石滚落的声音一路伴随着。
起初一直在翻山坡,有人说这叫绝望坡,因为来来回回兜兜转转,却看不到尽头。靠山的一侧不时有细小的沙石流下,茂盛的植物像挤不下似的,各种角度兀自生长着。另一侧则是万丈悬崖,没有任何的防护设施,就是松散的泥沙,以及一簇簇的灌木。
山峦之间,有着缥缈的云雾,似神仙居住的处所。这段路途上,不乏独特的藤桥。因为珞巴人喜住崇山峻岭,交通通常是由白藤编制的索桥。据说,不要一板一钉,只用原始森林里的藤本植物那细长的茎蔓,就做成了柔韧的藤桥。过这种桥是有技巧的,你的步伐要跟随着藤桥起伏的节奏,才可以安安稳稳走过。否则,就会不停摇摆,越害怕越容易被捉弄。
海拔已经越来越低,空气中潮湿的水分子贪婪地亲吻着皮肤。亚热带的丛林里,植物交错生长,有着特别的层次感,凌乱却不显拥堵。片片青苔说着古老的故事,清澈的泉水则滋润着当地的生灵。
一路上的植被,总给我以远古的孤独感,无论是曲折向天的参天大树,还是垂下细腰的小木,都像是山林的守护者,又似来自另一个空间的主宰者。
拐过一道弯之后,可以看见两座山之间波涛滚滚的雅鲁藏布江了。对面山上就是德兴村,架在浑浊的江水之上的是德兴藤桥。细细一道白色的线,连接了两岸青山,穿流而过的江水似也失了霸气。
继续往前,依旧是无数的小塌方,原本窄小的路面被沙石堆去一半,更加坎坷。一路上,不时有经幡出现在眼前,有时是在路边,有时是在桥上。
最爱是那随处可见的芭蕉树,硕大的叶子,只是看看,就让人心生凉意。因为此时,气温已经很高。
小道上,有抬着大竹竿的门巴人,也有背着小背篓的门巴妇女。
在周边的山头,依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刀耕火种是新石器时代残留的耕种方式,伐树或将地上的草晒干,用火焚烧成灰做肥料,然后就地挖坑播种。火烧过的土地变得松软,加上草木灰的肥料,一年就不再施肥。这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土地一年一换,生产力非常低下,农作物的产量很低,俗称“种一偏坡,收一箩箩”。
沿途可见门巴人焚烧的山地,单单那一块光秃秃露着,像个癞子头。他们在灰烬中埋下种子,驱赶野生动物,便守株待兔似的等着庄稼自然生长成熟。几年后,当土地变得贫瘠,便被放弃,原本的人家又搬迁到一处山林边,再烧出一片地来,重复以往的刀耕火种。据说,非洲有很多这样的农业方式。
门巴人每天起早贪黑,在农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着农活,用一些简易的工具维持着全家人的生存。在这山岭之中,他们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高楼大厦,也不知道人类已经可以登上月球,只是简单重复着每天的劳作,觉得这就是人生。
雅鲁藏布江与多雄拉河交汇处,让我想起了15岁随母亲的旅行,从大连到上海的邮轮上,清清楚楚可以看见渤海与黄海交界的线,一边是浑浊的渤海,一边是碧蓝的黄海,而此时,绿树这边是清澈的多雄拉河,而彼岸则是混沌的雅鲁藏布江水。
融汇到一起的河水朝着下游奔流,而我们也终于看到了解放桥。这意味着前面就是终点,就是最美丽的背崩乡!
大桥是不允许拍照的。边防证交由部队检查后,我们沿土路缓缓爬行两里路,就到了背崩乡。
这盈盈绿色铺满了目光所及之处,淡淡的雾气飘浮在半空,不知道是炊烟还是云朵。之间,点缀着一些红色的,是房屋,也是泥塘。
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加措。
住进村头门巴人开的旅馆,迎头就撞上了一个懵懂的小伙子,他匆匆道歉离开,却又在看到陶伟的越野车时驻足停留,只见他抚摸着脏兮兮的车身,然后抬起头问:“这是你们的?”
那双眼睛,纯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