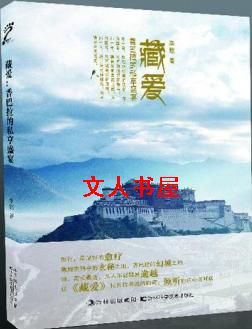藏爱:香巴拉的私享盛宴-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旅途中偶遇的人们再相见,都像亲人一般。我们惊喜地拥抱了彼此,笑嘻嘻问着对方的行程和经历。
他们一直待在郎木寺,直到这天早晨才向红原方向出发。阿力说:“旅途不该是走马观花地路过,而是居住。吃当地人的食物,听当地人的歌曲,学当地人的语言。”
我和管元面面相觑,没想到浪子般的阿力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不然也想要流浪在大江南北风情各异的地方。
我记得,几年前,曾与齐蓝策划了一条走遍中国且不回头的路线,好漫长的一路,我们却一直没有启程。各自有各自的牵绊,各自有各自的无奈。
阿力说,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走完四川,就要回去过都市生活,毕竟父母年岁已老,再丢下他们,心里总是不太放心。不管有再多的误会和不理解,那也毕竟是生养自己的双亲。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他们更加重要。
不知道在郎木寺经历了什么,阿力与我们初见的时候不同,似乎更加成熟,也不那么惹人讨厌了。旅途总是可以让人改变许多。
我们呢,这几天去了花湖,在蓝天白云下发了一阵呆,凭吊了一番初恋;在若尔盖午餐,结识了贡布一家;去唐克两次,却没有看成落日;跑到红原,竟傻乎乎闯到扎营的部队门口,被人驱赶;倒转回瓦切塔林,路途中偶遇了超美丽的双层彩虹。
阿力和晋亦听了,大笑个不停,说我们简直是在演一场滑稽的剧目。
滑稽吗?人生不就是由这样那样的偶然组成吗?
我们说着说着,又沉默了下去,各自看着连绵的经幡,想着不同的心事。
云层逐渐升高,雨停了,太阳却没有出来。我们穿行在白塔之间,抚摸着触手可及的经幡。不知这美丽的经文,日日飘荡,是在为谁祈福?
一圈下来,没有更多的语言,我们都各自上路。这次,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日后,兴许都不会再见了吧!
一直以来,都不习惯在路途中留下联系方式。相遇的人们是缘分,离开的时候,就该回到属于各自的生活中,不带来什么,也不带走什么。
再上路,我们就是归程了。回到兰州,就要告别甘南的一切。
管元继续她的生活,我则前往敦煌,预计到川藏线走一圈,再回去江南的小城。
直到上了敦煌的火车,我还在想念穿大红僧袍的喇嘛、草原上忽{文!}隐忽现的旱獭、天空中翱{人!}翔的雄鹰、亲和的藏民和{书!}美丽的格桑花。我依旧惦念着在{屋!}拉卜楞寺遇见的诗颜,不知她过得好不好,心里的空洞什么时候才能填补好?我依旧惦念着郎木寺遇见的阿力和晋亦,不知去过四川之后,再回到都市,阿力是否就能乐观地直面生活?我惦念着若尔盖的贡布一家,不知草原的鼠患会不会影响到他家人的生活?我惦念着亲爱的管元,还有她的朋友夜雨和菜菜,一别之后,不知多少年后才有再见的机会,希望她能够快乐地生活。
郎木寺的安宁,尕海的云淡风轻,花湖的羞涩,唐克的悠远,塔林的经幡……我想,无论多少年过去,只要回想起彼时的风景,感触都会如在昨天。
乐章七 向西,是另一种抵达
她是那样一个见微知著的女子,身处群众之间,却不苟言笑。
在宛若秋阳的昏黄光线下,她说,不安宁的月份,注定了一生奔命。
传说中,星座流失象征着大变动,无人能预料其祸福。比如,她在家破人亡的七月出生,这就是宿命。
行走在历史之上
因为在甘南圣地留下了一滴泪,我的内心始终保持着盘马弯弓的姿势,等待再度启程。来自香巴拉的呼唤,渐渐渗入我的每一次呼吸,触碰着我心底的期望。
仅仅一个月之隔,当我再度踏上征程,心情却是平和安稳的。
生命,不过是一次起承转合的过程。
机窗外雾霭浓浓。我想起七年前,第一次来到成都时,那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成都于我而言,就像是前世的故乡,只为填补今生的空洞苍白。
在那时,我将成都比喻为一名缘起千年前的女子,引领我前来。
飞机抵达“天府之国”时已是傍晚,灰蒙蒙的世界,与想象判若云泥。心绪猛然澎湃,似已抵达那个女子的温柔。我终于靠近,在灰蒙蒙的掩饰背后,旋转着已逝的命运年轮。而她在何处?我已靠近,她甚至可能就躲藏在我身后,但我依然看不见她。
这是已等待千百个轮回的约会。我要亲自走到她面前,告诉她,这就是宿命。于千百年前的一次回眸,终将指引我来到这儿,靠近她的身边。这正是一种莫须有的依存。
这片土地,散发着故乡的味道。是植物的辛辣清香,以及成都特有的味道。暮色是一袭遮羞的布帘,在夜色之中,像与前世的我有了一个真实的拥抱。
空气里,熟悉的气息随处可以闻见。
那时刻,我想要以五体投地的姿态爱抚足下土地,犹似触碰那隔世的爱。
而七年之后,我再度踏足,却不是为了此地,而是对香巴拉藏地那片净土的眷恋。
有人把漂泊当做梦想,另一些,则渴望着能在路上遭遇些什么。
行走,对于大部分青年是种诱惑。初出茅庐的青年,怀着满腔凌云的壮志,渴望翱翔。如果能感受飞的快意,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抚摸着白云,与鸟儿对歌,亲吻蓝天,多美,多惬意!
年轻的心无所惧怕,横冲直撞于世界的每一角落,最终,当那颗曾经热泪盈眶的心能够原谅世间所有不公,才猛然发现,每一次迈步,都是向苍老靠近。
小雅从雅安赶来与我见面。她是我认识十年的朋友,却从未谋面。我们在同一个论坛写字,喜欢上同一个男人,然后同样地被抛弃。
不同的是,小雅从未离开过四川,而我从十八岁起,几乎没有在家乡待过完整的一年。
我们找了家有落地窗的茶楼,轻轻说起过往以及现状。
我说,生命中擦肩而过的男人,在多年之后谈起,都显得云淡风轻。正由于当时的不成熟,反倒因单纯而显得美丽。
小雅却说,成熟又是什么呢?不过是被习俗磨去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当年或许还有着真实的自我,而现在,不过是精神的夭亡。
她说:“我永远都只是自己认为的样子,因为孤寂,才看到生活本身的模样,而日常中,却总在扮演着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
小雅是雨城养育的女子,性格之中,多了份细腻与忧伤。
说起雅安,大家都知道它素有“雅雨、雅鱼、雅女”三绝的美誉,殊不知,在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接壤的地方,在这亚热带季风的影响下,雅安人比别处的居民更懂得包容的意义,也因此更懂得淡然处世。
比如在外人看来孤苦无依的小雅,却坚强地撑起生活重担。她家早年遭遇变故,家破人亡,却并未丧失生活的勇气。在她看来,你认为自己没有的东西,或许正在前方等待着你,而你羡慕别人的时候,或许别人也正在羡慕着你。
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都不过是生活罢了。
这次的行程,没有预计在雅安停留。我与小雅谈论她的家乡,她淡淡微笑着说,最爱的是家乡的红豆相思谷。每当遇到坎坷,或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她都会驱车前往那片幽静的山麓。
在那里,有着南方特有的美好风景。当你面对千佛岩双手合十,内心也会随之安宁。而当你抬头仰望树龄千年的红豆树,会感到人生如此渺小,没有什么值得你停下脚步。
在雅安,这棵红豆树被当地民众称为“仙树”,据说能测祸福、卜吉凶。而小雅去往那里,只为遗忘过去,以支撑起前路。
然而,不可遗忘的,是属于雅安的历史。
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就是雅安附近的夹金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当年的夹金山没有人烟,空气稀薄,而今日,作为川西的咽喉之地,民族的走廊,那些荆棘丛生的小道已被宽敞的公路所取代。
纵然如此,这座终年白雪皑皑的大山,依旧提醒着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
在19岁那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向西,是另一种抵达》:她深爱暮色的天空,那幻化的透明的蓝已经折出朦胧的灰色欲望。没有他守在身旁,她没有守护在他的身旁。亘古的更声在敲击着回荡,女人独处山中,等。守候的,是一份无限期的契约。
她为自己砌好一座华丽的墓碑,旁边是紫色飘带捆扎的淡蓝鸢尾。她用一缕绵长的思念点燃指间香烟,手中的细线怡然松弛,微风带走了那只古老的筝,白鸽亦展翅扑闪着开始了流浪的旅程。
那时候,是为了一份懵懂的爱情,而如今,不是为了守候,是为了追寻心底那片精神的乐土,那片纯净而伟大的圣地。
告别小雅之后,我沿着茶马古道一路向西。
记得,第一次接触茶马古道,是在云南的拉市海。
导游告诉我们,这要追溯到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和亲。当年,他们从长安一路向西,翻过日月山,走近青海湖,却在这时,随行的汉人头昏脑涨、四肢乏力,医生也找不出原因,此时,文成公主吩咐随从取出蒙山茶,用倒淌河里的水煮开,拌上藏族奶酪,让随行们喝下。片刻之后,随行便精神抖擞。茶进入藏区,便由此开始。
一千多年来,茶马古道从来没有断过背夫马帮。茶成为了藏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也有了“汉家饭饱肚,藏家茶饱肚”的说法。
走在这条经历千年的道路上,不由得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动。
坐在开往新都桥的大巴上,一路经过了天全、泸定和康定。
远在新石器时代,天全县就已是人类的聚居之处,古氐羌民族在此安居,称此地为徙都。在这里,经历了我西行的第一险——二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