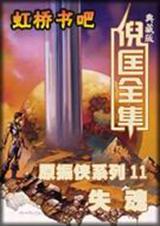11-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前,有一个少年,他从小就喜欢剑。
他那做镖头的老爹在他五岁那年为他削了一把木头小剑,他从此便像得着了宝,连睡觉都要揽在怀里,别的东西他都愿意跟玩伴们分享,独独这小木剑,谁要他也不肯给。
直到有一天,他拿这把小木剑戳伤了别家孩子的额角,他爹爹一怒之下,把那木剑折成两段丢进了炉灶——他心里伤心得要命,却忍着一句话也不说,一滴泪也不掉,只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它在跳跃的火焰中慢慢变得焦黑。
后来他偷偷地把那柄木剑从灰烬里扒了出来,埋在了河滩上。
当时他有点赌气地想,他再也不要玩这种东西了。
——虽然爹爹并不知道,那个前大街绸缎庄家的独生小少爷是多么骄纵野蛮,把隔壁瞎眼王阿婆的菜篮子打翻在地,还用泥巴丢她的后背……
他不想解释,小小的他已经似懂非懂地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解释是没有用的。
到很久很久以后,他都一直记得那把木剑带给他的快乐时光,也忘不了它在火焰中燃烧的悲鸣。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爹爹的指导下习武操练,使刀使枪使棍使锤……独独不肯学剑。
那把“剑”,是他未被折断的童年。
十岁那年,这个少年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把剑。
那算不上什么绝世神兵,但却是一把真正的剑。
少年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当那个浑身是血的汉子临死前把它交给他的时候,只来得及对他说最后一句话:
“小鬼,拿着它,它能保护你自己!”
是他把这个奄奄一息遍体鳞伤的汉子从后巷扶回自己家的后院柴房,端来了一碗清水,几个半热的馒头。
因为他就是相信,那是个侠士,不是个坏人——在肮脏凌乱的尘土血泥中,一个坏人,是绝不会有那样一双充满热意的、清得透亮的眼睛。
那汉子从头到尾没有对他说一个“谢”字,但却把自己腰间的剑解下来送给了他。
这一次,少年的爹爹没有责骂他,只是看了那把剑很久很久,然后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你就拿着它吧。”爹爹说,注视着他的眼神意味深长,里面有什么一瞬即逝。
少年把这把剑擦得很亮,小心地挂在了腰畔。
冰凉的剑身地贴上他的肌肤,又慢慢变得温热,似乎整把剑都热烈地流动了起来——有那么一瞬间,少年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几乎觉得,这种兵器已经开始长进了自己血肉里去。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过其他任何兵器。
多年以后,当别人用“侠义”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当年从那汉子手里接过那把剑时,自己手心的温度。
也许吧,从那把剑起,他一夜之间成长。
那把剑从此陪他年少得意,陪他鲜衣怒马,陪他意兴方豪,陪他遇到了卷哥,陪他离开京城,陪他来到了小雷门……一直到大半个江湖都开始热烈传说起,霹雳堂小雷门大总管响当当的名头,就叫做“九现神龙”。
少年侠士,如歌岁月,天大地大,纵马江湖——他开始爱上喝最烈的酒,开始觉得身边缺少一个最美的女人。
就像他开始需要一把最快的宝剑。
那一年,他横扫了关东第一大派,初识了江湖第一美人,换上了一把名为“青龙”的剑。
格斗中,他执这剑为她流过血,怒江边,他用这剑为她摘过花,佳人倾城笑靥,江湖儿女演尽情怀。
“青龙”吟处,神龙入海。
他的日子正值火焰一般的年少,他的江湖和他人生一样:风和、日丽、山高、水远。
——并因了那个女子,而更加热烈、芬芳。
他不知寂寞为何物,亦未尝过失败味道——没有什么是他不敢追求,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得到。
当他带着青龙剑脱出小雷门,投身连云寨的时候,他用其隔江割袍,凭它服众立威,执着它领兵抗辽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拿着它在篝火旁与弟兄们痛饮狂歌。
它见证了他生命中最快意方遒的一段辉煌。
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一把改变他人生的剑,即将出现。
他注意到那把剑有着一个听上去很悲凉很壮烈的名字,它叫做:逆水寒。
他因这把剑而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和这把剑一样的遗世而绝立,孤峭而清冷,也一样有着不能掩却的凌厉之芒,倨傲之锋。
遇到那个人的第一天,宝剑越匣而鸣,他认定,那是因为那个人的到来。
那个人,一表人才,气宇不凡。
那个人,惊才绝艳,智计无双,能运筹帷幄,可决胜千里。
那个人,他看到他的第一眼,心中就起了一阵莫名的震荡,那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交浅言深,一见如故。
这令他不得不相信,生命中总有些什么是不可阻挡。
那一夜,他为他舞剑,他为他抚琴,击节把酒,引为知音。
那一夜,他就做出了决定,要把连云寨大当家的交椅送给他。
那一夜,似乎比一瞬还短暂,又仿佛比一生都要漫长。
他剑一般飞扬的眉,剑一般明亮的眼,剑一般豪烈的笑纹,最后都变作漠漠黄沙如醉寥寥清风如诉里一段宿命的相逢,一场灭顶的知遇。
琴声与剑影相和的旗亭一夜,竟是永生难忘。
可身为连云寨的大当家的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是那把突如其来的剑,就是那个从天而降的人,把他全部的人生颠倒、翻覆、毁灭,连一点冰冷的余烬都不曾留下。
“这到底是把什么样的剑?”青衣书生终于忍不住转过脸来,“再后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白衣男子想要微笑,不知为何眼中却隐忍不住淡淡的苦涩,“这故事过于久远,连我也记不清了——”
他看起来好像有些疲倦,抱臂仰卧下来,直视向上方,似乎望进无涯的虚空,明亮的眼中荡开一层几不可察的黯灰。
故事仍然继续了下去:
再后来,九现神龙失去了他的兄弟和寨子,基业尽毁,历经艰劫,但好在,他一直没有放弃那把剑,也没有放弃希望。
流亡的岁月里,虽然有生死相随的女子和患难与共的兄弟,但他却常常觉得,自己剩下的,能够把握的,其实只有那把剑。
这个时候的他,终于感到了寂寞。
无数次的狭路相逢中,他用这把剑和那个人对峙,也亲眼看着仇人和兄弟的鲜血交相洒上那寒铁剑身,他心里知道,其实剑也是会痛的。
逆水寒剑。它是阴谋,也是热血,是毁灭,也是希望,是残酷的背叛,也是义无返顾的付出,是黑暗与卑劣,也是侠义和光明。
当他终于洗清了自己的冤屈,再一次见到那个人的时候,逆水寒架上那人的颈项,他却始终斫不下去。
只有他自己清楚,这终于放下的一剑,也许,不仅仅是宽容。
拿起与放下,何轻何重?
生与死,孰悲孰欢?
得势成龙的功业,生杀予夺的权柄,份量到底有多么沉重?
重不重得过侠义,重不重得过家国,重不重得过千万条无辜的性命,重不重得过深爱的女子眼中最后的泪水,又重不重得过知音相许的承诺和不离不弃的誓言?
他真的很想问问那个人,他最初想要的,是不是仅仅只是一把剑?
只是那一瞬间,迎向那双深不见底的漆黑绝望的眼眸,他反而像被狠狠刺了一剑,这道剑伤穿心而过,终生不能痊愈。
后来再后来,他做过名动天下的名捕,也当过领袖群龙的楼主,仍然是用剑,通体雪白的剑身,透明清澈得如同新雪,糅不进半生往事,吟不断半阕离歌。
他叫它做“痴”。
他用“痴”斫杀过无数敌人和对手,奠定过万人景仰的偌大基业,可它的颜色却日复一日地寂白下去,就和他的衣袍一样——无论再多胜利的激发,再大权柄的润色,再美女子的抚摸,都不能令它更加绝艳而夺目。
它只是更沉静、更寂寞。
谁说剑不会生病?
寂寞正是一种无药可治、渐入膏肓的恶疾。
他这才知道,他和他的剑,都病得很重了。
于是他带着他的剑,放下他的江湖,去找那个人,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可他就是认定那个人能治好这一场万劫不复的寂寞。
当他找到那个人的时候,他突然顿悟过来:自己这一生,恐怕从此再也不需要剑了。
可不是么。
剑可以杀,而不能度;可以灭爱,而不能斩愁;可以毁灭,而不能新生;可以涤荡江湖风雨,而不能挽留人面桃花春风如旧;可以驱除人间奸佞,而不能抚平积年累月刻骨铭心的伤。
其实有时候,有些习惯是可以改的。
比如喝惯酒的人一样可以变得喜欢喝茶,比如拿惯剑的手一样可以用来拿笔——端看你是为了什么。
九现神龙半生没有离开过他的剑,剑就是他的生命和江湖,但他穷尽这半生的时光,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比剑更重要的。
最重要的。
“说完了?”
“说完了。”
“你的故事越来越不好听了,”青衣书生轻哼了一声,恹恹地道,“今天这个又不如昨天那个,拜托明天能说个新鲜点的罢。”
白衣男子无声一笑,也不作答,只手拎起抖落的被子,把身侧的人盖了个严实,正欲起身,却听那边一句细不可闻的问话:
“喂,我以前……有没有用过剑?”
白衣男子怔了一下,烛火在他黑白分明的眸中晃了一晃,又归于平静。
“没有。”
他回答,眉宇间风轻云淡,满是五蕴深种的宁定与深情。
想了一想,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也很久没有拿过剑了。”
榻上的呼吸声越发清长悠远,青衣书生的最后一句话已带上了梦呓般的语调:“你……不是做过……江湖人么……连剑也丢了……就不怕……”
“怕什么。”白衣人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背影,半晌,终于忍不住伸长手臂将人揽入怀抱,对向他的耳朵,“我一样可以守护着你,就算没有剑……也一样。”
低低的话语伴着交缠的呼吸,散落于无声的夜里。
悲欢离合总无情,不如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故事终归是故事,有些片断,说不说出来又能怎么样呢,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的仍未到来。
该记得的,总不会忘记。
勾栏院的惨淡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