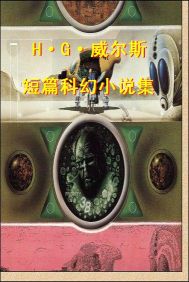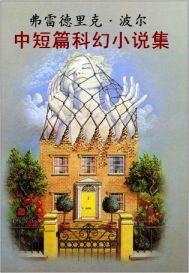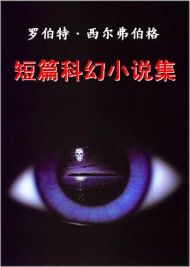短篇合集 by:该隐-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那一瞬间,我终於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圈套。
为什麽要弭平一向顺服於王朝的东夷?
是圈套,这一切都是圈套!
我乾呕著,吐出了男人硬要我吞下的黏腥。
我哭不出来。
因为我已经被撕碎了。
他直到要上早朝之时才放开了我,任由我像块破布似地摊在地上。
在男人离去之後,我脑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我要见你。
我一定要见你!!!
我披上了蜀锦的赤色外衣,抢了宫中马厩里脚程最快的一匹马。
我马不停蹄地硬闯出宫。
一路上有许多手忙脚乱的宫人想阻止我,直到那个最最冰冷的声音,丢下了一句诅咒。
「让他去吧!就让他去看那人最後的下场也好!」
我离开了。
春天已经渐渐远去,我们已经有多久没见了呢?
沿途我不眠不休地在驿站更换马匹前进,战火肆虐之後的景象,又岂是民不聊生所能形容?
我勉强问出了战场的所在,因为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发出阵阵恶臭,所以没有人敢接近那里。
几个大胆的男丁,说要趁著夏天瘟疫容易蔓延之前,把战场成堆的尸体全部烧掉。
我听不见。
我什麽都听不见。
我跌跌撞撞地踩入尸体堆之中,蛆虫爬了我满脚,扑鼻的恶臭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但我还是执意地往那位於正中间的朽白走去。
是你,我知道是你。
你很寂寞吧?
你很害怕吧?
我来了。
我来找你了。
远方拿著火把的男人不知道对著我喊了些什麽。
我听不见。
我什麽都听不见。
他们说我疯了。
说我被战场的冤魂附身了。
其实,我只是想见你而已。
你说…人头盖骨顶端就是白。
没错,真的很白啊!
满地的白,是不是就像夏天的雪呢?
你不是最喜欢雪的吗?
白色是雪。
赤色是大地。
赤色是太阳。
赤色是……大火。
燃烧一切的红莲之火。
我拾起掉落的面具,紧紧地抱著你,红色的血,红色的泪争先恐後地从我体内奔流而出。
「不活了,我再也不活了………」
「下辈子,我们不当人……就当土石、当草木,就是不当人,好不好?」
苍蓝的天,渐渐被血般的火焰所缠绕。
我闭上了眼睛,将你随身的匕首缓缓插入心窝。
不活了,我再也不活了。
苍龙王朝太宗永祺三年。
东夷灭,丞相赤云、将军白翼双双战死,遗体均不可获。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四十多年後,龙煌出生,许多的事情都还尚未开始。
《冬之旅》
在那个静的只听见下雪声音的破晓,在晨曦照在积雪上的那一瞬间。
我开始了我的旅行。
『我眼中的泪水,
滴在雪地上,
冰冷的雪花,
渴饮尽这炽热的痛苦。』
低声哼唱著舒伯特所谱写的Müller诗篇”冬之旅”。
我想在雪中,静静地在海里……沈没。
风像剃刀似地刮著我的脸,我却忍不住落下喜悦的眼泪。
因为,那让我想起……
你的吻。
你在哪里?
听著廉价音响中女人轻悠地唱著德国艺术歌曲。
每到高音时就会发出微微的沙沙声。
像是垂老的歌者。
哀悼。
你在哪里?
我将身体埋入雪中,想找寻你。
可是你不在。
明明……
与你的怀抱那麽相似啊!
我松开了越留越长的头发,编成了辫子。
故事中的王子,不就是沿著公主的头发爬上来的吗?
虽然我不是公主。
但,你会来吗?
你在哪里?
在这个冬天里。
只有痛苦是热的。
只有思念是炽热的。
或许…
还有你贯穿我身体的阳具。
你在哪里?
我曾说过我只等你一个冬天。
让思念有如长发纠缠住我的手指我的颈子。
但是,当春天到来,积雪消失时。
我就会融化对你的情思。
结束我们在你怀中的……
短暂旅行。
若是我们的爱情就只能存在於冰点之下,
那麽,我希望春天永远不要来。
你在哪里?
我高举著烛台,在黑暗的尖塔中游荡。
歌德式建筑的锐利屋顶,彷佛像要刺穿天空一般。
虽然外表华丽,但是内部却极为狭隘。
窄小而陡峭的阶梯,只能容我侧身而过。
我要爬到最高的塔顶。
要不然……
我看不见你。
宛如窗外的暴风,你在我体内肆虐著。
双手被束缚在雕饰繁复的床架之上。
那是象徵丰收的葡萄藤。
敞开的腿欲走还留地勾住你的腰,秘穴中翻出的鲜红内壁,淫荡地吞吐著你罪恶的分身。
侵犯我吧!
把你最肮脏、最丑恶的欲望都交给我吧!
你可以揪住我的头发,扇我好几个耳光,直到我嘴唇溢血。
我允许你。
侵犯我吧!
Ich liebe dich。
是禁句。
这是比伊甸之蛇还要恶毒的禁忌。
Küssen。
是面具。
这是比做爱还要虚假的面具。
那一天,疯狂的火焰燃烧著雪。
映著天际一片殷红。
融化的雪就只剩下一场污秽泥泞。
连一丝丝的白都不复存在。
魁武的男人们攻破了城堡坚固的大门。
我听不见男人的哀嚎与女人的哭叫。
我只是一个为了等待而生存的容器。
我被剥光衣服吊在城墙上。
城内的火尚未熄灭,光秃秃的墙上仍留有馀温。
粗糙的石面刮伤了我的背,我依然面无表情。
「他就是公爵所豢养的那个没有表情的脔童啊!」
耻笑著我身上的瘀伤鞭痕,我也不过是个任人泄欲的玩具而已。
支撑著全身体重的手腕,疼得像要断掉。
或许,它也真的断了。
男人用匕首在我身上描绘出血红色的弧线,最後,深深地终结在我的腹部。
「不知道当你的肠子被人挑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哭叫著求饶呢?」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肠子。
血淋淋的,跟猪肠没什麽两样。
男人把匕首留在我的身体里,就像是插著他自己的阳具一般兴奋。
他快意地赏玩著我痛苦扭曲的表情,没有人告诉他,其实我是哑的,就算他把我全身的肉都剜下来,我也哼出不一点声音。
直到,我头顶上方的绳索被人射下。
你回来了。
你在哪里?
你策马奔到我的身边,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举起手,你就毫不犹豫地扯住我的长发,将我拎上马背。
那有如雪般冰冷的怀抱,你坚硬的盔甲彷佛从未褪下。
走投无路地被追兵赶到悬崖边,你搂著我低声说著:
「我的军队就快到了,你再撑一下子!」
你灵活地操控著马不断变换方向,在远方隐隐传来马蹄声时,你也不得不勒紧马缰,急急停住。
一只劲弩袭来,你为了躲避而闪过了身子。
你的重心刹时倾斜,而我就这麽拖著你往崖边落下。
我只觉手腕一痛,便狠狠地正面撞上了峭壁。
你一手扣住了崖边,一手抓住了我。
崖上的兵马传来厮杀声,激烈的缠斗却无法影响你我。
那是一种诡异至极的平静。
你中了箭,撑不久的。
血,沿著你的肩膀滴到我的脸上。
我缓缓地拔出了匕首。
抬头对著你。
笑了。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我笑著斩断了我的手腕,坠入了我旅行的终点。
雪,已经融化了。
旅行,也该结束了。
十九世纪中,德国巴伐利亚公爵在自己的领地里因病过世,他终身未娶也无子嗣,享年56岁。
当仆人在为他殡殓时,赫然发现他生前从不离身的锦囊中,竟装著一只完整的人类手骨,这个消息传开之後,顿时引起欧洲皇室的震惊,却不曾有人知道公爵为何会随身携带如此诡异东西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那只手究竟是谁的。
历史,依然沈默且无情地转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