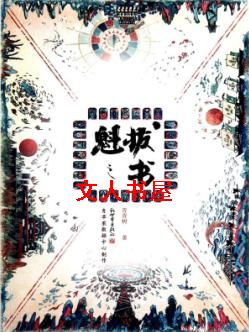坟场之书-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场生活过—样。”
伯蒂自豪地笑了,但笑容马上就止住了。他又一次看着坟墓。他说:“可是,赛拉斯,你会一直待在这里,对吗?如果我不想离开的话,我也可以待在这里?”
“一切皆有自己的时节。”赛拉斯说。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伯蒂早早醒来,此时的太阳还只是冬日灰色天空中挂着的一枚银币。他很容易就会把白天的时间都睡过去,整个冬天都在漫长的夜间生活,永远看不见太阳。所以每晚睡觉前,他总要提醒自己,他要在白天醒来,离开欧文斯夫妇那温暖舒适的坟墓。
空气中有股奇隆的味道,强烈又带着花香。伯蒂循着这种气味上了山,来到埃及路。冬天的常青藤一簇簇地悬挂着,那堵仿埃及风格的墙、塑像和象形文字就掩映在这密密匝匝的常绿植物后面。
那种味道在这里极其浓烈。有那么一会儿,伯蒂想,是不是下过雪了?因为常青藤上点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色东西。伯蒂走近几步,认真地看着那些白色东西。这是些五瓣的小白花。伯蒂把头凑过去闻闻这花香不香,就在这时,小路上传来了脚步声。
伯蒂隐到常青藤里,观察着。原来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是活人,正沿着小路朝埃及路走过来。那女人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华丽的项链。
“就是这里吗?”她问。
“是的,卡拉韦夫人。”其中一个长得又圆又胖的白发男人喘息着说。和其他男人一样,他手里也拿了一只大柳条篮,空的。
那女人似乎有些茫然和困惑。“如果你这么说,那好吧。”她说,“但我不敢说自己理解了。”她抬头看着那些花,“我现在干什么呢?”
男人中个子最小的那个把手伸到自己的篮子里,拿出一把已经失去光泽的银剪刀。
“市长夫人,给您剪刀。”他说。
她从他手里接过剪刀,开始剪下那一簇簇的花朵,又和那三个男人一起往篮子里装。
“这么做真是太可笑了。”过了一会儿,市长夫人卡拉韦说。
“这是传统。”那个胖男人说。
“太可笑了。”卡拉韦夫人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剪下白花,丢进柳条篮子。第一只篮子装满之后,她问:“该够了吧?”
“我们要把所有的篮子都装满,”小个子男人说,“然后把花儿发给古镇上的每一个人。”
“这是什么传统?”卡拉韦夫人问,“我当面问过市长大人,他说他从没听说过这回事。”接着她又说,“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看着我们?”
“什么?”第三个男人说,此前他一直没有开口。他留着胡子,戴着穆斯林头巾,“你是说鬼魂?我不相信有什么鬼魂。”
“不是鬼魂,”卡拉韦夫人说,“只是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
伯蒂很想隐藏到常青藤的深处,但他忍住了。
“上一任市长大人不知道这个传统,这不奇怪。”那个圆胖的男人说。他手里提着的篮子几乎已经满了,“花朵在冬日开放,这还是八年来的第一次。”
长着胡子、戴着穆斯林头巾的男人不相信鬼魂,但他却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着。
“古镇上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一朵花,”这个小个子男人说,“男人,女人和孩子。”他说得很慢,仿佛在努力回忆某件他很久以前知道的事。“有人离开,有人驻足,所有人都去跳骷髅舞。”
卡拉韦夫人嗅了嗅鼻子。“都是废话。”她说,又继续嗅着花。
下午的时候,黄昏降临得早,四点半就已经是晚上了。
伯蒂在坟场的小路上闲逛,想找人说话,却看不见有什么人。
他走到制陶人之地,想看看丽萨在不在,但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他又回到欧文斯的坟墓,发现那里也空无一人,他父亲和欧文斯夫人都不在。
他开始恐慌起来,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十年来,在这个自认为是家的地方,伯蒂第一次有种被人抛弃的感觉。他跑下山,来到那座老教堂,在那里等着赛拉斯。
赛拉斯没有来。
“也许我跟他错过了。”伯蒂心想,可他并不相信。
他来到山顶,朝四周眺望着。
寒冷的天空中悬挂着星星,城市里的灯——街灯、汽车灯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在移动,有条不紊地展现在他的眼下。
他慢慢地从山上下来,来到坟场大门前,站住了。
他听见了音乐声。
伯蒂听过各种音乐。有冰淇淋车上甜美的音乐。工人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克拉里蒂·杰克在他那积满灰尘的小提琴上演奏的乐曲,但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一连串深沉、抑扬顿挫的乐音,就像某种乐曲——也许是序曲——的开头。
他从锁着的大门侧身钻出去,下了山,走进那座古镇。
他从市长夫人身边走过,站在一个角落观察着。就在这时,市长夫人伸出手,在一个从这里走过的商人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一朵小白花。
“我个人不捐款,”那个男人说,“这事我交给办公室去做。”
“这朵花不是要你捐款。”卡拉韦夫人说,“这是本地的传统。”
“噢。”男人挺起胸膛,向众人展示着那朵小白花,神气十足地走了。
下一个从这里路过的人是个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妇人。
“这是干什么?”看着市长夫人朝她走来,她狐疑地问道。
“一朵花给你,一朵花给孩子。”市长夫人说。
她把花儿别在年轻妇人的冬衣上,把给孩子的花儿用胶带粘在孩子的外衣上。
“可这是为什么呢?”年轻妇女问。
“这是古镇的习惯,”市长夫人含含糊糊地说,“算是某种传统吧。”
伯蒂继续往前走。无论他走到哪里,都看见人们身上戴有那种白花。在街道的一个角落,他看到了和市长夫人一起的那三个男人,他们每人手里都提着篮子,不停地向路人分发白花。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从他们手里接过花,但大部分人还是这样做了。
音乐仍在放着,只是不知在什么地方,声音若有若无,庄重而古怪。
伯蒂把头歪向一边,想确定声音的来源,但这只是徒劳。
音乐在空中,它无处不在。它在飘扬的旗帜和遮阳篷上,在远方车辆的轰鸣声中,在干燥的铺路石上马蹄的嘚嘚声里……
真奇怪,伯蒂看着人们朝家走,心里想。他们正按着音乐的节拍走着。
留着胡子、戴着穆斯林头巾的那个男人篮子里的花儿几乎没有了。
伯蒂走了过去。“对不起。”伯蒂说。
那人吓了一跳。“我没看见你。”他说,言语之中带着责备。
“对不起,”伯蒂说,“能给我一朵花吗?”
头戴穆斯林头巾的男人将信将疑地看着伯蒂。“你住在附近吗?”他问。
“对。”伯蒂说。
男人递给伯蒂一朵白花。伯蒂接了过来。
“哎呀!”有什么东西刺到了他的大拇指。
“把它别到外衣上,”那人说,“小心别针。”
伯蒂大拇指上冒出一滴猩红,他吮吸着大拇指。
那男人把花儿别到伯蒂的毛衣上。“我从来没在这里看见过你。”他对伯蒂说。
“我确实住这儿。”伯蒂说,“这些花儿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古镇的传统,”那人说,“在这座古镇形成之前就有了。当山上坟场里冬日花朵开放的时候,就把花剪下来发给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贫穷富裕。”
现在音乐声更响了。伯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戴了那朵花,于是能更加清楚地听到音乐。他能分辨出音乐的拍子,有如遥远的鼓声;他能分辨出风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乐音让他想飞跑过去,随着音乐起舞。
伯蒂从来没有以观光者的身份到过任何地方。他忘记了不能离开坟场的禁令,忘记了山上坟场里的死者都不见了,他一心只想着那座古镇。
他穿过镇区,来到老市镇大厅前的市政花园。(这座花园现在是博物馆以及旅游信息中心,市镇大厅已经搬到古镇另一边的一座更有气势、更新一些但也更加无趣的办公大楼里了。)
市政花园里已经有人在闲逛了。现在是隆冬季节,市政花园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片随意点缀着台阶、灌木丛和雕像的宽广草地而已。
伯蒂入神地听着那音乐。三三两两地,一家人或一个人,不断有人走进这座广场。他从来没有同时看见过这么多活人。他想,这里肯定有几百人,每个人都在呼吸,每个人都像他一样鲜活,每个人都戴着一朵白花。
“活人就像这样过日子?”伯蒂心想,但他知道应该不是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肯定很特别。
他先前见过的那个推婴儿车的年轻女人站在他身边,手抱婴儿,随着音乐摇头晃脑。
“这音乐要持续多长时间?”伯蒂问道。
但她一言不发,只是摇晃着,微笑着。伯蒂觉得她笑得不太正常。他敢肯定这个女人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也许他不知不觉间隐身了,也许是她对他不够关注,没听他说话。
就在这时,她说话了:“哎呀!就像圣诞节。”她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做梦,仿佛她正从外面看着她自己。她用一种身在异处的语调说,“让我想到了我奶奶的姐姐克拉拉。圣诞节前夜,我们都在她那里过。我奶奶去世以后,她在自已的老钢琴上演奏音乐,有时还唱歌。我们吃巧克力和坚果,她唱的什么歌我都记不得了,但那音乐真是太美了,就好像所有的歌都被同时演奏出来一样。”
婴儿的头靠着她的肩膀,似乎睡着了,但小手也在随着音乐轻轻地摆动。
后来,音乐停了,广场上一片寂静。那是一种压抑的寂静,就像落雪带来的寂静。所有的声音都被夜晚吞噬,广场上的那些身体没有一个跺脚或移动,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近处的一只钟开始敲击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