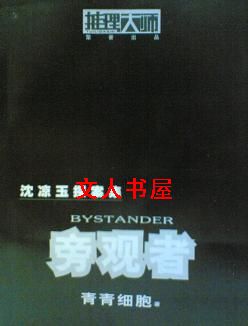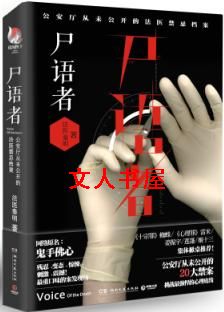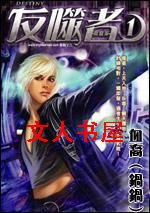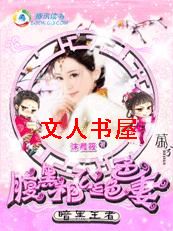网人 作者:黄孝阳-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电子版?人家为何要掏钱买你的时代三部曲?你说,你的时代三部曲是写给十八岁以上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们。
他说,这恐怕是你一厢情愿了吧。这部分人有多少?现在谁的工作、生活压力不大?大家对有趣、休闲、情感等方面的需求恐怕要远远大于对思想的需求。而对思想有需求的人又有多少个会对你的小说感兴趣?首先杂文比小说更能准确、鲜明,富有逻辑性地表达思想;其次比你更有思想的人海了去,光解读大师的作品都够他们呛;再次你也不是名人,凭什么让人有兴趣拿起你的小说又仔细读下去?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包装你。只是风险太大。你的小说比较边缘、写法也另类、新鲜。我承认,从文学观念上来说,它确实是一种好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与王小波的东西可以做一番比较,但这样的小说很难获得主流媒体的承认。王小波生前谁愿意出版他的书?《黄金时代》现在满大街都是,加上盗版,数不清到底有几个版本。可94年华夏出版社推这本书最早的一个版本卖了多少?亏得一塌糊涂。香港那边干脆把《黄金时代》改了名字叫《王二风流史》,拿它当一本准情色读本来操作。这说明什么?默杀、封杀,因为无法置评,超过了主流媒体的经验范畴与认知习惯;因为它是一种威胁,一根令一些人不大舒服的刺。所以说,这样的市场风险与政策风险,我承担不起。何况你的性别与年龄亦毫无优势可言。要知道,想真正推出一个新人,投入起码在三十万。我是一个商人。任何一部文稿,不管作者再怎么呕心沥血,对它付出过多大的感情,在你这里,它们只是冷冰冰的产品,有的产品能够转化成商品,完成那惊险的一跳,有的不能,或者说很难,不值得付出那样的代价。
你说,你明白。你也曾经是一个小商人。你心知肚明故事的重要性。但只是不愿意打着“写实”或者“新写实”等旗帜去写,譬如电影在细节、悬念、场面方面的表现力完全不是小说能够相提并论。如果小说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与临摹,那它只有死路一条。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就说电影能替代过去许多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且是最要紧的部分,并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得多。
他说,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些人爱读小说?你说,第一,一本书大小有限。方便携带,方便阅读,有纸质感;第二,文字的和谐与美感,这是汉语的最伟大处;第三,小说中的一些东西毕竟是电影表达不了的,或者说无法表现得那般充分。但你对此也常觉疑惑,因为小说所渴望表达的,坦率说,在未来的网络里完全能够实现。网络极可能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并行的虚拟世界。每个人在那或许也会领到一张身份证。你甚至还时常怀疑现在这个现实世界其实也是一个由其它智慧生物所设定好的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智慧生物我们根据祖先留下的记忆碎片将其称之为上帝。
他说,第一,所谓纸质感,更多是人们对传统阅读的留恋,所以作品必须得符合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中国人的传统阅读习惯是什么?是人物,是故事,是情节,而不是意识流,大段的心理描写与对真实的追问。人物要有外表,张飞豹头环眼,关羽面如重枣,刘备动不动如丧考妣放声大哭。这些人物能形成一个极易识别的脸谱,忠奸智愚一目了然。他们要有过去,不能平空消失或出现,行为皆由因果牵动,如长江之水由西向东,从高至低,决不会中途掉过头来流。他们不能平空出现或消失,得合理,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线性因果推动性格形成与情节前进,一切果皆由因,一切因必种果。他们最后完全独立于作者之外,作者不能忽然跑出来指手划脚唾沫四溅。至于故事,它当然得有趣、好看,煽情,足够消闲,不能通篇灰暗压抑,没有一丝光亮——你小说中的愤怒、绝望、阉割、荒诞、疯癫、虚无,那是万万要不得多,顶多像芥末撒上一丁点——被孔老夫子熏陶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一向缺乏悲剧意识,所以不能把瓶子彻底打碎。第二,关于文字的和谐与美感,我承认。不过,你还没有认识到文字的历史沉淀。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等等,这些文字无不贯注了一个个民族几千年的精、气、神。这种底蕴决定纸质书永远不会被一些电子光束所彻底淘汰。当然,我也并不否认它们或有一天会进入博物馆的可能。第三,客观的真实是一个无限的问题。只能回答,为我所见的,便是真实。这是客观的唯心主义。唯心与唯物,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既然不知道,那干脆不去问,不去想,一个人若只看到眼前,叫短视;看到明天又或一个星期,叫精明;看到一个月乃至一年,叫智慧;看到一生,那叫悲哀。关于人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参差百态一点好。我不反对你的看法,也不赞成。你要记住我目前的角色,我现在是一个出版商。
你说,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书在现在好卖?他说,其实开始已经讲了一个符合传统阅读胃口的书,但时代在前进,更好卖的书是与时代同步振动的。内容新鲜、形式时尚等。这里面说起来就话长了,你有没有兴趣听?你点点头。他说,有一个犹太法则,世上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皆为百分之二十的人所创造,并为其所享用,此法则同样适合于做书的选题策划。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买书的人究竟是哪些人?父母买给孩子看。譬如,名着、励志书、学习书、教辅书等。不过,自己掏钱为自己买书的青少年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对什么书感兴趣?按顺序可作如下排列——教他一技之长或给其职业添砖加瓦的书,譬如计算机、考研辅导等;搞笑、幽默、有趣的书,客厅读物,休闲读物,可以在枕上读,厕所读,路上读。你说,是的,网络上这种资源海了去。一个好编辑,得是足够年轻足够酷的编辑来选稿,再加上一个老练的文字编辑来校订。无厘头大有作为。这个系列里,一年整出十来本没问题,简单一句话,找概念,再找相应文章,再来把别人已经出的笑话幽默什么的玩意拿过来作参考。他点点头,说,一些小故事大智慧之类的励志书。它与幽默书一样都可以与读图时代溶合在一起。找出切入点来。这将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操作;通俗易懂谈赚钱又或是为人们打开一扇财富之窗充满金钱与梦想的书。谈赚钱的书永远也不没市场,梦总是迷人的。这也是看一个如何写,如何面对特定的人群进行再细分的过程;好看、刺激、能充分满足感官需求的书,这里面就包括从游戏派生出来的奇幻小说。这里的市场大得惊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把书与软件游戏结合起来。还有诡异恐怖吓死人不赔命的小说;时尚话题。它包含两方面,一是概念,譬如小资、波波等够酷、够眩目的一些崭新的生活方式及理念。你说,小资过了是布波(BOBO),布波过了是什么?他笑起来,是狗屁。就纯文学书而言,出名人的书当然最好,但僧多粥少,书稿难求。可找那些有潜力,后劲足,目前还未冒出头的年轻人,跳出一个做书的狭窄概念,做人,做的不仅是他本人,更重要的是做这个人背后的底色,他所代表的思想,生活方式等。三流编辑做书本身,二流编辑做作者,一流编辑做概念。目前做纯文学的还多半是把一些各种风格不同作者的书放在一个系列推出。换一个思路。不从书这方面入手,从“人”这里入手,同时推出同一个人的几本书。当然,这些书具有好小说的几大特征——深刻、新鲜、悲悯、有趣——技术层面上的立意、结构、语言、情节、人物皆有可圈可点处,以及烙印在这些特征上的“智慧”。这是内容上的“新”。版式花样、开本大小,封面设计等也都强调一个“新”,譬如在小说里加入世界名画来阐述细节,把那些揉碎了的黑芝麻串起来,让它们具备连环画一般的动感,就能弥补故事性的不足。说句老实话,我很想做你的小说,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说,那什么是畅销书呢?他说,畅销书其实是一个很极富弹性、相对的概念。它的弹性不仅表现在绝对销量上,还表现在我开头所言的这种种选题都有可能成为畅销书的可能。你笑起来,畅销书的实质?特征?其生成机制,内在动因?似乎都没有讲清楚哦。他笑了,那你不妨讲讲看?你说,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畅销书”下过一个定义——一个时期内,在同类书的销售量中居领先地位的书,作为表明公众的文学趣味和评价的一种标志。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是迎合“公众”,或者简称为媚俗。媚俗不是贬义词,它意味着出版商对公众此时此刻心理需求的准确把握。你渴了,我这里有水;你饿了,我端来香喷喷的大米饭,你不想吃饭喝水,只想喝可乐、肯德基,我也懒得告诉你快餐吃多了会发胖,我的职责只在于尽快把水与米饭收起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为你送上可乐与快餐。他笑起来,一切皆由公众的欲望说了算。他们是上帝。畅销书所体现的种种是社会政消费治、经济等诸多规律在文化产业上的投射。它纯粹是一种商业运作,一种贴着煽情、励志等时髦性感标签的产品。一个好出版商在判断一本书是否畅销时,必须摒除文学意义、思想价值等因素,除非它的文学意义、思想价值强大得能够成为一个足够眩目,让人眼花缭乱的口号。你说,是的,它得通俗,富有亲和力,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能摆着一副权威的面孔高高在上,哪怕再专业的书籍,在畅销书运作的范畴内,也得放下身段,借助于漫画、卡通、寓言、小故事、等表现手须来让它变得慈眉善目,从而将其阅读障碍尽可能减少到零。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一部满篇之乎者也的书注定不能成为畅销书。一部在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