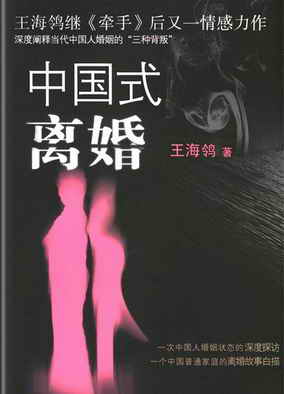离婚-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
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
四
“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张大哥请客无须问人家有工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说有工夫。
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无论什么事,他就好象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到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抽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得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
“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五点半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
“好吧,”老李把事才听明白。“别多弄菜!”这句说得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
老李确是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
整五点半,敲门。其实老李十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两三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
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三个人情,两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她谈话!
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她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像,都有点象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她看着象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象姑姑,及至她一说话,你才敢决定她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她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式,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髻,心中觉着失去平衡。
“坐下,坐下,李老!”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这里有的是茶,瓜子,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不客气。把大衣脱了。”她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
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臂上。坐下,没敢动大婶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奇…书…网屋中已安好洋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得方便的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
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时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作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期”火锅,与气象预告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窖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近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朴秀雅的。
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她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象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作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的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
五
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象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无事忙。坐下。有茶没有?”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我去把东西交给她,”头向厨房那边点着。“就来;喝茶,别客气!”
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象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至好也不过和手纸,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老李,”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儿,“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哈,”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
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换洋火人家不要,真使他想不出办法来。
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舐了舐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
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六
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
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漂着一层油星和绿香菜叶,好象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给冲得滑腻,言语就象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
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
张大嫂作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作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她马上就都搬运了走,好象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的替她收拾一切。设若她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她是个女神仙。
张大哥给老李一只吕宋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燃,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弹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仿佛是。
“老李,”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
他的嘴唇动了。
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
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的那么急。
“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不大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
第二
一
“有什么事,坐下说,二妹妹!”张大哥命令着她,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这不是外人;说吧。”
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
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说话呀,二妹,你看!”
“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泪又是三串。
“为什么呢?”
“苦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抽气,“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巡警要是枪毙他呢!”眼泪更加流畅。“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张大哥说。
“就是圈禁一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
老李看出来,她是个新媳妇,大概张大哥是媒人。果然,她一边哭,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