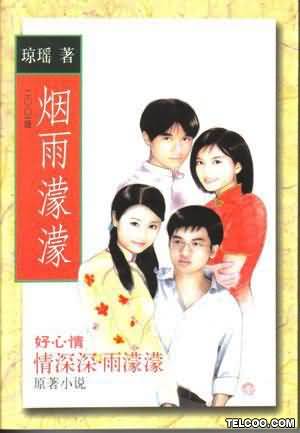烟雨一蓑-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感觉。脚穿矮跟布鞋,即使这样也比父亲高出得多。白白的脸上一双嫣然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着,如桃花丛中挥舞翅膀飞逐的蝴蝶。也许是整日劳累,身上没一点赘肉,走起路来很有那种城里大家闺妇身材款款婀娜如柳的韵味。
父亲突然有股攀不上的感觉。
姥爷的村庄就在爷爷要饭到过的那个刘山下,依山傍水,山村人家。姥爷一生想要个儿子,生了五个女儿后,第六个才是男孩,可惜又饿出病来死掉了。姥爷的五个女儿在当地是出名的,个个出落的水灵大方,如五朵出水芙蓉,光彩艳丽。母亲排行老二,姥爷上过私塾,读的最熟的是《三国志》,在当地小有名气。给五个女儿分别起名叫迎春、春香、夏薇、秋茗、腊梅。姥娘生下母亲后,母亲身体很弱,哭起来像小猫没声没气,姥爷是封建家长制专横的人,叹了口气,“唉!这孩子活不了了。扔掉吧。”母亲被扔到村东乱坟岗子一天了,姥娘总觉是自己心头肉,傍晚去看了看,发现母亲还没咽气,心想,“这孩子命不该死!”又抱回家竟然慢慢养活了,并且,姥爷五个女儿中,唯有母亲生的孩子最有出息。
“哎,我爷在浇菜园,到了你可要打招呼。”母亲和父亲走到村后面的水库边,母亲老远就看到姥爷和一个本家姥爷站在水库一角,挖了个大坑,用两条绳子拴住水桶两边,一人一条绳子,站在大坑的两边,来回拽着水桶,不断地提着在汲水浇园。
“爷,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母亲低声对姥爷说。“大叔,在浇园啊!”父亲打着招呼。
“先回家吧。”姥爷低头收拾着水桶、铁锨,也不多说。
姥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见父亲矮矮的个头,黑黑的普通样相,如降嵋山上烧焦了半拉子木头,就没看中,皱着眉头,在天井里背着手来回踱着步。
“不行!不行!不行!”父亲在房间里听见姥爷在外面对着母亲说。
“爷,你小点声。那我怎么办?我带着三个孩子,你让我嫁给谁家?要不三个孩子你们带着,我另找个合适人家。”母亲在外面抽泣着。
姥爷没有话说。
姥娘一开始不敢说话,最后说:
“孩子的事情,让她自己说了算吧。当初那个是你给她挑选的,虽然个头高大,但我看着黄焦蜡气的,不像个好身子,这不没几年死了。你看这个,不就是个子矮吗?人好身体好就行。”
父亲和母亲回来,又到村里代卖点赊了两斤糕点,把母亲送到家里。女孩正在家里哄着男孩,男孩一见妈妈回来,跑着扑到怀里,父亲把糕点打开拿出几页递给小男孩,孩子一把抓过来偎依在母亲身边贪婪地吞咽着,恨不得把指头吃进去。父亲又拿几页递给女孩,女孩接过来,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母亲,抿嘴咬了一口。最后父亲递给最大的男孩,大约十一二岁,男孩正在用刚折来的柳树枝子左一道右一道飞扬着修补一个破筐子,冷冷幽幽地看了看父亲,没接过来,拿起一把镰刀,削了削散乱的树枝,“吧唧”一下把镰刀扔到地上,低头干自己的活去了。镰刀落到地上,跳起来差点迸到父亲脚上。
父亲心里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后跟。
4月20日,柳梢吐绿,飞絮淡淡,榆树青翠,榆钱簌簌,草长莺飞,春燕呢喃,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母亲和父亲定好今天在飞水公社门口碰头去民政处登记。
天空飞起了毛毛细雨,幸福就是毛毛雨。父亲贪婪地吸吮着新鲜湿润的空气,任毛毛雨在春风中亲吻轻拂着,任一种只有春天才在我们当地出现的名字叫“龠龠”的漂亮小鸟在树上婉转欢快鸣叫,任杨花在粘着丝丝雨意吻在脸上贴在身上。那洁雅如絮似雪的春杨花,细雨中飘飘的雪,轻轻的雪。“不斗华不占红,自飞晴野雪。”古人叹:“飞絮淡淡舞起,游丝漫漫凝成。去时狂逸住何曾?总付流光一梦。素心原无管束,岂为牵惹东风。斜阳院落砌层层,惆怅青衫犹冷”,“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漂泊怨他飞。淡日滚残花影下,软风轻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借蒙蒙细雨般的杨花来表达孤寂、失意、怅然和抑郁的愁绪。而如今,杨花多情,杨花浪漫,杨花激情,不再寂寞,不再孤独,不再惆怅,不再愁肠,千寸柔肠,万种才思,为爱痴痴地笑,把情狠狠地烧。
在路边雀跃行走着,父亲36岁的人像孩子一样不时跳起来,伸手够那些路边青翠欲滴的杨柳。毛毛雨给了激情,毛毛雨的婚姻给了激情,这段没有爱情的爱情给了激情。上帝恩赐!菩萨保佑!迟落的红绣球终于在36岁这一年从空中飘悠悠砸到了他头上。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办,特别是在农村,找不到媳妇那是要低人一等,现在自己说到媳妇了,不管怎么着,自己就要登记结婚了,不管怎么着,秦戈庄从此又少了根光棍,少了个寡妇,多了个家庭,多了份美满。不管怎么着,父亲就要结束人影相吊的茕茕孤身了,不管怎么着,伴随着1966年这明媚的春天,父亲的春天到了。
父亲矮小的个头陡然感到高了许多,心里底气也陡然十足了。
哎嗬嗬嗬嗬嗬呦!
二月里来呀冰床开,
麦穗子发情把尾摆,
苇唧唧来探亲,
燕子双飞把窝盖。
走到村北甘石桥,父亲看到前面有两个人在赶路,感到面熟,走近看竟是如胭母子。两人大包小包地背着,毛毛飞雨中急匆匆。
“是你们娘俩啊,这是去哪里啊?”父亲问。
“二哥,我和孩子走了。到县城去投奔我失散多年的一个姨娘。”如胭说。“怎么不在村里住了?”父亲问。
“伟,你自己先朝前走,我和你大叔说句话。”如胭说。
“二哥,你说,我不走,在村里我还能待下去吗?王二死了,我整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那些光棍晚上像猫一样在屋后乱转。”如胭眼圈发红。“不走没办法了。”
“在村里再找个合适的,出去也不好过!”父亲说。
“不是没找。看了几个,不如意。有如意的吧,孩子死反对,我也没办法。大狸猫老是缠来缠去,每次他去看我,王伟就是不接受他,整天连摔加踢给我脸色看,搞得大狸猫也很郁闷。或者我前世接触男人太多了,老了不能再找了。”如胭话音带点凄凉。
“我想过了,还是不找了吧!这么大年纪了,再找也让人笑话。眼看孩子要急着找媳妇了。”如胭说,“哎,二哥,你这是去哪?”
“哦,我去飞水街看一个亲戚。”父亲听如胭这一说,突然把今天应当说的事情咽到肚子里去了。
如胭一提她孩子王伟,父亲又想到了母亲那11岁孩子冷幽幽的眼光和迸起的镰刀,兴奋的心又伴随着毛毛雨逐渐变凉。
母亲和大姨已早到公社门口,左盼右盼就是看不到父亲的身影,翘望着蒙蒙雨中的行人,母亲试图从那里面挖出父亲来。
“不是早说好了吗?怎么就是不来,不会有错吧?”大姨问。大姨家就在飞水街,为了母亲的今天,她一大早先赶到了母亲家,和母亲一道来的。
“不会啊,他说早一点赶到等我们。再说他那腿,人虽矮腿很快。”母亲说。
“唉!你说,这你和他结了婚,不还得生孩子吗?已经三个了。”大姨说。“我们女人不就是会生孩子吗?你不也生了六个了吗?”母亲说。
“唉!我是担心你年纪大了,再生这身子靠不住。”大姨说。
虽然没有太阳,母亲也估摸着有十点多了,就这10公里地,父亲早就该到了。看着偶尔满怀喜悦进去登记的一对,一会儿双双欢天喜地出来,低着头看着一张奖状样的东西,母亲也犯急了。
“春香,要不,咱先回我家吃饭,呆会儿我打发孩子来看看。他要再不来,我到他家找他算账。”大姨忍不住了。
“大姐,再等等。他肯定有事,不然早来了。”母亲说。
“哎哟,你这还没登记,就向着他了。好,好,再等会儿。再不来,老娘没耐性了。”大姨发狠开玩笑。
“哎,你先在这等一等,我去找个地方解手,早上菠菜汤喝多了。”大姨说。大姨瞅眼看了看公社大院里面,几次抬脚欲进,又感到胆怯。实在憋不住了,把手中的包袱塞给母亲,一溜小跑到了大院西边的一个草垛场。
“啊”一声尖叫,“你怎么在这里?”大姨进了草垛场,躲到一个草垛后面急急地解开裤子“哗哗”而流,一抬头突然发现父亲躲在草垛后面。
大姨瞬间羞得脸红红的,顾不得许多,慌里慌张扎好腰带,拖着父亲就出来了。“春香,你看,人在这里。来了不见我们,躲在这里。”大姨火了。“说,你究竟什么意思,想耍我们啊?仕途,告诉你,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看上你,你祖宗八辈就烧高香了。”
“唉!大姐,不是这个意思。”父亲解释着。“我真担心我和那几个孩子合不来,怎么办啊?一辈子别别扭扭的,怎么过啊?”
“不管了,你今天来就给我进去登记去。孩子的事你和他们慢慢来。要是没孩子,你跪着求我妹妹,我们也不答应。”大姨拖着父亲就进大院。
“哎,哎,这干啥哩?拉拉扯扯的。这可是公社办公的地方,不是打架的地方。”传达室一个老头拦住问。
“大爷,我们是来办结婚登记的。”大姨说。
“如今可是婚姻自由,这强扭的瓜不甜啊!”老头说。
“甜!放心!大爷,我们的瓜甜着哩。”大姨说着推搡着父亲和母亲进了大院来到民政办。
民政今天办理业务的是一个戴着黑边老花镜的老头,他把眼镜向下推了推,露出两个老鼠一样的小眼睛,黑溜溜地滚动着。
“干什么啊?”老头问。
“大爷,我们结婚登记。您吸烟,您吃糖。”父亲一看大姨这阵势,也不能犹豫了,主动向前,拿出一盒当时流行的价格九分钱的“丰收”牌香烟,掏出一小把纸包的透明的糖块。
“你和谁结婚啊?”老头眼还是向上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