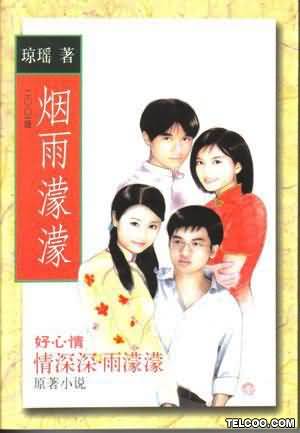烟雨一蓑-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效亮,怎么弄的?就只有这些粮食了?”主持分家的子灵老爷爷火辣辣地问我四爷爷,那样子,像是在审问他的作品。其实,连我老爷爷孟斗也不知道究竟粮食还剩多少,平常都是用一把锁锁在东厢房里。要分的粮食大约2石多。
“大爷,一直就这些啊!”我四爷爷低声唯诺着。
“大哥,算了,都是自己的孩子,你就主持分家吧!孩子都大了,成人了,该分了,我老头子了,分家后,他们两家轮流养我和你弟媳。”孟斗老爷爷吸了一口陈年豆叶。那时,喜欢抽烟的老爷爷是没有烟叶抽的,只好搓一把去年的大豆叶凑副抽。豆叶的烟味辣辣的怪怪的,搞得他长舒一口气。
子灵老爷爷从他的画纸里撕了块废纸,弄成两个纸团,对父亲说:“仕途,拿一个,吃糖。”他哄着父亲说里面是糖块,让父亲抓了一个。
“香臻,你也抓一个。”效亮四爷爷的大女儿香臻抓了另一个纸团。
父亲是1931年阴历四月二十日出生的,那时已经7岁了,记性特别好,所以当时分家的情景记得特别清楚。子灵老爷爷的分家是这样安排的:分到路北面是一间半屋外加湾北2分良田并带有一个约半亩地的院子,分到路的南面就是五间屋但院子比较小,其余2亩多地平分,粮食平分。结果父亲抓了路北面一间半屋外加湾北2分良田;香臻抓到了路南面五间屋。爷爷这一大家从一开始分家就注定了走向一条与贫穷命运决斗的路了。爷爷老实勤恳,这一性格传到我父亲辈一直留着明显的棱角,岁月怎么磨蚀,也去不了他的本性,一直到我辈,再到我现在12岁的孩子,都保留了这种老实善良的本分,只不过在我和孩子身上又多了份孤傲和狂放。刚分家不久,老奶奶就死了,为了办得体面些,两家凑钱体面地办了丧事,为此,爷爷只得把马刨泉4分地卖给了本村的朱勋久。
“分家了,要注意过日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孟久大老爷爷在他弟兄几个和村里也算是有学问的人。
“分家后,要注意忠孝节悌。我不求你们效仿二十四孝,但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要记住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灵老爷爷捋着长长的胡子教训道。
其实子灵老爷爷的忠告,爷爷和叔叔大多听不懂,只知道他在教训。
“仕昌,你也算是我们李家有文化的人了,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要注意修身养性。孟仲贫困之极,视你如己出,资你求学,指望能报国为家,汝勿辜负。”
“爷爷,我尽量做到,也正在考虑以后如何做是好。”大爷诺声相应。
分家后爷爷就带着一大家人在路北面居住,开始了打火烧谋生的日子。当时还是一大家人,父亲、我大爷、我三叔和我的两个姑都在一起生活。打火烧没有宽绰的地方,只得在这一间半屋。当时院子虽大,但空荡荡的,几株老梧桐带着斑驳的老树皮,不管这贫穷的春天,不管他娘的小日本还是国民党,空寂昂然地仰头面对春天绽开着桀骜的花朵,随风阵阵郁香飘散在院子里。破屋的西南角,是一盘爷爷的爷爷就走出来的圆圈,围着一盘磨,从爷爷的爷爷开始,就靠这盘磨,磨出了一家人的生计,磨出了岁月,磨出了沧桑,一直磨到我的童年。大爷李仕昌是1920年正月十三日出生的,死于1948年。听父亲说,祖辈以来个头都挺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可父亲就矮了,一米六多一点。大爷也是那种魁梧高大的体形,父亲说,大爷一米八二,长的也帅,和他现在看到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罗京几乎一模一样,就是罗京额头上缺少一个月牙样的伤疤。大爷小时候让骡子照头踢了一脚,就留下了一道伤疤。父亲一想起早死的大爷,就说:“你大爷那爷勒盖(额头)有这么一小伤疤,其他和那电视台的那个长得一个模样。”当时大爷已经在本家李孟仲老爷爷的资助下从国民党的学堂毕业了,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水平,也在家里帮忙打火烧。但大爷这时的主要工作是和本村的高守诚担任村里的财务管理,主办《土地晨报》。三叔么,典型的影视作品和绘画科班作品里的那种中国传统农民的写真,就知道低头种地,做不出其他惊人留名的事情。对他来说,土地是他的至亲,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这样活到现在。
打火烧,是从我老爷爷就会的一门手艺。虽然就是面食的一种,但在我们村周围,也是很有名气的。虽然本村和临村都有打火烧的,但就是没有我们家打出来的好吃。
火烧,有很多种,大多经过炉子烘烤而成,与烧饼有点类似。如有杠子头火烧、簸箕火烧、梭子火烧、坎火烧。有的带馅,有的不带馅。带馅的扁圆如肉烧饼、菜火烧,含陷似饺子,皮薄陷多,外酥里绵,鲜香味浓,轻咬一口,油水便滋溢而出。火烧还分为干火烧和油火烧两种。干火烧的做法是,把面和好揉匀,切成一两左右大小,用擀杖擀成薄皮,皮薄可至纸张一般,抹上油卷起,竖立压开,包入肉陷,再压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饼,放在专门打饼子用的鏊子(一种烙饼的平底锅,打火烧的比较大)上烙至外皮焦黄即可。油火烧则直接用面皮包陷,在平底锅浅油中煎熟,食用时,浇蘸上醋蒜汁,清香解腻,更为爽口,其陷多用猪肉剁大葱。也有用羊肉或牛肉的。不带馅的则为硬面火烧,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打法。
爷爷打的火烧,是一种硬面火烧,经过面粉发酵的,又不同于老潍坊的杠子头硬面火烧。杠子头也是用硬面和出来的,用枣木杠子压,中间薄,有孔,边厚。古时,用麻绳串成串,挂在鞍边、车旁,食之方便。凉吃越嚼越香;热吃,用菜、肉去烩,柔韧不散,非常有味。爷爷祖上流传下来的硬面火烧,工艺虽和一般的差不多,但只要吃过的人,就感觉不一样。手工面食就是这样,同样的工艺,面揉几遍,火候的掌握,出炉的时间都不一样,时间长了,就如同厨师掌盐用手一掂与秤准是一样。
爷爷打的硬面火烧,工艺就很简单。先由爷爷领着奶奶、大姑、二姑轮流推磨,把小麦一遍一遍地磨细,直到磨成面粉,然后把以前发酵过留做引子的类似酵母的干巴面用温水泡好。那时没有现在的酵母,只能留上次发酵过的面,我们当地人称“老面”。待“老面”泡开,以“老面”作为盆底,开始用水和半干半湿的面和面,一开始,不能用水太多,水太多了,和出的面太软没法用,故水要少。和出的面开始很硬,以后越揉越软了。面和好后,再用木杠子来回反复地压,其实也是和面,因为和的面多,没法用手和了,只能借助于木杠子,如同现在的机器和面一样,但机器和面的效果总是不比手工和木杠子和出来的面打火烧效果好。面和好后,爷爷先用柴草把煤点燃,挨到煤烟散尽,只剩红红的火苗,把鏊子放到炉上,根据火候就可以打火烧了。这时候就把和好的面揪成一个个的剂子,按成厚厚的圆饼,人工翻来覆去地揉,待揉到手感很好的时候,先放到鏊子上面烤皮,烤到半硬的时候,再用长长的铁叉子把它放到里面炉口的周围烘烤,要不断地翻,不能烤煳。最后根据烤的程度,一个个黄灿灿的散发着香喷喷面香的火烧出炉了,爷爷用一个大的柳条编制的当地人叫“浅子”的器具把火烧晾好,就可以卖了。当然这种硬面火烧,在北京等地方还叫“墩儿饽饽”,《天桥杂咏》中有一首诗形象地描写了卖饽饽的情景:
饽饽沿街运巧腔,
余音嘹亮透灯窗。
居然硬面传清夜,
惊破鸳鸯梦一双。
这个做法,一直到父亲这一辈,还一直这样做。
1938年的春天,刚刚下过的春雨,使寒冻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带着睡意苏醒过来,土地松松的软软的。
远远的巷里,传来父亲的童音:“卖火烧了!……换火烧了!……”当时一个火烧卖的话四个铜板,用小麦换的话,一两小麦。父亲这卖火烧的声音,从童年嫩嫩地喊着,一直喊到了苍老。记得我上高中时,家里还一直打火烧。
听着父亲的喊声,爷爷对三叔说:“打火烧的引柴火快没有了,三跟我去山上刨去。”穷苦的日子过惯了,爷爷显得有点麻木,老百姓还有什么追求,能吃上饭就是追求!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就是最高的追求!
他叹息着:“大妮、二妮,先把面发上,等我回来再和面。”
带着三叔出门,已是日头高高,爷爷说:“你大哥去推煤也该回了。”大爷年龄大了,爷爷已打发去坊子煤矿推煤。我村离坊子大约40公里,为了省钱,爷爷尽量不从镇上或安丘买,那样总是贵,而是让大爷直接去坊子煤矿买。但兵荒马乱,爷爷哪能放心?刚刚前不久,2月18日,驻昌乐县日军还到小善地村屠杀群众20人,打伤6人,抓走10人,烧房296间,被抓的10人中有7人被枪杀,村民刘德先全家被杀。潍县城后门街30名失业者去坊子推煤贩卖,行至城南王尔庄,被巡路日军杀害。
穷的连打火烧的引柴火都没有,爷爷只能到降媚山上去到处刨茅草之类的野草回来用,或从山上弄些灌木干柴。茅草长得很深,满山遍野到处是,爷爷带着三叔一会儿就刨满一筐子,然后爷俩一前一后用镢头扛着筐子下山。刚回来,大爷也推煤回来了。
“仕昌,怎么回来这么晚?”爷爷问道。
“爷(土语:父亲),我路上碰到鬼的好了,他动员我去参加国民党,和我拉了很长时间。”“鬼的好”名叫高瑞云,在飞水镇公所给国民党干杂活。
“仕昌啊,咱不图干什么党,只要平平安安就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