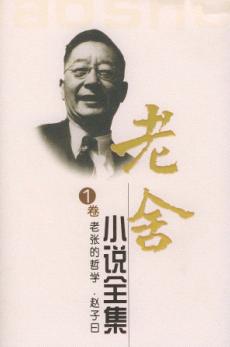三兄弟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剪了小平顶头,腋下长着毛,看起来像六十年代的疲惫的难民,她也的确是这样。当听说他老婆等着见他时,费恩一点儿不激动。
她名叫卡门·托波斯基·雅柯比,一长串她成年后用做武器的名字。她是奥克兰激进的女权主义律师,专业是代表女同性恋者起诉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每个客户都是与愤怒雇主斗争的愤怒女人。工作很难做。
她同费恩结婚已有三十年。结婚,可并不总住在一起。他曾与其他女人同居,她也曾同其他男人同居。他们刚结婚时曾与满满一屋子人同住,每周有不同的组合。人来人往。在六年的时间里,他们过着动荡的一夫一妻生活,生了两个孩子,都没有多大出息。
一九六五年他们在伯克莱的学生运动中相遇,两人都抗议战争和其他社会罪恶,都学法律,都忠诚于社会变革所需的崇高道德。他们勤奋工作,为选民注册,为移民工人的地位奋斗。他们在越南春节攻势时期被捕。他们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红杉树上。他们同学校里的基督徒斗争。他们代表鲸鱼起诉。每次游行都能看到他们行进在旧金山的大街上。
他们酗酒,以极大的热情寻欢作乐,喜爱毒品,他们搬出搬进,到处和人睡觉,这都没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为墨西哥人和红杉树斗争。他妈的!他们怎么会是坏人!
现在他们累了。
她很尴尬,因为她的丈夫,一个跌跌撞撞爬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出色人才,现在被关在联邦监狱里。他很高兴监狱在佛罗里达州而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然她会来得更勤。他呆的第一个监狱在贝克斯菲尔德附近,可他设法转了狱。
他们从不写信,从不打电话。她去迈阿密看妹妹,正好路过特朗博尔。
“晒得挺黑。”她说,“你看起来不错。”
而你像只李子一样萎缩了,他想。他妈的,她看上去又老又丑。
“过得怎样?”他问,并不真的关心。
“我工作得太辛苦。”
“那很好。”很好,她在工作,挣钱度日,这是她多年来时断时续干的事。费恩还有五年才能抖落脚上沾的特朗博尔的灰尘。他不打算回到她身边或加利福尼亚州。如果他能活下来(这是他每天都怀疑的事),他会在六十五岁时刑满释放,他的梦想是找一块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以字母排列的政府恶棍们无法行使司法权的地方。费恩非常痛恨自己的政府,他计划放弃自己的国籍,移民到其他国家去。
“你还喝酒吗?”他问。他当然不喝了,虽然他有时从看守那儿要一小壶解解馋。
“我还很有节制。多谢。”
每个问题都是讽刺,每个回答都是反击。他真的想知道她为什么来。很快他找到了答案。
“我决定离婚。”她说。
他耸耸肩,仿佛说:“干吗费这个心思?”不过他没这么做,而是说:“这主意或许不坏。”
“我又找了个人。”她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问,非常好奇。现在没什么能使他惊讶的了。
“一个男人,比我年轻。”
他又耸耸肩,几乎要说:“那就上吧,老太婆。”
“他不是第一个。”费恩说。
“我们别谈这个。”她说。
费恩无所谓。他总是崇拜她旺盛的性欲和充沛的精力,可很难想像这老太婆能定期干那事儿:“给我文件,”他说,“我马上签字。”
“文件一周后到。这次是一刀两断。再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财产可分。”
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雅伯法官和托波斯基·雅柯比女士曾共同申请位于旧金山小艇停靠区的一所房屋的抵押贷款。加州律师害怕冒犯任何人,因此他们写的申请书措辞干巴巴的,抹去了一切沙文主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歧视老年人的暗示:申请书显示的财产与债务之间的差距差不多近一百万。
一百万对他们双方都无关紧要。为了保护森林和农田等自然资源,他们忙于同冷酷无情的伐木工人和农民开战。事实上,他们曾为财产的匮乏而骄傲。
在加利福尼亚州,家庭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这意味着财产要大致平分。种种原因使离婚文件很容易签署。
有一个费恩永远不会提到的理由。骗局正在生钱,藏匿好的肮脏的钱,任何贪婪的机构都休想碰一碰。卡门女士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费恩不知道怎么会从夫妻共有财产想到巴哈马的秘密账户,可他也不想找到答案。给他文件他会高兴地签字。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谈了谈老朋友。时间很短,因为大多数朋友都死了。他们说再见时,没有悲伤,没有悔恨。婚姻很久以来就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他们终于得到了解脱。他没有拥抱她,只是祝她一切顺利。随后他去了跑道,脱得只剩下平脚短裤,在太阳下走了一小时。
第十章到达开罗的第二天傍晚,拉夫金在市内花园城的沙丽爱尔滨海路的一家路边餐馆吃晚餐。他喝着浓咖啡,注视着商店关门。
这些店有卖地毯的、卖铜壶的、卖皮包和巴基斯坦棉布的,都是做游客的生意。距离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一个卖古董的小贩仔细地收好帐篷,接着不留一丝痕迹地离开了。
拉夫金看上去很像现代阿拉伯人,他穿着白色宽松长裤,浅色咔叽上装,一顶压到眉毛的白色软呢帽。他从帽子和墨镜后面观察这个世界。他的脸和胳膊晒得很黑,黑发剪得极短。他的阿拉伯语近乎完美,他轻松地从贝鲁特跑到大马士革,再到开罗。
他住在尼罗河边的埃尔-尼尔饭店,与尼罗河隔着六个拥挤的街区。当他走过市区时,一个有外国血统的瘦高个说着还过得去的英语,突然和他走在了一起。他们彼此熟悉,彼此信任,随后一起向前走。
“我们认为行动就在今晚。”那联络人说,眼睛也遮着。
“说下去。”
“大使馆有个晚会。”
“我知道。”
“环境不错。车也多。炸弹会放在一辆货车里。”
“什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
“还有别的吗?”
“没有。”他说,然后消失在人流里。
拉夫金独自一人在饭店酒吧喝了杯百事可乐,考虑是否给泰迪打电话。自从他在兰利见到泰迪到现在已有四天了,泰迪没和他联系。他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泰迪不会干预。现在,开罗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地方,没人能有力地批评中情局没能阻止对大使馆的攻击。会有哗众取宠的表演和指指戳戳,可恐怖会很快被国人藏到记忆的深处,然后被忘却。大家都关注着即将举行的总统竞选。不管怎样。这世界变化太快。国内和海外有这么多攻击、袭击和盲目的暴力,美国人已变得冷酷无情了。二十四小时的新闻,一连串的突发事件,世界总是在什么地方有危机。新透露的消息,这儿冲突,那儿冲突,不久你就无法跟上时事的步伐了。
拉夫金离开酒吧回到房间。从四楼的窗户望出去,这座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城市,建筑杂乱无章,一眼望不到底。美国大使馆的屋顶就在他面前一英里以外的地方。
他打开一本路易斯·拉穆尔的平装书,等待着爆炸。
那是一辆两吨的沃尔沃嵌板式货车,满载着罗马尼亚生产的三千磅塑料炸药。门上喜气洋洋地印着城中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饮公司的服务项目广告。这家公司常去许多西方大使馆送餐。车停在供送货人使用的地下室入口处。
过去,这辆车的司机是个魁梧友好的埃及人,守卫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叫他谢克。谢克常常出入,为社交活动搬运食品和供给。谢克现在躺在车厢地板上。他死了,头上中了一颗子弹。
十点二十分,一个恐怖分子躲在街对面操纵遥控装置,引爆炸弹。他刚按下按钮就躲到汽车后面,不敢再看。
爆炸掀掉了地下室的支柱,大使馆向一边倒去。爆炸的碎片散落在许多街区,附近的绝大多数建筑都遭受了结构上的损坏,四分之一英里内的窗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传来时拉夫金正在打吨儿。他跳起来,走到狭小的阳台上,注视着烟尘。大使馆的屋顶再也看不见了,几分钟后出现火苗,警报无休止地响了起来。他把椅子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坐下来观看整个过程。不会再睡觉了。爆炸发生六分钟后,花园城停电了,除了美国大使馆的橘红色火光外,开罗一片漆黑。
他给泰迪打电话。
当泰迪的防窃听技术人员向拉夫金保证线路安全可靠后,那老人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仿佛他们是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聊天:“喂,我是梅纳德。”
“我在开罗,泰迪。正看着我们的大使馆在大火中化为乌有。”
“什么时候的事?”
“不到十分钟以前。”
“火有多大……”
“很难说。我在一英里外的饭店。我想涉及面很大。”
“一小时后给我打电话。今晚我留在办公室。”
“好的。”
泰迪转到电脑前,敲了几个键,几秒钟之内就找到了莱克。莱克正坐在他闪闪发光的新飞机上,从费城飞往亚特兰大——莱克的口袋里有一部电话,一部可靠的数字电话,只有打火机那么大小——泰迪又敲了几个键,拨打莱克的电话,泰迪冲着监视器说:“莱克先生,我是泰迪·梅纳德。”
还会是谁?莱克想。没别人能用这部电话。
“就你一个人吗?”泰迪问。
“请稍等。”
泰迪等着,接着又有了声音:“我在厨房里。”莱克说。
“你的飞机有厨房?”
“是的,一个小厨房。这是架很好的飞机,梅纳德先生。”
“很好。听着,很抱歉打扰你,可我有个消息。十五分钟前他们给驻开罗的美国大使馆扔了炸弹。”
“谁?”
“别问。”
“抱歉。”
“报界将会围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