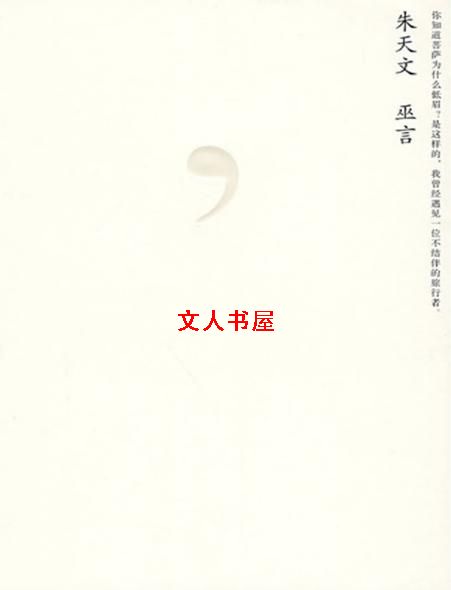巫言-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学会血腥味像铜的味道,某些时候也像嘴里含铁,铁味,而极度痛苦中,他像是可以尝到金属和皮肤上的盐分。警察看过太多死亡龌龊于是只得把死者非人化:“他们搬运尸体下楼时,几乎用拖的,尸体就在一格一格阶梯上撞来撞去,那是把尸体弄得不像人类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处理起来跟垃圾一样,你就不会有感觉,不会痛苦,不会去想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是喔波本加咖啡。”
咖啡使一切速度加快,波本使一切速度减慢。我转过五十七街沿第九大道朝北走,遇见阿姆斯壮酒吧(双塔消失的一年后也消失了),我进去要一杯“早年时光”波本威士忌,不加冰,与马修坐上一晌瞪着玻璃杯里的琥珀色液体像是里面藏着答案,像是透过琥珀色滤镜看世界:“喏,让光线变暗,音量降低,棱角化圆,它没有答案它只是溶化了问题,但往往那样也够了不是吗?”
如果我再朝北走一点,横过大道,五十八街和五十九街间我会遇见圣保罗教堂。我会绕过侧墙,走下一层狭窄楼梯到地下室,AAA,匿名戒酒协会。在那里,轮到马修讲话时他总说:“我叫马修,今晚我只听就好。”
——不,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我刚刚不喝酒那时,我的辅导人告诉我,如果我一整天下来一口酒没喝,就算成功的一天。那时我惟一赖以生存的清晰信念是,别喝酒,并参加聚会。
——唉我这一生老掉牙的写照,辅导人吉姆·法柏说,不是迟了一天,就是差了一块钱。
——那么艾迪死的时候没喝酒吗?一名戒酒成功很久的人只在乎这点。
——应该没喝,房间里没有任何酒瓶,看不出他破戒。
——噢真是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什么呢?不论喝醉或清醒,反正他都死了不是吗?
——没错,辅导人吉姆说,但如果他非死不可,我会很高兴他死的时候保持清醒。
“我说呐,”那时我忍不住插嘴,“你们这些戒酒人对这点,看得可真严重。”
“的确,这点似乎对我很重要,我想查出他死前是否保持清醒。也许因为如果是,那他除了一连串挫败便一无所有的人生,就有了一项胜利。所以我知道水合氯醛的事以后,就朝这个方向紧追不放。”“是喔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马修·史卡德。”
“唔,我必须往前走,我无法往前走,我会往前走。”
——那么我不可能收买你?你是那种绝对清廉的吗?未来纽约州州长说。
——大多时候我是容易收买的,马修说,但你不能收买我,惠森达先生。
那时山茱萸盛开叠叠似积层云的五月,我来到侦探作家协会票选最佳谋杀城市第一名,纽约,站在五十七街第九大道街角仿佛站在世界的中心。I of me,世界的中心。我朝西望,第十大道东南交口上,公寓二十八楼敞窗开向南及西,西街从华盛顿桥到炮台公园,越哈德逊河至纽泽西,一望在目。丽莎郝士蒙的公寓。马修来到公寓,脱掉靴子像脱掉他的生命留在门口,亦砰然把世界关在门外。我说,当然,马修说:“这始终是丽莎的意义。不仅仅是某种欢乐的来源,某次征服的欲望,某个好伴侣。她是一道我可以走出去的路。而我是那种总要走出去的人。不管我的生活其实多舒服,或我和我周遭一切多契合无间,我总会要溜出去一下晃荡。我的某一个部分。”
啊那已是两千年前夕(站在世界的中心我讶叹着遥遥当空一架Sony荧幕正在跳动变换着跨世纪的倒数计秒和计日),终究取得私探执照的马修为了工作起来方便些?收入合理些?因此体面些?“就说罢,我拿执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分子。”合法化的正常社会一分子有没搞错啊。是头壳坏掉?被收编了?堕落了?是江郎才尽?是老了?我与马修对望一眼,苦苦笑起来。以上皆是好不好,千禧年了吔。
——所以丽莎,我毁掉你的生活了?
——波本加咖啡?
——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你是说真的。答案是,不是。就像其他人一样,毁掉我生活的是我自己。
——是罢。
——总有一天,你不会再打电话给我,或者总有一天你打电话来,我会跟你讲不要,你不要过来。只不过现在,时候未到。所以,何不怜取当下?
“怎么说,怜取?”
“怜取当下。”语出古中国诗: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如此我站在世界的中心。朝东望,斜对街有大厦一栋,不可思议叫Vandemdome,凡登大厦果然是?一九九三年马修随伊莲搬来,大厦后面十四楼。但马修仍然保留了西北旅馆一间房做联络处,一间自我所在的小小私闭地?一只对过往弃不掉的奶嘴?我知道伊莲喝蔓越莓汁加汽水,我也喝一杯。
我沿第九大道朝南走,在五十六街后面找小猫小姐酒吧,已经消失了。一直走,五十二街巴黎绿酒吧,也已消失了。巴黎绿,一种砷的化合物,砷和铜,变成了毒药绿。再南走,五十街我折西过马路往第十大道走,前方转角处,那是葛洛根开放屋,我仿佛看见橱窗上霓绿灯闪着竖琴牌麦酒和健力士啤酒的矮胖桶。如果我走进去,那是间老式爱尔兰酒吧,一寸平方的黑白两色瓷砖铺地,桃心木长吧台,台后等长壁镜。典型的吧,不提供食物,一台自动点唱机,一架电视,一个飞镖靶和几条观赏鱼,那是米基巴鲁的店。
屠夫米基巴鲁。头颅又大又硬好似复活节岛上那些风化巨岩的米基巴鲁,眼睛绿得像绿玉髓,颜骨上数道血疤有几道横过鼻梁。关于米基巴鲁最被广传的乌何国故事,他带着一口保龄球袋走遍第九和第十大道酒吧,逢人便拉开袋子给看某某某的脑袋。人们传诵,他喜在店中穿那种肩膀到脚部遮住的洁白(除了上面的污渍)长围裙,仿佛刚下班的屠夫冲进酒吧快快喝杯酒。人们说他会指着一块新污渍说:“知道这是什么?是告密鬼的血。”
记得吧那首爱尔兰民歌《爱国者之母》,母亲要儿子就是死在绞刑台上也不要出卖秘密给敌人。仇视通敌者的了不起传统是吗?但我听过米基说:“所以喽,你也很清楚另外一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有通敌的了不起传统。你怎么可能只有此面而没有彼面?”米基喝十二年份的詹森牌爱尔兰威士忌,加两块冰角。但米基店的执照,连同行车执照,农地产房地产,皆登记是别人名字。我痴听米基如痴听佛法云:“不论你有什么,文件证明的或秘密拥有的,别人都可以从你手上拿走。若你不在乎,我想你就不会有问题。失去的东西倒也罢,怕是你恋恋不舍就麻烦大了。你不拥有,人家想拿走便没那么容易。”
——没错印第安人说,人类并不拥有土地,不过借用而已。
——我们怎么说啤酒的?你不能拥有它,你只是去租它。
——你也可以这样说咖啡。
——或是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事。
站在五十街第十大道转角,天色已暗,阻我前行。设若我前行,前面是地狱厨房。凶杀新闻称之地狱厨房而房地产广告名为柯林顿的这一带区域,已转型成中高级住宅区,我应可前行¨wén rén shū wū¨。但晚霞红得像血腥玛丽的红将城市涂上一层红,我遂告诉自己,这里是边界了啊边界,我好想前行,我不能前行……我站在公用电话旁边,像一个巫,呃,一个巫人,站在左边的左边。
这么说吧马修,光谱上,如果右边是社会化,左边是不社会化,巫在最左边,不能再左了。可如果再左一步呢?马修,再左一步那里会是有去无回的,非人区。
不是神不是鬼,不是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不知生亦不知死的动物比人可爱多了),皆不是。对此我无以名之,只好相对于人,名之为,非人。
非人区有去无回,没有从那里回来过的报导人,没有拉撒路那个从死境回来把一切告诉大家的报导人。那里蛊蛊的霓光映上我脸让我脊冷冷一颤而艳异的霓影已长长伸过边界伸上来时,我拔脚折返了。再回头,亮起霓虹市招的边界肃空无人,无车,惟公用电话一柱立在那里为明灭跳跃的霓虹所占满。
边界的电话。
多年前我遇见一位打国际电话的帽子小姐蕈形帽遮住大半张脸只尖尖一点下巴露出,她一通接一通打,一大把电话卡很快被吃掉像硝烟里炸开的弹壳迸飞落满地。我亦目睹一名热恋相思人,去到巴黎心不在焉只管一边换算七小时时差一边张望何处有邮局和烟草店可以买一百二十单位的电话卡打给恋人,黄底蓝色信鸽标志的邮局和tabac招牌和电话亭,构成了热恋相思人眼中的巴黎。我也曾在摩纳哥公园面向地中海的天涯断处看见旷无一物,除了一座钛银色电话亭,那时我坚信从亭里我可以打往海底,打到过去,打给晴日好风跳上墙头走入桂花树丛中就再没回来的猫咪它的名字叫麻瓜。感伤的马修啊,那些立柱式公用电话若全数取代了玻璃亭电话之后超人要去哪里换衣服?
我遂告诉自己,待天明,对,就是天明一大早,有人有车有市声苏醒时,我会搭L线换A线到十四街下车,往西走,我会遇见圣本纳德教堂,每天清晨七点有一场弥撒,八点有另一场在左边小房间。米基的屠夫父亲总在上工之前来望弥撒,常常带着还是小孩的米基一起。我会看见米基和马修,无论你称他们是男性情谊或者,男人那一套?他们总在各自,或者共同,完成一件耗尽心力的残酷任务后,相偕来此待待,总在夜尽天明,清晨的屠夫弥撒里。(其原型显然出自《教父》结尾的暴力美学,平行剪接着复仇屠杀和婴儿受洗。)所以我看见他们随仪式进行站站坐坐或跪下,念一段以赛亚书或一段路加福音。他们并不领圣餐,不告解,不祈祷,然后,对,然后他们离开。往西走,他们穿过哈德逊街格林威治街,走到肉类批发市场。
看哪肉市,Meat Pa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