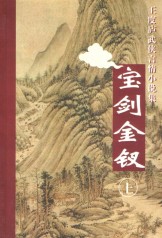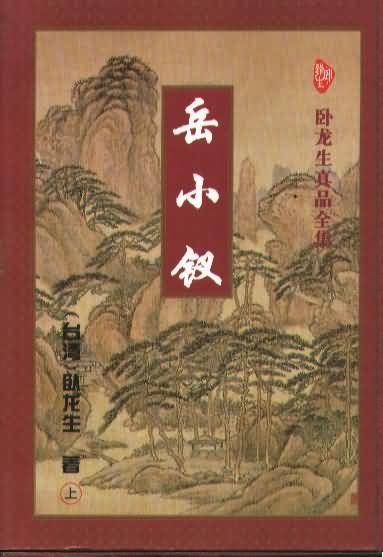弁而钗-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谷道内渍渍有声,赵生甚觉有趣,不知不觉把屁股乱颠乱耸,乱扭乱摇,发作了。翰林看他从来无此光景,知他得趣,一发狠肏,肏得赵生哼哼喃喃,叫:“亲哥哥肏得好,肏得快活。”把平时庄重光景一些也没了。翰林又抱转他头来与他亲嘴,又吐残唾与他吃。赵生到此时忘了形,竟与女子侍夫一样,便一一都吃了。翰林提出龟头,猛撞到根,那屁股内淫水肏得随屌而出,涓涓不断。翰林又抱定赵生,把屌在屁股内一顿揉肏,肏得赵生屁股里骚痒难当,骚水直流,道:“我要死也。”忙耸迎不止。翰林忍不住,着力一连几送,也泄了。那屁眼内方才止了痒。翰林道:“有趣么?”赵生道:“若不身历其境,安知当身有此乐巢。”此后夜夜如此。翰林却真心教他做文字,把笔气都改过了。
若要不知,须是莫为。他二人起初还收敛行迹,后来渐渐不谨。连秦先生也有些觉得,诸朋友一发不消说,然而只是胡猜,却无处实迹。又先生功令极严,住得又散,故即有好事者,也不能发其私。如此三月,赵生文字竟与翰林无二,连字也有些相像。一日会文,秦先生看到赵生文字,认做是翰林的,后来看到翰林的,方知那卷是赵生的。忖道,怎么他文字与遇之一样?这小子有些做怪了。着馆童召来赵生。
赵生到先生房内,先生道:“你的文章从哪里来的?”赵生道:“是学生做的。”先生道:“这文章是涂遇之做的,你哪里做得来。我着意仿他尚然不能,你幼学浅识,安能到得。”赵生道:“委实是学生做的,不信就面试。”秦先生就出个题目与他。赵生不待思索,一挥而就。秦先生看来,比会卷又好。先生大惊道:“做便是你做的,缘何造化这步地,若无口传心授,断不能模仿至此,你可从直说来。”赵生道:“不敢相瞒,因先生极口赞涂遇之好,学生虔诚请教,蒙他面指心教,才能造成此局面。”先生道:“二人光景已是可疑,今有此实证,一发是实了。我这里是甚么所在,你敢犯我规矩。”
赵生跪下道:“还望先生周全。”先生道:“涂生行藏原是可疑,如此看来,不是为我来,倒像是为你来的。”赵生红了脸,低着头,跪在地下。先生道:“你且起来,你好生收敛,我及门人多,看破不像模样,那时我却不恕你了。”
赵生谢了先生辞出,行未数步,只见馆童赶来道:“相公叫你转去,还有话说。”赵生只得又回见先生。先生道:“涂遇之人品文章,俱不似诸生中人,他虽拜我门下,我原以宾礼待他,他的文字我亦仿他不来,他既引你造到这地位,他也不是我损友,你也算作会取益的。方才我说的话不必与闻于他,恐他心中又多一番芥蒂。”赵生称谢而回,恐翰林知觉不妥,并不说破,只是自家深自避嫌远疑。五鼓归房,更静方至东园,日间相会淡如他人也。朋友们看他光景如此,倒也释了些疑。
忽一日,监台接秦先生进衙,一连十多日不回,先生不在,那些学生便不像那等各守己房,便东走西串。有两个没事寻事做的,一个叫做杜忌,一个叫做张狂,专好谈人之私,揭人之短。两个看破赵生与翰林的行为,恶狠狠道:“赵生这小畜生,我们同府人,倒不结交,反倒巴结外路人。今夜拼一夜不睡,趁先生暂时不在的机会抓住他们。”
至黄昏,他两个躲在隐暗处,看见赵生来到翰林住的东园,看得赵生入内,他二人便也挨身而入,赵生进了翰林卧室,他随后跟来,幸得韵出来看见,叫声:“是谁深夜在此?”张狂无计只得答道:“是张相公、杜相公。小赵来得,难道我们便来不得。”口里说,脚下便一步一步攒将上来。翰林与赵生正在那里做此道儿,听得人来,忙穿了裤子,抖一抖衣裳,走得出来。二人已到门口,道:“涂兄好受用也。”翰林正色道:“甚么受用?”张杜二人大笑道:“你休要瞒我,我已知道久了。”翰林道:“知道甚么?”杜忌指着赵生道:“知道他……。”赵生道:“知我甚么?”张狂道:“还要强嘴。真等我出你的丑?”
杜忌故意做好人道:“涂兄份上,存他些体面。”说完扯扯拉拉去了。赵生道:“这事怎了?羞杀人也!”翰林道:“为我受此恶气,心实不安。”赵生道:“只恐不从此而止。他二人极好拨草寻蛇,无事尚生波浪。他二人见此行迹,怎肯默然无言。”翰林道:“造化忌盈,好事多磨,乐极悲来,此理之常情,你我从此相会日少矣。”言罢,泪流满面。赵生垂泪道:“不可必者,外来之遇,能定者,吾心之天。天下尚有钟情如吾二人者哉。风波任彼,吾二人情终莫解也。愿吾兄耐心几日,待事少定,当续旧好。今日弟且回,恐二人谋孽生端,又多一番耻辱。”翰林亦不敢留,含泪送至门前,欲着人送,赵生道:“此处不远,园门关闭不便,不必送得。”赵生去远,翰林方回房,和衣而睡不提。
且说赵生别了翰林,行至中途,杜、张走出道:“赵兄,我们相候久矣。”赵生不答竟走。张狂道:“赵兄,何厚于涂生,而薄于弟等?”杜忌道:“从此厚起,也未迟哩。”就走到赵生身旁,赵生怒道:“这是怎么说?”杜忌道:“说不得,你把我肏一肏。”赵生看他出言无状,喝道:“胡说。没廉耻,我是何等人,你敢轻薄如此?”张狂道:“太做作,仅遇之肏得,我们便肏不得?偏要肏。”一个抱定,一个就去脱裤。
赵生看他们用强,知难脱身,便诳道:“兄既相爱,当以情讲。奈何用强。依我说便使得;不肯依我,虽死不从。我乱叫起来,你们有何礼面?”杜忌道:“心肝,只要你肯,一凭吩咐。”赵生道:“此露天地下,寒风凛冽,不好罄谈。同到我房中细细披陈。”二人被他一赚,便道真肯了。放了他同行,却是摸手摸脸,赵生只得听他。将到己房,道:“我先去叫门。你们略后退一步,”叫启开门,小燕开了门,赵生到房,也不说话,拔了壁上挂的剑,迎出门来,大呼道:“张狂、杜忌,你来,你来,好吃我一剑。吾头可断,吾膛可剖,吾身不可辱,今日之事,不是我凌辱你,是你寻我,好歹与你合命。”言罢,提剑赶来。
二人看他变了脸,手中又有利剑,又见小燕持解手刀赶出接应,看得不是风头,转身就跑,鞋子都脱落了。回到房中,整整颤了半夜。杜忌道:“屁股不曾肏得,几乎送了八寸三。”张狂道:“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拆开他们风月,也算不得是个人。我们逢人便说,传到秦老儿耳朵里,难道弄不得他们一个没趣?我们也泄这口气。”杜忌道:“是,是。”
且说赵生回房,把从前事对小燕说了一遍,小燕道:“天下从此多事矣。”两人长叹短吁,道:“月明又被云遮掩,花正开时被雨摧。”
第二日,张狂、杜忌对同窗诸友添出许多恶言恶景,个个说过,道:赵家小官会养汉。那些书呆听了这话,交头接耳,唧唧哝哝。赵生羞得不敢出房,又恐二人撞着,并不敢到东园,翰林亦不敢来。虽隔咫尺,若视楚天。张、杜又去寻着东耳生、水之藩,说这此话。二人素恨赵生不肯从他,又恨舍旧友寻新师,闻得此言,道:“好,好,今日可消夙恨了。”竟到赵家见赵生父,半讽半讥,一敲一打的说了一遍,发笑而去。
其父乃正气人,道:“气杀我也,我只道他寻师读书,倒做出这般流氓事来。”其母正在那里分劝,忽小燕来取供给。赵父性头上,一把揪着头发便打,道:“我叫你服侍那不成材的读书,叫你伏侍他做奸养汉。”小燕道:“这话从哪里来得?”赵公道:“还要强口。合馆俱知,东耳生、水之藩亲口对我说的,再不认,我去接了张、杜二人来质证过,活活敲杀你。”小燕想来不能隐言,就道:“老爷坐了,等我说来。相公又不是女人,就有此事,亦世俗当情,老爷得知,只好置之不理,其议论自息。奈何信他人毁言,伤自已天性?若去寻张、杜来,他已任造谤,岂息面情?出了丑,老爷面上也不好看。小相公一生事业未曾动头,后来还要做官,依小燕说,老爷只是隐瞒好。”
赵公被小燕一篇话说醒了,道:“倒也说得是。我错打你了,你去叫了那不成材的来。”小燕领命,到馆把这些话都说了,赵生道:“父亲知了,羞杀人也,不如死休。”小燕道:“江汉以濯之,不可冼吼,虽死何益。父子天性,我已讲过,不要与他分辨,让他说几句罢了。”赵生脸红了,点头不语。
小燕道:“可别一别涂相公么?”赵生道:“众人瞩目观望,怎可去得。自那日别后,迄今数日未能一见,想他肝肠断矣。若不别他而去,何以安其心,我作数字告别,庶使知我行止,少自慰也。”小燕道:“事不宜迟,快些。”赵生拈笔在手,道:“涂兄,仅隔数步,不得面晤而别,天何限我两人至此也。”言罢,泪落如雨,笺纸尽湿。小燕道:“要上街行走,不好看相。”赵生强忍泪眼,破涕而写,其札云:不肖辱蒙雅爱。自谓金兰契谊,共定千秋,而失意匪人。毁伤天性,家严震怒,不敢不归。岂不欲别,畏人多言,虽玉成有日,会合可期,而一日三秋,难熬此冬夜如年耳,有衣有食,愿台兄少留意焉。遇之情兄爱下。即日。
弟赵王孙泣拜别。
付小燕持去。将到东园,只见杜、张突出道:“你这贴旦,又传书递柬了。”小燕不睬他,竟走。杜、张知道有夹带,便赶来要搜,恰好得韵至,小燕道:“韵哥,我没功夫,还你耽去。”得韵会意,接了竟进东园。杜、张悔道:“再快些便落我们手了。”两人败兴而去。小燕回,道及前事,赵生伸舌道:“幸是不曾去,不然又受他一番恶说。”忙收拾同小燕回家见父。父骂道:“不成材的狗才,我怎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