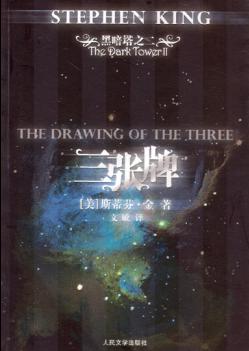三张牌 (单文档版)-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即,陷入一阵昏黑,他睡了十六个小时,睡梦中西海的涛声在他耳畔经久不息地轰响。
3
枪侠醒来时海洋已成一片昏暗,只是东边天空露着一点朦朦胧胧的光亮。拂晓将至。他坐起来,一阵头昏眼花差点让他一头栽倒。
他垂下脑门歇一会儿。
晕眩过去了,他瞧瞧手掌。是感染了,没错——整个手掌都红了,红肿一直蔓延到手腕处。没有再发展到手腕以上的部位,但他发现身体其他部位也开始有隐隐的红丝显现出来,这红色条纹最终会侵入心脏要了他的命。他觉出自己浑身发热,在发烧。
我需要药物,他想。可是这里哪有什么药物?
难道他走到这里就要死了不成?不,他不能死。如果他注定要死去,那也得死在去黑暗塔的路上。
你是多么了不起啊,枪侠!穿黑衣的男子在他脑子里窃笑着说。多么不屈不挠!
你那愚蠢的痴心是多么浪漫!
“我操!”他低沉沙哑地吼着,又喝口水。没剩多少水了。他面前是整个的大海,能喝就可以随便喝。水,全都是水,却没一滴是可以喝的。想也别想。
他扣上枪弹皮带,把它系紧——整个过程摆弄下来费了好大工夫,等他完成这套动作,黎明的第一缕光线已昭示白昼确实到来——他挣扎着想站立起来。他不能确信自己是否能做到这一点,结果还真的站起来了。
他左手扶着短叶丝兰树,右臂挟着那个还剩点水的革囊一下甩上肩膀,接着把皮包也甩上去。身子一挺直,忽而又是一阵天旋地转,他只得垂下脑袋,等这一阵过去,心里祈愿一切无碍。
晕眩过去了。
枪侠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那踉跄的脚步活像一个喝到晕头转向的醉汉,他费力地折回沙滩上,停下来,打量着像桑椹酒似的浑黯的海洋,从皮包里找出最后一点牛肉干。他吃了一半,这一次嘴巴和胃都能接受一些了。瞧着太阳从杰克殒命之处的山后升起,他把剩下的一半牛肉干也吃了——太阳先是攀上了那些寸草不生就像野兽利齿一般尖尖地耸立在那儿的山峰,一会儿就升得老高了。
罗兰脸朝太阳,眯起眼睛,微笑起来。他吃光了剩下的牛肉干。
他想:好极了。现在一点吃的都没了,我比出生时要少两个手指和一个大脚趾;我是个子弹说不定哑火的枪侠;我被怪物咬了生着病却没有药;剩下的水还够喝一天,如果我拼尽老命,也许能再走十几英里。直说吧,眼下我是濒临绝境。
该往何处去?他从东边过来,可是现在不能继续向西跋涉,因为他再也没有圣徒或是救赎者的力量了。那就只剩下南北两个方向。
向北。
这是他内心的提示。一个没有疑问的答案。
向北。
枪侠开步走了。
4
他一连走了三小时。摔倒两次。第二次摔倒时,他以为自己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这时一阵波涛卷来,当波涛快要冲到身边时他不由想到自己的枪,连忙下意识地直起身子,两腿抖抖瑟瑟像是踩在高跷上。
他估摸这三小时里自己大概挣扎着走了四英里。这会儿太阳已经非常耀眼,晒得地上越来越热了,但不管怎么说还不至于热到脑袋像挨了重击似的难受,也不至于使脸上汗如泉涌;从海面吹过来的微风,更不至于让他寒意丝丝地哆嗦个不停,弄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牙齿也直打颤。
发烧了,枪侠,黑衣人嗤嗤地笑着说。留在你体内的毒素开始发作了。
感染的红丝现在更明显了。从右腕一直延伸到半个小臂。
他又硬着头皮走了一英里,水囊里的水全都喝光了。他把空了的水囊和另一只一起系在腰间。地面上一片单调而令人生厌。右边是海,左边是山,他破烂的靴子踏着贝壳遍地的灰暗沙滩。海浪涌来又退去。他找寻着大螯虾,却一个也没见到。
他惘然地毫无目标地走着,一个从另一时间走来的人,似乎已经抵达一个无意义的尽头。
快到中午时,他再次倒下,心里明白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那么就是这地方了,这一时刻。毕竟,这就是终结。
他双膝双手着地仰起头,像一个被击败的拳击手……前面还有一段路,也许是一英里,也许是三(发热使他两眼模糊,在毫无变化的沙滩上根本无法辨识路程远近),他看见了一些新出现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就伫立在海滩上。
是什么?
(三)
没有的事。
(三是你的命运)
枪侠竭力使自己重新站起。他低吼着,祈求着,那声音只有盘旋的海鸟能听见(如果能从我脑袋上把眼睛抠去它们该有多高兴啊,他想,有这样的美味叼来吃该是多么惬意!),他继续朝前走,踉跄的脚步偏斜得更厉害了,身后画圈似的足印几乎像乩符一般怪异。
他竭力撑住脚步,睁大眼睛盯着前面沙滩上那个什么东西。发绺落到眼睛上,他连忙捋回去。可是这么走下去却似乎没有跟那东西挨近。太阳快升到天穹顶端了,那东西似乎还离得很远。罗兰想像着自己再度身处荒漠,跟那个最后的陌生人的棚屋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豆子吃得越多,屁就放得越响)
还有车站那儿的男孩
(你的伊萨克)
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他膝盖一下软屈了,又一下挺直,再一软,再挺。头发又落到眼睛上,他不再费神把它捋回去——没有力气顾及了。他看着目标,那目标后面的高地上有一道窄窄的影子,它还在走着。
现在他可以弄明白了,不管是发烧还是没发烧。
那是一扇门。
距离那门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罗兰的膝盖又软屈下来,这回却再也挺不起来了。他倒下了,右手划过砂砾和贝壳,断指处的创面又划出新的伤口。断茬处又开始流血。
他只好匍匐身子爬行,西海浪起潮落的嚣声伴随着他的爬行在耳边阵阵萦回。
他撑着膝盖和肘弯爬行,在脏兮兮的海草为标识的潮汐线上爬出一道歪七扭八的沟痕。他以为是风不停地吹——一定是风,凉爽的风,这能把他身体的高热带走一些——可是他听到的风声只是从自己肺部呼进吐出的一直吁喘着的粗气。
他靠近那门了。
更近了。
最后,在这近乎疯狂的一天的下午三时左右,在他自己左边的身影已经拉长的时候,他到达了。他蹲下身子,疲惫地注视着。
那门有六英尺半高,用坚实的硬木制成,然而生长这种材质的树木离这地方至少有七百多英里。门把手好像是黄金做的,那上边精工雕饰的纹样……枪侠终于认出了:那是一张狒狒咧嘴而笑的脸。
门把手上没有锁眼,上面下面,都没有。
门上装着铰链,其实什么也没关住——看起来似乎是关着的,枪侠想。这是一个谜,最最神奇的谜,但这事确实非常重要吗?你就要死了。你自己的谜底——对任何男人或女人来说最终惟一重要的事——即将揭晓。
凡事皆通,万法归一。
这扇门。这儿本来不该是立着一扇门的地方。它就矗立在潮汐线上边二十英尺的地方,显然像是标志着海洋的尽头,太阳现在转到了西面,把门厚重的影子斜斜地投向东面。
门的三分之二高度上,用黑色的正体写着两个字:
囚徒
恶魔附在他身上,恶魔的名字是“海洛因”。
枪侠听见一阵嗡嗡声。起初,他以为是风声,要不就是他自己发烧的脑袋里臆想的声音,但后来他越来越清楚地听出那是发动机的声音……就来自门背后。
打开它。它没锁上。你知道这门不上锁。
但他没去打开门,却蹒跚着绕到门背后去察看。
这门没有另一面。
只有灰色的沙滩,一直向后延展,只有波浪,只有贝壳,潮汐线,还有他自己一路过来的痕迹——靴子的痕迹和他用肘弯撑出的坑眼。他再仔细看,把眼睛又睁大一点,门不在那儿,但影子却在。
他伸出右手——噢,学习使用左手是这么的慢——他放下右手,举起左手。他摸索着,想摸到什么坚固之物。
我摸过去,可是什么也碰不到,枪侠想。临死前做这么件事倒是挺有趣的!
原来该是门的地方摸上去却是空无一物。
无门可叩。
发动机的声音——如果确实听到过的话——也没有了。现在,只有风声,波浪声连同他脑袋里的嗡嗡声。
枪侠慢慢走回原来那边,心想刚才所见一定是自己开始有幻觉了,可是——
他停住了。
他朝西边瞥过一眼——那儿原本只是一望无际的灰色沙滩,堆卷的海浪,可是这会儿,眼前却出现了一扇厚厚的门。他还能看见挂锁,也像是金子做的,上面凸起着插销,似是一个粗短的金属舌头。罗兰把脑袋向北面移过去一英寸,那门就朝后退了。罗兰再把脑袋缩回,门也推回来了。一连几次都这样。它不是出现在那儿。
它本来就在那儿。
他绕了一圈走过去对着这扇门,摇晃着身子。
他可以从海边绕过去看,但他明白准是跟刚才同样的结果,而这一次他可能会倒下。
我真想知道,如果我从门里穿过去的话,也像是穿过乌有之物一样吗?
噢,所有这些事情都叫人摸不着头脑,但其实也简单:面对一扇立在绵延无尽的海滩上的门,你能做的就是二选一:打开它;由它去关着。
枪侠隐隐约约有点幽默地意识到自己或许不会像预想的那样死得快。如果他是个垂死的人,那还会有这种惧怕吗?
他伸左手去抓门把手,那玩意儿摸上去既不像金属似的冰凉,也不是那种隐密花纹给人的灼热感,这感觉倒让他惊奇了。
他转动门把手。拽一下,门朝着他开了。
他什么都料到了,就没料到会是这样。
看着眼前的景象,枪侠呆住了,发出了他成年以来第一声尖叫,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