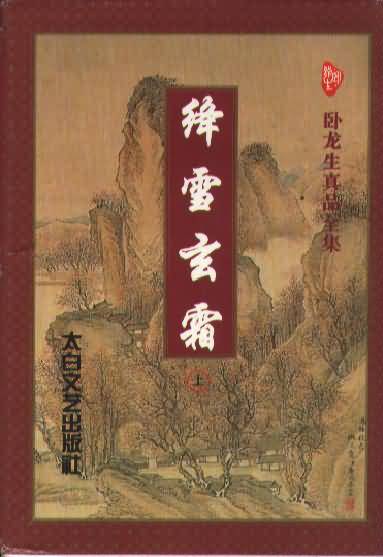九秋霜-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在这个古怪的孩子面前留下点尊严。
名叫丁香的女孩注视着我,轻轻微笑。“请不要太担心,至少他那张脸没什么事。”
她话里清楚的讽刺我已经没空挑剔。我喃喃自语,“我宁可他虽然毁了那张脸,人却是活生生的。”
她愣了愣,便不再说话。
我被这女孩引入调查组。身为医务官兼调查官,我得以获得大量有关资料信息。
昏迷不醒的他,是现仍存活的德鲁伊教相关人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
那些几乎在欧洲大陆上掀起腥风血雨的神明和祭司们,他们的尸骨已经永远留在了爱尔兰漆黑的冬夜森林。他们筹划已久的祭典和活人献祭的目的至今也没有查明。这古老而邪气的教派,一夜之间彻底颠覆。余下的只是清除残余势力,全面调查犯罪嫌疑人,以及大概许久之后的审判工作。
那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只在爱尔兰停留了不到三天。他是在第一轮搜索中于森林边缘被发现的,之后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抢救。我刚刚看到他时他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丁香为我安排了一切然后神出鬼没地消失。我想自己最好冷静下来。我不是病人家属也不是犯罪嫌疑人,于是我决定当个货真价实的医务官。我不知道凤阁究竟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主宰一切,但我持有的身份证明显然给了我极大特权。
他的状况稳定之迅速令人吃惊。所以三天后他便被转移到法国里昂,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附属医院。那时他的情况已经开始显出怪异。观察仪器显示他在某些时刻会有短暂的清醒。但那种冬眠般的昏迷掌控一切。他像个靠睡眠来积攒力量和自我医治的古老吸血鬼一样沉沉昏睡着,只在有人偶尔试图靠近他的时候,他的呼吸节律会发生变化。
血压和脉压差都很正常。舒张压没有升高。心率变化不明显。以我的专业素养来推断,这几乎不是一个重伤者应有的状况。可是管他的,只要他没事就好。
他昏迷的时候如同沉睡。我几乎不敢多看他,一看他就会不由自主发怔。这样的他让我想起那个夜晚,沉醉的少女,温柔妩媚睡脸。额头上淡淡的汗意和淡薄湿润嘴唇。我小心翼翼地,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接近他,凝视他,碰触他。我想要他醒过来,我想对他重复我终于能够出口的那一句话。
亲爱的,我为你而来,为你而在。
他处于这座医院最全面权威检测和监控之下。我不知道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病历报告却显示出一系列惊人结果。血液含氧量水平增高,细胞自我修复能力明显增强。换句话说,他真的像一个可爱地沉睡着的吸血鬼。不晓得是不是那神秘的宗教作祟,总之,他恢复的速度并不像常人。
在到达里昂的第二天,他终于醒了过来。
—Inuki—
好像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在梦里却远比现实痛楚。火焰,浓烟,惨叫。血肉焦糊味道和细微的嗞嗞灼烤声。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我并不害怕,只是那情景太恶心,牙齿不由得微微发酸。身体已经没有感觉。意识却出奇灵敏。我知道我一直是清醒着的。可是是怎样的清醒呢。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拔去牙齿切下脚爪的野兽,牢牢地捆缚得一动不能动。缝合了眼睛和嘴唇,封闭了鼻孔和耳朵,所有的一切都不听使唤,可是我仍然是清醒的。
那种感觉几乎令我发疯。
与此同时,有些什么在我的身体里缓慢而坚持地生长和伸展起来。那究竟是什么。它在我的身体里不停地同我讲话,用我所不能了解的语言。老实说,我吓坏了。我恨不得自己是真的昏迷不醒意识全无。那个探入我身体并以我所能清楚感知的速度渐渐同我融为一体的东西,它一点点侵蚀了我。乱七八糟的记忆汹涌而来。我想到很小时候看到的尸体。那大概还是在纽约,贫民窟的角落,某个经久不曾清理的垃圾箱后面,偎依在黑色胶袋之间大张着嘴巴的尸体。我害怕的不是那双只剩下两个黑洞的眼睛,是他被子弹撕开的腹腔里汹涌进出的蛆虫和蚂蚁,而贪婪的老鼠已经率先享用过这顿丰盛大餐。
我清楚地记得那小巷里的恶臭,那粘腻肮脏空气。还有那仰头望去被高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压榨得一条细线的灰蒙蒙天空。
那与死亡有关的颜色永远刻进了我的眼睛。
我害怕。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是无法得知一切究竟。比听觉视觉触觉更敏锐的却是那种侵蚀带来的知感。我知道自己被救援,被带走。他们大概试图像对待一个垂死的人那样对待我。我不能说话,所以也无法叫他们离我远些。身体里那股灼热而缠绵的力量徐徐流转,忽而凶暴忽而缠绵。在最初的时刻我以为我的筋骨血肉会就此蒸干,然而它只是渐渐注入了我,并一点点还给了我,我所有的感觉。
有些什么,在那夜那团火焰扑向我的瞬间改变了我。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似梦非梦,似醒非醒。我听到有人同我说话。迥异我身体内部那听不懂的言辞。那个人在我耳边用某种我所熟悉的语言轻声细语。他叫我的名字,叫我同,同同,像叫小孩子那么温柔,温柔得让我疲倦。沸腾的思绪在那个声音里渐渐融化。在真正陷入睡眠之前,我似乎打了个寒颤。我听见那个声音以一种我能够清楚记忆的音调轻声地说,“会好的。亲爱的,会没事的。”
他叫我dear。那个声音,那句话,我能够记得可是我没空思量。我在沉睡中醒来,我想这个梦可真长真怪。
可是当我筋疲力尽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的笑容。
让我陡然涌起杀人冲动的笑容。
他居然在我面前,就在我面前。那个怪里怪气的医生。晏雪匆。此时他看上去可真像个医生。他慢慢俯下身来,我下意识地想要躲避,却一动也不能动,只有任凭他的神情渐渐靠近。他凝视着我。那接近透明的目光出奇安静。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在我能够努力试图开口之前做出禁声姿势。然后他坐下来,在我身边。我能感到蘸水的脱脂棉轻轻扫过嘴唇时那种完美的清凉。我大概露出了贪婪的眼神,所以他才会那样微笑了一下。嘴唇像烧焦一样干枯疼痛,在他轻柔的动作下稍稍缓解。他轻声同我说话。我认命地合上眼睛。
他妈的,那不是梦。是他。
他仿佛能够猜测我的想法,在倾听他安静低语的同时我能感到他的注视。他在看我,用一种迥异从前的眼神,看得我不舒服得很。他不许我说话和移动,事实上我也没办法做什么。他说我仍在禁食期,不可以大量饮水。我睁开眼睛狠狠瞪他,我要渴死了,这人还在说风凉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伤成了怎样,不过也许不知道会更好些。他絮絮地同我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替我润湿嘴唇,我怀疑自己失水早已超过百分之二,补液根本无济于事,我渴得发疯。可是我也不想给自己搞出水中毒或者急性胃扩张,我还不想死呢。
我努力定下神来考虑自己目前处境。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简直叵测。透过墙壁我可以听见那些值班警员巡逻的脚步。我甚至能听清他们腰间的枪套和衣褶的摩擦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感觉似乎比从前敏锐太多。我呆呆地盯着晏雪,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他。我知道有人在翻动我的病历,对着X光片和化验报告窃窃私语,他们当我是什么,怪物吗?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好转起来,可是我为什么知道?
一切都没有答案。
晏雪用那种又安静又茫然的目光注视着我。那眼神逼迫我收回思绪同他对视。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看一个半死不活的我看得这么兴味盎然。如果不是现在,大概我早已狠狠一拳照准他的脸挥了上去。他垂下睫毛,我突然意识到他没有戴眼镜。那眼神通透得令我不由自主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轻轻说,“你总算又在我身边了。”
我很想做一个作呕的表情,可惜现在的我没那个本事。我不知道是该睁开眼睛瞪他还是沉默装睡,哪一种办法能让他迅速知难而退。老天啊,把这个家伙弄走。我已经足够烦了。我不需要他的出现来提醒我发生了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
他的指尖轻轻扫过我脸颊。我打了个寒颤,睁开眼睛。他还在看我。我突然发现他眼里有泪水。透明的瞳孔在水光里清澈如冰。我皱了皱眉。他似乎没有意识到那些,只怔怔地盯着我,依然是那种轻柔谨慎的语气,“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去你妈的,我怎么知道。
我很想这样骂过去。虽然我唯一能做的只是瞪着他一言不发。他摇了摇头,开始自言自语。我没办法拒绝倾听。他像个深宫内院里哀怨的老侍女一样絮叨。我默默咬牙,告诉自己这一切我其实有听没有懂。他的声音那么低柔,可是那么清晰。我几乎汗毛直竖。他说,他重复,他为我而来。那句话让我浑身发冷。我闭着眼睛仔细思考一切。自己当下的处境。我告诉自己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可是他的声音,柔软压低的音调执拗透进我脑海,那样不依不饶。他的国语流利但算不上标准,却足够一字一句说清他的意思。
他告诉我他怎样来到这里。他叙述他自己,从七月的最后一夜,到今天。我承认我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他,可是那又怎么样。我等着他骂我或者做出点更惊人的事情。毕竟眼下的处境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可是他说,他喜欢我。
我差点没叫出来。疯了,这人一定疯了。
抗议无效。他继续絮叨下去而我只能继续听下去。他这一次说的话比我们相遇这几次加起来都要多,多得多。如果我能动,我知道自己一定已经扭曲了脸孔。我闭着眼睛无声呻吟。上帝啊,或者其他所有我不信任的神明,弄走这个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家伙。
祈祷无效。我只能听着他表白下去。很诡异的,记忆随着他柔和语调慢慢铺展。四个月前的巴尔蒂摩,雨夜晶莹如银,酒的香气冰凉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