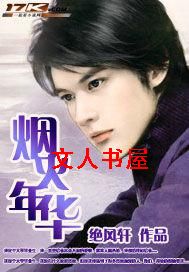草样年华ⅱ-孙睿-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知道喝了多久,终于喝不动了,再喝就都出来了,我大致算了算,应该不到8瓶,冲击记录未果。
为了不在现场喷发,我去厕所抠了嗓子眼儿。看着窗外的天,突然就亮了,感觉就像我们的青春,突然就没了。
天空飘下雨滴,上帝在为我哭泣。
举杯消愁愁更愁。我想,这时候周舟已经到了法国,忠心祝愿她万事顺利,别的想法,我已不敢奢求。
回到包房,坐下继续喝,喝着喝着,感觉耳朵失聪了,周围一切都没有了声音,只有一群人在我眼前晃动着,碰杯,划拳,抽烟,唱歌。
看着乌烟瘴气的房间里昏暗的灯光,码在墙角的三十多个啤酒瓶,电视上晃动的MTV画面,一群二十六七即将而立却不知道拿什么立的青年,他们目光浑浊,满脸横肉,正在手舞足蹈地碰杯,沉浸在空虚的欢乐中翩翩起舞……突然,这一幕在我眼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军训的照片:在一片湛蓝的天空下,一列青翠的杨树旁,一排红砖灰瓦的营房前,一群十八九岁的少年,身穿军装,戴着白手套,扛着步枪,眺望着远方,一脸对未来的坚定和自信,谁也不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未来什么样子,对他们永远是个未知数。
然后,我就像断了电的电视,往沙发里一躺,头脑里一片漆黑。
正文 尾 声
唐朝书城 更新时间:2008…9…22 10:45:41 本章字数:1193
我醒来的时候,他们都走了。
服务员说我们这屋到了早上六点突然就没有声音了,他以为出了事儿,就跑了进来,看见我们横七竖八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有人手里拿着话筒,有人拿着酒杯,啤酒顺着胳膊流下来也毫无感觉,大约四个小时后,就一会儿起来一个,因为都有事儿,便走了。
我问现在几点。服务员说下午三点,如果我还难受,可以再躺会儿,我们进来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既然已经醒了,就不躺了。我要了一杯冰水,喝完出了包房。除了难受,还是难受。
我走在北京的马路上,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发觉自己竟然那么渺小,以前从来都感觉高楼在我脚下。
也许人越大,越感觉自己在社会中的渺小。
风一吹,我清醒了许多,感觉胳膊有点儿疼,撸起袖子一看,流了点儿血,已经结疤。怎么弄的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必是昨晚喝多了摔跟头磕的,直到这时酒醒了才发觉疼,就像成长中的伤痛,当时并不察觉,也不知从何而来,只有长大了才能体会到。
青春像一条抓在手里的泥鳅,欢蹦乱跳,不经意间便会从指缝悄悄溜走,当发现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尾巴,越想抓住它,越用力去抓,它跑得越快。
当年毕业的时候,同学们收拾行李,我拿根烟在他们中间遛来遛去,并不着急,我说,我还有时间。现在,属于我的时间,已经没了。
如果让我为自己做份简历,我会这样写道:
姓名:邱飞
年龄:26岁
性别:男
曾有过: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女朋友、一些理想、八块腹肌
现拥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快二尺六的腰围、对生活悲观的态度
现在的我无比怀念和周舟在教室上自习的美好夜晚,无比怀念和杨阳在楼顶对酒当歌抽烟弹琴的深夜,还有那些曾经让我深恶痛绝现在无比怀念的课程和考试。
现在的校园已经很少能看见留长发的男生,也听不到草地和楼顶上的歌声,学校绿化得像个修补过的公园,整洁平坦,绿树红花,人为的痕迹太重,适合学习,不适合生活。
某天午夜,当我再次打开收音机,听到熟悉的Nirvana的旋律时,便不由自主想起那个背着吉他,听着打口唱片,走在撒满阳光的校园的青年——我开始迷惑,记忆中和此时的我,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Nirvana让我感觉有点儿闹了。但听到《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的时候,柯本撕裂而颤抖的声音,让我想到了周舟,于是眼眶湿润了。
柯本死得很是时候,如果现在还活着,也许同样不可避免会成为一个俗人。
生活有时候挺没劲的,但活着,却很有意思。
正文 后记
唐朝书城 更新时间:2008…9…22 10:45:41 本章字数:2038
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算上前两本——《草样年华I》和《活不明白》——凑成了我的“青春三部曲”。
之所以说“我的”,是因为这三本书的情绪和状态都是我相应年龄时的真实反应。《草样年华I》写的是大学时代的混沌, 《活不明白》写的是毕业一年后的茫然,这本《草样年华2》写的是毕业三年后的失落和无奈。
这本书费了我不少劲。
一稿写完后,发给出版社,以为再有半个月就能拿到印好的书了,然后便买了张去天津的车票,见了几个大学同学,开始给自己休假。但是第五天刚回北京,出版社就打来电话,让我过去聊聊。挂了电话,我感觉稿子可能得改,不仅仅是对错别字和用错的标点符号的修改。
第二天到了出版社,见了策划、编辑。他们对一稿给予了肯定后,说:
“但是……”
果然不出我所料,得改。编辑们说的每个“但是”都在我预料之中。这些问题,写作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但因为着急完稿,就忽略了,因为夏天要到了,天一热,我便无心做事。
一些动物需要冬眠,我需要夏休。北京的夏天令我十分难受。一进入七月份,我就开始彻底混曰子,等待秋天的来临,除了吃喝拉撒睡在已经紊乱的基础上仍进行着,其他事情都无法继续开展,包括写字。上大学时的那些不及格科目,也多出现在暑假前的考试。印象中特别清楚的是,我的四级是在寒假那次考试中通过的。
这样的曰子每年大约有三个月,到了九月份,我便开始好转。每到年终自我总结的时候,都发现这一年后半年开始的那段曰子,竟然没的可总结,我的有效时间才是别人的四分之三。如果按一个人活八十年计算,那么我有二十年的时问是在等待——太浪费生命了!
但是这个夏天,我有事可做了,而且必须在夏天做完,因为如果拖到秋天,那时我的心态不知要发生什么变化(二十岁的时候,我的世界观一天一个样;现在,我的世界观一个季度一个样),也许会彻底否定一稿,推翻重写——就像我现在看前两本书,都怀疑是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是自己付出过心血的二十万字,我决定在生活态度改变之前,抓紧时间改完出版。
这次谈话,也让我知道了,写作绝不能求快,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还欠火候儿就端上了桌,谁吃了也会感觉不烂。我得回回锅。
出了出版社,门口右手停着一辆夏利出租车,司机一直盯着我看,我态度坚决地朝左边拐去,司机按了几下喇叭,我没有回头。我想溜达溜达,把刚才编辑们提到的问题好好想想,这是我的习惯,就像吃完饭要散散步一样,有助于消化。
我半低着头,穿过一条骚臭的地下通道,沿着一条干旱的河边,不紧不慢地走着。不知走了多久,我对如何修改有了初步思路,这时一抬头,发现马甸桥到了。我是从健翔桥走来的,这段路大约两公里,刚才没打那辆夏利,这样我就省了三块钱,如果是富康或伊兰特,那么能省四块钱。
走了这么长的路,竟然一点儿没感觉累,也许是因为脑子被别的事情占着。我忽然意识到,长征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当时革命形势并不乐观,红军战士们一边跋山涉水,一边思索着严峻的革命现状,不知不觉就走了两万五千里,不知不觉就迎来了曙光。
回来后,开始修改。可能因为心里急(尽管我知道急对写作一点儿好处没有,但还是控制不住),有火,晚上睡觉又被凉风吹着了,第二天我便开始咳嗽,连咳二十多天,发自肺腑,呕心没沥血。声音之大,有时候走在路上能咳响了汽车报警器。
这段时间我每天吃三顿饭,四顿药,还拍了今年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医院的x光室照的。饮食上忌烟酒,避辛辣,喝不了凉的,吃不得烫的。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吃水煮鱼便宜的地方,打算每礼拜去一次,现在只得告吹。和哥们儿在外面吃饭,不但喝不了凉啤酒,连常温的也不行,只能喝着免费的茶水,看着他们端着杯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并接受他们在喝酒的间隙对我提出的批评,这让我知道了,身体好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了更多人。
带病改完二稿,发给出版社,他们看完说可以了,让我回去给书的副标题想个名字。我一边养病,一边想,最后想到现在这个名字:后大学时代。因为这本书就是写四年大学对毕业生后续的影响,以及无论毕业多久的人也无法摆脱与大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四年,说严重点儿,能影响人一生。
“三部曲”的写作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对生活的认识,像一眼泉水,不断冒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蓄成了一个小水坑,现在我把水盛进三个罐,坑里的水就剩的不多了,不够再盛满一罐的,好在我仍在成长,泉眼没有干涸,时不时地还往外冒着,等把水蓄得差不多了,又可以盛进罐里了。
也许“三部曲”仅仅是一个开始,说不定会发展成“六部曲”,甚至更多。
孙睿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