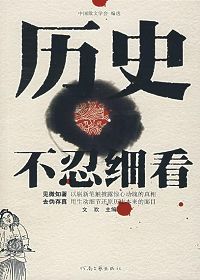教会历史-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联盟之所以在普世合一运动中扮演这样吃重的角色,与穆德作为它的首任主席是分不开的。穆德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世合一运动的灵魂人物。
1920年,因欧战而有七年未曾召开过大会的联盟召开第十届年会,穆德在会上辞去了充任二十五年的总干事一职,改任主席,直至1928年。
在两次大战期间,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积极推动各地学生团体参与战地救援、难民救济等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後,联盟成立了欧洲学生救援会(European Student Relief)。四年後,四十二个国家的学生组织筹募了五十万英镑,援助十九个国家的饥饿学生。後来欧洲学生救援会成为独立组织,易名'国际学生服务处。'(lnternationnal Student Service),後再易名为'世界大学服务处' (World University Service),这个组织至今仍在运作。
直到1960年代为止,联盟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1972年,联盟在组织架构上作了重大变化,原本中央集权的组织一分为六,在非洲、亚太地区、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北美等地,各自成立地区总部,而日内瓦则变成各地区的联络处,藉以容让不同地区的学生团体因应地区的政治社会环境,而拟定其学生运动的策略,及从事处境神学的反省。
不过,由於在北美及欧洲自由主义神学愈来愈泛滥,对一向站在时代前线位署之学生运动的影响尤为显著,联盟逐渐失去对传统意义的灵命成长与宣教使命的关怀,而社会福音思想更将不少前卫的基督徒学生引领到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战线,这引起了许多信仰较传统的基督徒不满。1910年,英国一些保守的基督徒首先脱离基督徒学生运动,另组'大专学生福音团契'(Inter…Varsity Fellowship,简称IVF),如此开始另一个基要主义的普世学生运动,「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r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IFES)於1947年成立。嗣後,普世基督徒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基督徒学生组织部分成'福音派' 与所谓'普世派' 两个阵营。
六、七十年代,普世派的基督徒学生运动愈趋激进主义,不少成员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造成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本身的分化甚至分裂。七十年代以後,随著福音派的迅速增长与自由派教会的没落,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基督徒学生运动都变得衰微,乃至结束。相对地,各种形式的福音派学生运动,如学园传道会、导航会和学生福音团契,倒有相当可观的增长。
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与中国近代教会历史曾发生过一次密切的关系,但却是相当悲剧性的。事缘1922年4月,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园召开第十一届年会,这是自欧战後联盟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上,德国代表提出有关欧战的战争责任的讨论,其他国家的代表群起反对,引来极大冲突;穆德虽然尽力保持中立,却被指摘为只顾友谊而牺牲了公义。此外,会议的召开亦惹来中国学生的抗议。他们反对这个富帝国主义色彩的基督教组织借用中国的高等学府,举办一个旨在荼毒中国青年心灵的会议;他们成立'反宗教大同盟' (後称「非基督教同盟。),举行各种抗议活动;在政党的援引下,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断断续续地绵延六年之久。这是继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後,中国另一场大规模的反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日後在中国的命运,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许多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所产生的反教议题(诸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至今仍为对基督教不友善的人所讲论。
穆德作为联盟的主席,当然出席了北京的这次会议,这是他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其後穆德分别在1925年、1929年、1935年重访中国。他合共曾到过中国七次。不过,大概是由於会议前後所发生的种种不愉快事件,穆德没有留下任何关於这次会议的记录。
3.促成国际宣教协会。
1910年6月10日,一个重要的普世宣教会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召开,是为「爱丁堡宣教大会'(Edinbrugh MissionaryConference)。这不仅是首次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对教会史家来德里(Kenneth S. Latourette,1884…1968)而言,这次大会更象徵著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标志著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有关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宣教会议的构想源自1907年举行的「北美海外宣教会议。(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America),在穆德及其他主催者的积极推动下,来自不同国家的一千二百名差会代表、宣教士及教会领袖,云集爱丁堡参与是次盛会。穆德作为主席主持整个宣教会议,亦在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他再次确认向未信基督的民族传教是教会至高的责任,而现今正是践行这个使命的最好时机,故全球各地的教会和信徒必须携手合作,集中宣教资源,俾能更快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使命。会议的成果是一本厚达二百五十页的报告:《基督教使命的决定性时刻》(TheDecisive Hour of Christian Missions)。
大会拟筹备成立一个普世的宣教组织,并首先组成绩行委办会(Continuation mittee)以董其事,穆德被选为主席。委办会刻意吸纳後进教会的代表,来自中国的诚静怡亦是委员之—。不过,由於他及其他亚非代表根本不能长途跋涉地前来参加会议,故委员会仍由欧美代表主持和运作。续行委办会在1910年通过一份宪章,并决定出版一份宣教刊物:《国际宣教评论》(InternationalReview of Missions),於1912年1月创刊。
1912至1913年,穆德作了一次重要的环球之旅,艾迪亦同行。除宣传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异象,协助後进国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外,同样要紧的是他们的环球学生布道工作。行程的首站?
是印度,然后在1913年1月转到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罗炳生(E。C。 Lobenstine)和诚静怡出任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於 1922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在是次旅程中,穆德和艾迪亦在中国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共有七万多人次参加,另他们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其後,穆德等转赴朝鲜及日本,协助日本成立续行委办会。
1922年5月,乘出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之便,穆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虽然他并没有筹备或主持这个会议,但却在大会两次发言,并对会议产生相当影响。因著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保守派的差会和宗派拒绝加入基督教协进会,今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大打折扣,不过,协进会的成立,仍是合一运动的一大跃进。同年,日本的续行委办会亦改组,成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穆德也出席了是次会议。
由於国际政治形势转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永久的国际宣教组织的构想被迫拖延。直到1921年10月,英美等国家不同差会的负责人在纽约慕康湖(Lake Mohonk)开会,组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为会员单位。协会的目的在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决定不处理任何教义与礼仪的问题,留待'信仰与教制运动'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下详)处理。协会出版并发行《国际宣教评论》及其他宣教研究成果。
国际宣教协会十七个创会会员中,有十三个为西方的差会。不过,协会也积极邀请亚非拉地区的教会代表加入,以增强其普世的代表性。嗣後,协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大会:耶路撒冷(1928、印度马德拉斯的坦巴兰(Tambaram,1938)、韦比(Whitby,1947)、惠灵根(Willengen,1952)、加纳(Ghana,1957)及新德里(New Delhi,1961)。
1941年,由於感受到来自年轻同工的压力,穆德辞去国际宣教协会主席一职。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後,国际宣教协会面对愈来愈多呼声,要求将组织并入成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部门。结果在 1961年的新德里会议上,国际宣教联会宣告解散,变成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事工部'(Division of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C.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
穆德在1928年国际宣教协会举行耶路撒冷会议後,便正式退休,离开青年会的工作。退休後,他到不同地方主持讲座,并将讲稿付印出版,包括《今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召唤》( The Presnet DaySummons to 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1931),《释放基督教平信徒的力量》( Liberating the Lay Forces of Christian,1932),有关学生工作的《合作与世界宣教》(CooPeration and theWOrld Mission,1935),为国际宣教协会所做的全球报告《今日的世界福音工作》(Evangelism for the world Today,1938),他的自传《五个年代与一个前瞻》(Five Decades and a Forward View;1939),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3-1971)等合著《基督教的危机》(Christianity in Crisis,1941),与更大的福音工作》(The Larger Evangelism; 1941)。
穆德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青年事工和宣教方面,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对於教会性的合一运动,诸如'信仰与教制' 、'生活与事工' (Lifeand Work)等运动,参与并不太多。譬如说,在生活与事工运动中,他没有出席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

![[网王]黑历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39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