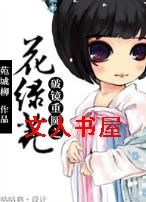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 作者:司马宣王(晋江银牌推荐高积分2014-09-11完结)-第6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出现在火光下,向那女孩询问了几句,女孩抬手指了个方向,那些人即刻又消失在寂夜的重帷背后。
没有丝毫不同。
他站住,在刚好能居高临下窥见那女孩的地方,将自己的身形融入钟楼在屋顶上投下的阴影里。不远处,永昼宫及侍立于它身侧的晨夕双塔静静矗立,它面前的广场已是空旷一片。为了不搅扰这座宫殿的主人休息,狂信徒们暂时散去了,但他们数小时前的高喊已经弥漫到空气中,为哥珊的每一个人所呼吸,应和着那尚未消逝的热潮,睡梦中的圣城亦无声呓语。
萤火抬头望向夜色笼罩的白色大理石塔尖。那里,他知道,安置着纯白之城的心脏。
教皇在夕塔最顶层的冥修室里小憩。
他靠在带扶手的座椅上,身体微侧,以手支颐,那姿态让他看起来像在沉思。或许并不能说“看似”,海因里希想——自从来到教皇身边,他再也不怀疑世上有一面安睡一面思考的人。命运剥夺了这种人做梦的能力,却给了他们一副超越常人的、不论何时都能全速运作的躯体。就这一点而言,如果真有神明存在,它确实是公平的。
风把长垂及地的窗帘掀了起来。侍卫长走过去,将它们挽上。当他转回身时,他发现教皇醒了,在立式烛台的昏光下澹静地注视他。
“你回来了。”圣曼特裘说。
海因里希跪下,吻了教皇戴着玺戒的手。“幸不辱命。”
“这事对你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教皇微笑,“叫阿玛刻严守秘密,在万安节祭典前只需等待指示。你拿什么作筹码令她配合,这不重要,我只希望届时行动得干净利落——圣裁军再也经不起任何无谓损失,两年前的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他的声音轻而有力。海因里希开始怀疑教皇刚才是否真的睡着,他很少看到一个刚从熟睡中醒来的人头脑如此清晰。“对了,”只听对方问,“你去见过了导师的遗容吗?”
“是的。他被戕害,然而面容如同安寝。”
“等再过两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教皇摆摆手,“天气慢慢热起来,尸体变得很快,但他那些弟子们在它全烂光之前恐怕是不肯举行葬礼的。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让刺客伏法,自己却只会跟着大流蛮干一气,今天还有几百个人跑过来,要求我追授那老头为圣徒——可是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没有名字,怎么写进圣册,怎么编成颂歌让信众传唱?难道要我把一座题为‘无名圣者某’的雕像搬进星煌殿?那太可笑了。他们既然在入会时宣誓舍弃一切,那就该有舍弃一切的觉悟,何况现在,圣徒这个称号可不比以往更有价值。”
“恕我愚钝,您打算从哪里开始调查凶手?万一……”
教皇唇边的笑容敛了下去,变得耐人寻味。“你觉得刺客如果是冲着我来,有必要打草惊蛇么?”
“……的确。现在这个局面,或许就是他们想看到的吧?人心大乱,信徒的愤怒被转移了方向。”海因里希顺着教皇的意思说下去,“这多半只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谁会从中渔利呢?帝国激进派的渗透者?还是您打算让阿玛刻对付的……那人?”
教皇站了起来。“这事交给你了。”他用略透着疲惫的嗓音说,“你心里有数,不要吝惜调动你的属下吧。夏天快来了,苍蝇一向都不缺,只要它们阻碍不了我的驱驾,几只苍蝇拍子就能应付。至于那人——”
冥修室的门忽然轻轻叩响。持默语戒的侍僧走进来,双手交叉行礼,奉上一张牛犊皮纸的薄笺。每个以私人身份进见宗座的信徒都必须以书面形式递交请求,这是自古有之的规矩,然而当教皇看到那张纸笺上的姓名,手指下意识的用力令海因里希觉察到了来者的异乎寻常。
“走吧。”教皇低声说,“跟我去谒见厅。他来得可真是时候。”
“他……?”
“是啊,”教皇披上侍卫长捧过来的缎面裘皮大氅,深吸了一口气,“你刚刚提到的那位,圣廷的英雄,帝国的奸贼,第三军统帅凯约将军。”
老人如祖母绿一般颜色的眼睛盯着谒见厅主座背后的那幅壁画。烛光从两侧照过来,壁画的色彩和细节被隐匿在淡淡的黯影里。历史是一个轻纱覆面的女郎,伫立墙上,五官模糊,只依稀透出肌肤泛黄起皱的底色。画的内容是武圣徒曼特裘为自己加冕,长有三只头颅的飞狮用纯白的羽翼覆在哥珊上空,武圣徒的装束一半是铠甲一半是祭袍,正将宝塔形的三重冠戴到自己头上。在他身边侍立着一个茹丹男人,和一个红发碧眼的老者,都全副武装,然而在最靠近圣曼特裘的地方,有一处非常显眼的人形空白,被填上了无数大张着嘴的面孔,可谁都能看出,那是涂抹后再修改的痕迹。
侧门的帷幔拉开,他听见熟悉的步伐声。位于壁画中心的武圣徒似乎微微一晃,随即被一个长而峭拔的黑影覆盖。
老人在来者刚刚坐定、还未及开口之前,匍匐过去,亲吻对方的足尖。
“您怎么了,将军?”教皇有些惊异地垂视着这个自己熟识已久的人,“请起来吧。圣裁军统帅是不必向神的仆从行如此大礼的。”
“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猊下。”严霜皑皑的眉一直低着,压住那深绿色双眸里的光泽。自从休战归国后,他第一次踏足这神圣的永昼宫,却是以这种与战场上截然不同的姿态——赤着脚,头发散乱,躯体瑟缩在一领破旧的粗麻单衣里,全身上下别无他物,彻底地凸露出原先被戎装掩饰的枯瘦干瘪来。凯约,新圣廷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位名将,已完全从这个佝偻无助的老人身上消失。对逝去岁月的悲号,对疾步走来的大限的惶恐,在他的皱纹间如此不加掩饰。
“如果连您都有罪,那么主父统治的国家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了。”教皇弯下腰去,亲自搀扶起伏倒在地的老人,“您是教导我行军谋略的老师,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我发誓,那些往您头上泼脏水的人,就等于将我的三重冠扔进泥污,狠狠践踏。总有一日,主父的愤怒会令他们自食其果。”
“耶利摹人和舍阑人想要我的脑袋,不是短短几天的事了。哪怕战死也不肯在屈辱的和约下苟延残喘,我理解那个千年帝国的尊严,只是我太过无能,辜负了上百万人的厚望。”老人深深顿首,眼睛却始终不曾抬起来正对教皇,“我年纪大了,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如果惩罚我能稳固圣廷与帝国之盟,不管什么处置,我都心甘情愿地领受。”
“您想让我承担信徒与民众的唾骂?谁在内忧外患的时候还能做到您这地步!我虽然没能亲往前线,但谁是谁非至少分得清清楚楚,您要我为了那些个只懂搬弄舌头的闲人,就叫跟随您的三万七千名将士鲜血都白流了么?”
教皇猛地一拍座椅扶手,说到最后,声音也渗出几丝沙哑,海因里希不失时机地端来圣盅,但教皇撇撇眉,示意侍卫长给茫然无措的老人送去。
“喝了这杯水吧。”他的眉宇重新变得和颜悦色。“我以圣盅的祝福、以辉光之父最亲近的侍从之名立誓,一旦这杯中清水沾唇入喉,凡阳光照耀下,再也没有人能加害您,再也没有言语能污蔑您、损伤您。”
老人枯枝般的手颤巍巍接过,却并未凑往唇边。
“……我想告解。”他忽然嗫嚅,“吾兄,您能允许吗?您愿意听一个满身血渍、除此一无所有的老头独自向您告解吗?”
海因里希望着他,又望向教皇,笑了笑。他在教皇沉默的颔首中施了一礼,快步离开。帷幔放了下来,只听见侧门外的持戟卫士退去的脚步声。
没有风,但大厅里最粗的一支火炬似乎猛地跳动了一下,然后熄灭了。
老人跪坐在原地,感到黑天鹅绒一般柔软的阴翳蒙上自己眼睛。当它们再移开时,他看到教皇正用一根细长的蜡烛点燃笔画前礼敬池中的水盏。那些浮动的奶白色光辉,如同睡莲绽放,融汇成一道星华流溢之河。壁画上的影像在这河流中浮动着,手持弯刀的茹丹男人,身穿甲胄的红发老者,还有填满那片空白的、千万张没有眼睛鼻子耳朵只有嘴的面孔,它们同被飞狮和过往诸圣翼护的哥珊城一样,在幽影与实体之间、故去的时间与长存的空间之间、死亡与不朽之间,用一瞬的凝固绵亘起了一条漫长道路。
那个仿佛是从壁画上走下来的人,来到他身边,将手放到他头顶的虚空之上。
他的仪容如此雄伟,完美无缺,兼有战士的力量与祭司的威严。
“真是……令人惊叹。”仿佛是被他身上散发的光芒刺伤,老人眼眶里溢出了濡湿的痕迹,“您的容颜,一如当初被神明选中之时……”
外表远比实际年龄年轻的男子低下头,轻轻微笑。“我已经老了,”他说,“已经过了被称为‘正当盛年’的时候。很快有一天,我会赶上将军您。一切生命终将凋萎,一切有形之物终将化为尘埃飘逝,然而人的灵魂永存不灭。”
“我今年七十一岁,比您多活了二十余年。直到五十一岁,我以为我已经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主父和您时,我有了自己的独生儿子。他的母亲因为年纪太大,在生下他后去世。他是如此虔诚地向往光明,才受了濯顶礼就离开了我身边,拿起长剑去追随一位圣徒战斗。可他的命运是什么?他没有光荣地死在圣战中,却沦为叛军将领,身首异处,尸体被烧成灰,头颅则被插在长矛上腐烂。他死的那一刻,我正在与舍阑人战斗,我以为主父正将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赐给我这老迈之躯奇迹般的力量及勇气,可当我回国得知消息,甚至不能见他最后一面,甚至不能为他罪孽深重的灵魂祈求垂怜!他死的时候还不足二十岁,不曾婚配,不曾欢爱,不曾为神奉献,不曾体味过人生最大的欣喜,而今却堕入火渊,永远在地狱的最深处挣扎悲哭!请告诉我,吾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