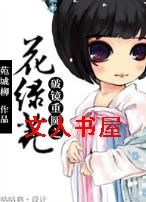髑髅之花 作者:司马宣王(晋江银牌推荐高积分2014-09-11完结)-第1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在乎。包括他是否爱我,或者憎恶我,都不在乎。我只要他活下来。”
“倘若你所言非虚,我必履行承诺。可是,女人——你又可曾考虑过自己呢?”
“您打算处决我吗?”
她的利用价值已罄尽,坦诚是最后的底牌。“我不杀你。当初没有这么做,现在也不会。”挡在他必经路上被他碾过的女人,侵蚀了他最珍视的两个孩子的女人。时间改变了她,然而正如十三年前那样,仍不足以让他对她抱有任何感情,无论怜悯还是仇恨。“你欺骗我,则另当别论。但如果告密属实,那么昔日眷顾于你的黑暗自然会惩罚你的背叛。我不想再看见你。一旦我证实你的情报,你就得立刻从我眼前、我统辖范围内消失,在我有生之年都不得踏足我的国土半步。回到那舍弃你的黑暗中去吧。像当年一样,一个人孤独地活着,自生自灭吧!这是比死亡更适合你们这种生物的结局!”
“感谢您。”
她顿首,仍朝着虚空。“再慷慨不过的处置。”
“因为您当年同样的慷慨,我活下来了。拜您所赐,我成为了当年愚蠢的我从未想过会成为的人,我经历了一个女人能经历的几乎所有艰辛。可我依然庆幸自己的生命如此坚韧,足够承受循环往复接踵而来的获得与失去。有人宁肯死,也不愿行尸走肉般生存,可我认为在最艰难的时世拥有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富足。黑暗的恩赐本不属于我,而我不过物归原主罢了,就算孑然一身无凭无恃,再没有奇迹发生,也不要紧。我从黑暗中已经汲取了够多的力量,这十多年来我阅尽人们心思转变,看着一念之差如何推动他们的行为,推动命运波澜;即使失去这种能力,我也依然可以从人们的言行举止中判断其用意,触及他们内心。我的不幸与幸运是树上百味杂陈的果实,终究要熟极而落,经验却是深扎土壤的根系,永远归我所有。”
“感谢您容许当初那个幼稚无知的我活着,”她平静地说,“夺走我的一切,而仍让我活着。”
他们陷入沉默。大厅被沉默包围,像在等待某个耳朵听不见的声音来临。吊顶上弹奏、祈祷、念诵诗篇、拔剑战斗和静静观看他们对话的诸圣画像仿佛也在等待着那个声音。一只鸽子从天窗飞进来,在圣徒足底的横梁找到了落点,垂眼张望。
爱丝璀德取出什么,弯下腰,轻轻放在身侧的地毯上。
“这件东西原本是您的。您可想要收回?”
那是枚配有白铜细链、镀金的镍制十字章护身符,十字的交点用紫色珐琅镶嵌着日轮。
“云缇亚送给了你?留着它无妨。打从它一开始被另外一个女人拥有,就只是作为虚弱感情的见证,除此别无用处。将它带在身边吧,让它随时提醒你这个事实。”
她捡起它。
“爱丝璀德。”
教皇忽然唤道。
他第一次称呼她的名字。
“你是少数没有让我浪费时间与之交谈的人,”顿了顿,他补充道,“……在弱者当中。”
目光无法抵及的地方,她的脸或许微笑着,却与这句话无关。
鸽子飞出了窗外。
“对了,猊下……您一定有个期盼已久的愿望吧。”
被士兵带出大厅之前,她停伫片刻,说。
“一定是特别宏大、壮美、光辉万丈,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也要将它达成的愿望。
“我呢……我也有个愿望。当然相对于您的,它太普通,也太渺小了……
“我不祈求这个世界上良善的人都能幸福安乐,但求他们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如果连这也无法实现,我希望他们至少能活着。”
“先是活着,”她说,“然后才是尊严。”
爱丝璀德向圣堂外走去。
她沿鲜红长毯,一步步走近敞开的厅门。黑暗在她眼前如春冰绽开细纹,慢慢皲裂,某种明亮的介质像迅速涨溢的河水那样上涌。她开始辨认出颜色。区分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的颜色。尽管贝兰曾教她记住它们的名称,一时却还无法与原初的感觉对应:地毯炙热的颜色,石砖地面清凉的颜色,花束温暖安谧的颜色,圣像古旧的颜色,士兵甲胄冷而坚硬的颜色,还有拼嵌玻璃窗上斑斓错杂令人目眩的颜色。
随后她看见那明亮介质的实体。
它向她扑奔而来,透过窗,是一束束琴弦似的线缕,透过门则是洪流,将她融于其中。
她看见了太阳。
作者有话要说:
☆、Ⅳ 光翳(2)
“那女人拥有一种黑暗的力量。”
痛。泥沼浸没双膝,剧痛却早已进入身体内部向上奔涌,淹过了胸口、喉咙,升到鼻腔,直冲大脑。无法挣扎,无法呼喊。……谁?谁在跟我说话?是谁的声音?
“人心最深处、最隐蔽的秘密对她如同曝露在明眼人面前的阳光之下。她是黑夜中飞翔的九音鸟,以月亮的阴影为猎物。你越是刻意掩饰,她看得越是分明。”
啊……妇人。我们在哪儿见过?……你来提醒我么?来救我……来杀我么?
“请远离她。”
别……别再说了。太晚了……
“永远也不要靠近她。”
求你……不……不管是谁都好……
“她会洞穿你,出卖你。”
杀了……我…………
“然后毁灭你。”
云缇亚依旧睁着眼睛。
没人来蒙上它们,或许是没人相信他此刻还能看见什么。空气里的炙热酸味像烧红的针尖戳刺鼻孔,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的梦,梦里有刑台、绳索、烙铁、刀匕、斧锯和煮沸的液体,各种杂音环绕他,一场等待将他脔割而食的盛宴。
“把他绑结实些。待会一动就糟了。”
“麻药准备好了吗?”
铜壶的长嘴捅进喉管。连颈部似乎也被固定住,至于吞咽更加无法主动完成。他分辨不出和上次对他造成无尽痛苦的药汁是不是同一种。一张脸冒出来,观察他的瞳孔变化。圆胖脸盘,眯缝小眼,鼻子上夹着镜片,海因里希的医师,他恍恍惚惚想起。又是新的一轮拷问?
可我没有价值了啊。我只是废物、垃圾、残渣,除此什么也不是了。
他感觉自己站了起来——确切地说是漂浮。药性分割灵魂和肉身,之前和肢体一起被牢牢绑缚住的意志终于真正成为最轻和最自由的东西,他感觉自己融入“乌有”当中,而一切的“有”则在他眼底展开。他在房间上空漂浮,悬于每个人头顶俯看下端:木制平台上不成人形的身躯(他第一次这样疏离地从外部审视自己),医师的秃顶,两口沸腾着浓醋和烈酒的锅,那三个将他变成这副模样的幽灵(它们依然一声不响,只换了身干净的灰衣,戴着在醋里煮过的手套),火炭盆,装药膏和绷带的盘子,还有她——
是她。
他已认不出自己了。但他认得她。
那个正全神贯注地把接下来要用在他身上的刑具,匕首、锯片、夹钳、剪子,一件件从醋锅里捞出来的女人。
那个带给他此前遭受的一切都不足以比拟的痛苦的女人。
他曾经爱过的女人。
“你很果决,”医师对她说,“不过大概会白忙活。锯掉他的腿也不能挽救什么啦,他全身都是伤,太虚弱,估计承担不住手术的重创。就算这些都撑过去,创口顺利愈合没有感染,我认识的被截去下肢的病人,顶多也只能活个几年,还得像狗一样爬着,熬过无数个被魔鬼诅咒的阴雨天,直到爬进坟墓。我倒是不介意挑战技艺,可对你来说,花大力气换来什么结果,得有所觉悟才行。”
“如果不这么做,他活不了三天。别耽搁时间,医师。扎上止血带。”
是的。
那是她。
永远冷静、圆融,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永远能做出最精准的判断和最适当的取舍。犹如黑暗的真相一样加诸于她的特质,也是他最厌恶的一点。她本应是情感的动物但她依靠完美得可怕亦可憎的理智来行动。早就知道了,他们俩绝非同路人,他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东西在她那儿可以像掸一掸灰尘似地舍弃掉。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两个人竟会相爱?!
“用这个?扎住膝盖上方?”
充分浸湿的牛皮绳索绑紧大腿,她夹起一块红炭小心凑近,让湿牛皮在炙烤下逐渐干燥,更加紧缩。“想象力真丰富。”医师不断搓手,活像循血腥味而来的苍蝇。
“开始吧。”爱丝璀德说。
停下!别碰我!你这妖妇!
两个幽灵分别握住锯子的一端。它们干这个活儿再拿手不过:同时具备膂力、冷酷和对人体结构的精确认知。锯齿切入朽木般的死肉,接下来的事对它们只是家常便饭。老到的屠夫熟极而流地进行着宰割。肌腱分离了,有什么强硬的东西还在用咯吱声负隅顽抗。来呀,快在我喉咙这儿锯下来,然后我们都清静了。听到吗,贱货?快叫他们锯掉我的头!快呀!
她欺骗了他。那时他以为她的力量已衰竭,双眼真正地不可视物,因此在去哥珊的前夕才终于毫无防备地与她相处。可那只不过是个把戏罢了,故意让他沉耽于蒙蔽到她的得意和瞬间温暖里。早在贪恋那虚弱的温暖时,他便泥足深陷。
现在一切都晚了。
愚蠢啊,云缇亚!你是何等幼稚和盲目,竟然爱上一个魔物!哪怕你一直在畏惧她!哪怕一开始你就得知她最终要毁掉你!
身体的一部分脱离了他。但并不是头颅。
也不是痛苦的源头。即使漂浮在空中,他所见的那具身躯的痛苦仍然存在,仍然位于那里。张开大嘴鲸吞上来的泥潭将永远陷没他。
“没有流多少血。”医师的声音,“居然管用。”
“把针线递给我。”
“你想干什么?不是该用沸油或烧红的熨斗吗?”
“靠烫伤止血等于喝毒药解渴。遇上脓血症或坏疽,他必死无疑。得找别的方法封住血管,至于消毒可以用煮沸过的烈酒清洗创口来完成